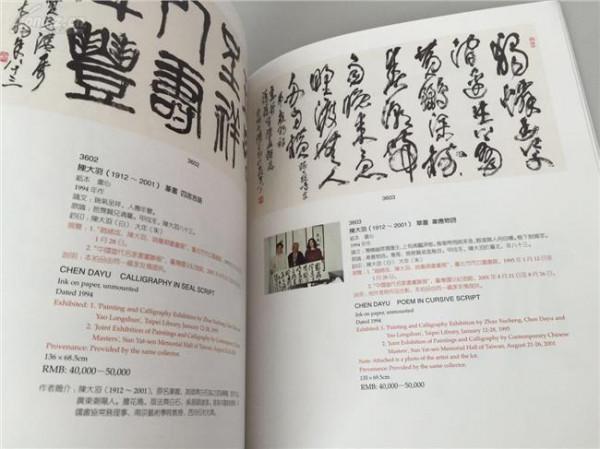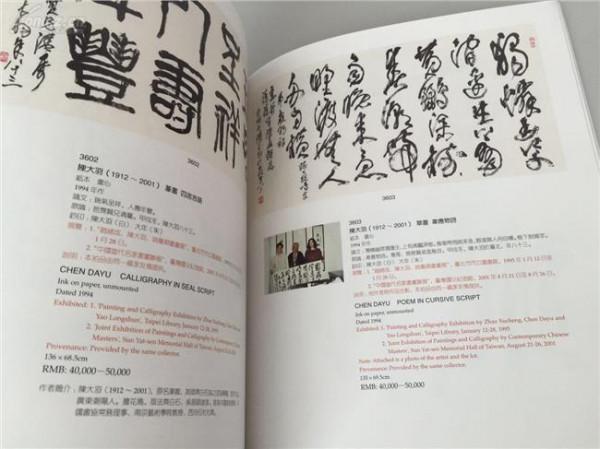黄永厚画作 忆·黄永厚丨凌宇:我与永厚先生交往的那些琐屑
在我的感觉中,2018年似乎是一个特别之年。因为就在这一年,国内各界著名人士,诸多鹤驾西行,永厚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虽因诸多原因,我未能亲至灵前吊唁,但思念之情却不绝如缕。先生的音容笑貌,时时如在目前。

我与永厚先生第一次见面,大约是在1990年夏秋之交。那天,我接到作家刘舰平的电话,说永厚先生现正在长沙,想见见你。并问我能否抽空见见面。永厚先生是名闻遐迩的画家,又是沈从文先生的至亲,因研究沈从文的缘故,黄永厚于我,早已是一个熟识的名字,能与他见面,当然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在陪我乘车去永厚先生下榻的蓉园宾馆的路上,舰平说起了永厚先生想见我的缘由:当年,舰平的小说 《船过青浪滩》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永厚先生读过后,十分激动——这篇小说勾起了永厚先生连绵不断的儿时记忆。其后,因文为媒而与舰平相结识。

青浪滩是沅水中游的一个长年恶浪咆哮的长滩、险滩,位于沅陵县境。上世纪抗战时期,永厚先生一家就住在沅陵。母亲在乌宿教小学,父亲则做过青浪滩绞船站站长。这次永厚先生来长沙,舰平见他无书可看,便将我送舰平的《沈从文传》拿给他,让他闲时翻翻。谁知永厚先生看过后,便执意要舰平邀我与他见面。

一见面,我便立即感到永厚先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湘西汉子:热情、爽直,丝毫也不掩饰自己的内心情感。甫一落座,当我问及其兄永玉先生近况时,他便开始数落永玉先生的不是。其时,正值永玉、永厚兄弟因种种误会而失和。
这等兄弟间的龃龉,自不容我辈置喙。于是,我赶紧寻机转移话题,和他谈从文先生,谈与他家世相关的《一个传奇的本事》。——从文先生的这篇传记性的散文,就是通过对其表哥黄玉书(即永玉、永厚先生父亲)一家人生际遇的叙述,浓缩在那个战乱年代乡土知识分子及湘西地方的悲剧命运。当我谈及这篇文章的分量时,永厚先生冷不防插一句:
“表叔看我父亲,那是居高临下!”
我不觉吃了一惊。因为在所有沈从文研究者那里,谁也不曾留意到这篇文章思想情感取向的这一节点。文章曾这样叙述黄玉书:
“面容憔悴蜡渣黄,穿了件旧灰布军装,倚在门前看街景。……事业不如意,人又上了点年纪,常害点胃病,性情自然越来越拘迂。过去豪爽洒脱处早已失去,只是浓眉下那双大而黑亮有神眼睛,还依然如故。也仍喜欢唱歌。邀他去长沙著名的李合盛吃了一顿生炒牛肚子,才知道已不喝酒。
问他还吸不吸烟,就说:‘不戒自戒,早已不再用它’。可是我发现他手指黄黄的,知道有烟吸还是随时可开戒。……第二天再去看他,带了别的同乡送我的两大盒吕宋雪茄烟送他。他见到时,憔悴焦黄脸上露出少有的欢喜和惊讶,只是摇头,口中低低的连说:‘老弟,老弟,太破费你了,太破费你了。不久前,我看到有人送老师长这么两盒,美国军官也吃不起!’”
平心而论,文章的叙述当属写实,叙述者主观上似乎并无自矜自炫之意。但其笔致,则迹近鲁迅在《故乡》中对闰土的叙述。从被叙述者角度看,便难免有被悲悯之感。——永厚先生可谓是一语中的。
又由此谈及凤凰人物。我说:“凤凰不得了,一座小小县城,出了个熊希龄,一个陈渠珍。文人中有从文先生,永玉先生和你。应该写一部人物合传,就叫《凤凰三杰》!”永厚先生赶紧说:“千万别写我!”
《一个传奇的本事》曾这样叙述永厚先生:“……十二岁,也从了军,跟人作护兵自食其力了。”由此,永厚先生回忆说:
“有一次行军,我掉了队,成了一名散兵游勇。一路走来,又饿又渴,且身无分文。实在累得走不动了,便朝路边一空地躺了下去。心想:这时如果身上有一块光洋,那该多好。当我躺下身去,头一着地,便感到触到了一个硬东西,便伸手将它从脑后摸了出来。拿到眼前一看:一块光洋!
那真叫天无绝人之路!”
永厚先生的画品位极高,我私心里早就想得他一幅画。但一来生就的脾性,我从不愿为自己向人求字求画;二来缘于我和从文先生的一次谈话。大约是在1980年,我去从文先生家里,见他家四处皆无黄永玉先生的画,便问:“您这里怎么没有永玉先生的画?”沈先生漫不经心地说:“人家那里要卖钱的!
”(直到从文先生80岁生日,方见沈先生客厅里有了永玉先生为从文先生贺寿送的一幅画)于有市有价的画家而言,索画便是要钱,是轻易不能为的。
不意就在第一次见面后不久,我就收到了永厚先生寄来送我的两幅画作。一幅题为《庚午记事》,一幅则取材于唐代诗人刘叉故事。画面除了极简约的人物写意外,便是满幅见缝插针的题跋。《庚午记事》图写老妪乳子,跋文则叙画思之缘起,中涉大哥赠渐江实体乳子图、梦见苏小小秒变罗丹笔下老娼妇及心中感念诸事。叙刘叉故事一幅,跋文则为:
“一条万古水,向我手中流,临行泻赠君,勿薄细碎仇。刘叉向以侠义自诩,曾不视天下负已者为仇。此赠剑诗抑骂人不倒,杀人不绝,自作下高楼之云梯乎?虽然,丈夫失志于三姑六婆,何恨!”
画属写意,书用行草,文取古体,且画、书、文俱佳,三者合璧,意趣横生,生面别开。
这两幅画似显示出永厚先生绘画一以贯之的风格。永厚先生之画属典型的文人画。“标举‘士气’‘逸气’,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并重视文学修养”,在这诸方面,永厚先生的画与传统文人画根连枝接。但有两点,又有别于传统文人画。
一是在他的笔下,少见山水、花鸟、竹木,而以人物画为主,且多取材于野史、笔记、神话、小说、典故,或暗藏机锋,或蕴含哲思,或满纸谐趣,且多关乎世道人性,并文、书与画互为主、宾,究竟是画还是文并书,于读者而言,常常是仁智互见;其二,是他决不避世。
就在我与他第一次见面时,他曾向我谈及他的一幅题为《为彭、陈、贺帅造像》绘画(画面为《水浒》人物李逵手执大斧,怒目圆睁、须、发奋张,跋文为梦麟先生专为此画所作《念奴娇》词,中有“宋氏大哥,赵家皇帝,任谁弄鬼域。铁牛在此,咬牙磨斧深谷”句)的际遇:
在此画参展的一次画展上,一位曾为陈毅元帅属下的将军,在这幅画前驻足良久,心情激动,热泪盈眶。我见状,便走上前去,对将军说:“这幅画是你的了!”
画如其人。张扬人间正气,似乎是永厚先生一贯的追求。他一身名士风骨,无论对谁,决不违心附和,任何场合,遇事从不虚以委蛇。从旁人看来,永厚先生似乎有点冷面不近人情。但在实际上,永厚先生恰恰是一个性情中人,从不在人前摆名人架子。
他总是愿人示以真性情,他也必以真性情待之。在随后几年里,我曾几次与他见面。一次是在北京南二环他借用于朋友的寓所。我应同为湘西籍的作家蔡测海之请,带他去拜识永厚先生。蔡测海也是位性情中人,与永厚先生一见如故。
整整一个上午,我们一起谈文学,谈绘画,谈湘西种种,宾主皆大欢喜。其间,谈及有朋友将永厚先生赠送的画作卖掉之事,永厚先生十分洒脱,说:“赠送的画为什么不能卖?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卖时,当然可以卖!”而后诡谲一笑:“最好别掉价!”
终于到告辞的时候。永厚先生似乎意犹未尽:“别走!就住我这里。房子小,如不嫌弃,就打地铺!”
另一次是在长沙。那天,突然接到永厚先生电话,请我和孙健忠先生去长沙火宫殿见见面,一起吃个饭。我很高兴,便坐出租车赶到火宫殿,恰好健忠先生也同时到达。一进门,永厚先生便迎了上来,并伸手给我俩分别递出一个信封。我接过来,打看一看,里面装着一张百元大钞。我大惑不解,问:“这是为何?”永厚先生满面笑容:“我请你们吃饭,哪能不给车马费!”
一句话,惹得我们三人哈哈大笑起来。
1997至2007年,我连续两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每年例会,我都会去北京。在这期间,记忆中我与永厚先生,有过三次见面。
一次是在永玉先生家中。永玉先生是享誉世界的著名画家。代表团中,一些代表知道我与永玉先生相识,遂不断怂勇我带他们去通州拜访永玉先生。盛情难却,我遂打电话给永玉先生,说明其意。永玉先生慨然应允,并详细地告诉我到万荷堂的行车路线。
车到万荷堂。一下车,正碰上欧阳松、张新奇一行数人,也来拜访永玉先生。至门前,只见大门上贴有“家有恶犬,非请莫入”字样。既然已获主人应允,便心无忐忑,遂扣门、报名。永玉先生迎了出来,其身后果然跟了一群恶犬。永玉先生说:“请等等,我去拿打狗鞭,否则,我也镇不住它们!”待永玉先生拿鞭出来后,我们便紧随其后而入。
到了客厅,一行十数人围着永玉先生,相互握手、寒喧、拍照合影,好一幅群星捧月图!突然,我看见客厅侧门边,默默地站着一个老头,直如中世纪豪门里的老仆。等我仔细一看,是永厚先生!这一瞬间,我明白了:这兄弟间,已经前嫌冰释,重序兄弟之情了!我绕过众人,与永厚先生握手问候。永厚先生向我摇摇头,摆摆手,意思是别节外生枝,打断那边主客间交谈的兴头。
来客中多数是冲着永玉先生的名头而来的。而对其弟永厚先生,却所知者甚少。然而,平心而论,就其绘画成就而言,在我这个美术门外汉看来,实在是难分伯仲。永玉先生长于花卉,永厚先生则长于文人画,且二者都有着对传统的创新变法。自然,就知名度而言,弟不及兄。因此,在这场合形成的一冷一热,也就不足怪了。
但在永厚先生心里,希望的就是这一冷一热。他始终恪守着传统的礼仪:在家中,兄是主,弟是从;在人众面前,兄在前,弟在后。我常常感叹:在当今社会里,永厚先生恐怕是传统礼仪的最后一位守望者与践履者了。我曾疑心这次所见只是一种偶然。
当我将这一判断向湘西刘路平先生说起时,他为我提供了又一次证言:这兄弟俩先后几次回过凤凰,在类似场合,永厚先生也总是默默地跟在围在大哥身边的人众后面,从不越雷池一步。一次,路平先生看到永厚先生,遂过去向他问候,并随意说了一句对他的画切中肯棨的话。待人众散去后,永厚先生过来对路平先生说:“我送你一幅画!”
一次是在通州永厚先生的寓所。仍然是几位代表,听说我要去通州看望永厚先生,一并嚷着一定要带他们去。我明白,因我与永厚先生相识多年,他们无非是想借我之口,向永厚先生求画。那年正值农历猪年(2007年),永厚先生创作了一幅猪年生肖画。画面是一头神气飞扬的猪,鼻头上翻飞着一只蝴蝶,大约是取意于庄周梦蝶典故。绘画充满谐趣,又飘逸着哲思,在我的感觉里,那真是猪年的天下第一猪!
至通州后,主宾相见甚欢。临别,我开门见山地说:“这几位代表都很敬仰先生,也很喜欢你的画,总不能让他空手而归罢。”
来自湘西吉首大学的张苹英抢先说:“黄先生,今年是猪年,我属猪,就先给我吧!”
永厚先生说:“给,给,给!”
言罢,转身去书房,拿出一幅“天下第一猪”,签字,盖章,递给了张苹英。
我怕就此没有了下文,便麻着胆子说:“能不能其他几位都给一张?”
这几近强人就范。但永厚先生二话没说,再次返回书房,又拿出三幅,分送给了另外三位。
——那时,书画市场上的行情,永厚先生的画是四万多一尺。
第三次是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在一次宴会当中也曾一晤;宴会过后,也便各自散去。
2007年后,我不再是人大代表,便很少去北京;永厚先生大约年事已高,也很少再来长沙。前两年,听朋友说,他因身体欠佳,回转安徽去了。不意数月前,突然从微信朋友圈中,看到了永厚先生的噩耗。这北京的第三次相见,竟成了我与永厚先生的最后一面。
生老病死,原本人生常态,何况永厚先生仙逝时,已是九十余岁高龄。但一想起我与永厚先生生前交往的种种,他的精神人格和率真本性所赐与我的教诲和生之乐趣,便难免悲从中来。倘若永厚先生泉下有知,我真想对他说:你若再来长沙,我要请你吃饭,还会东施效颦,送上一个装有百元大钞的信封,说:“我请先生吃饭,哪能不给车马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