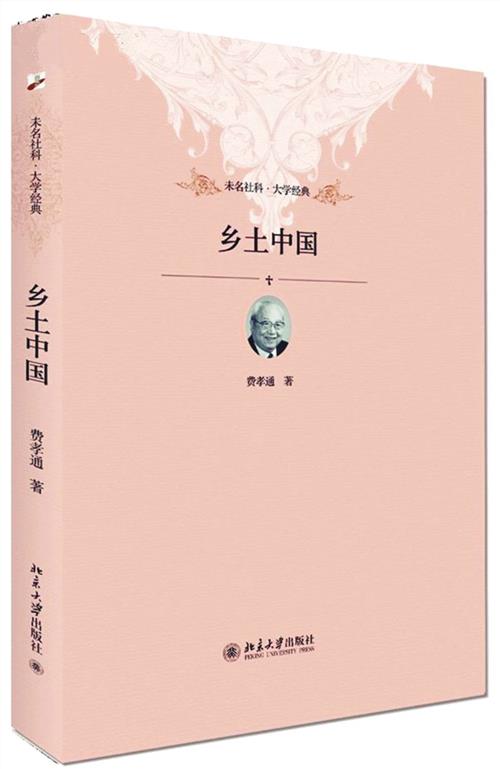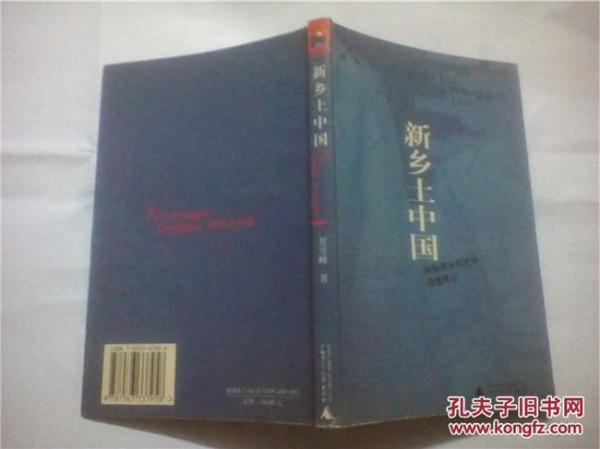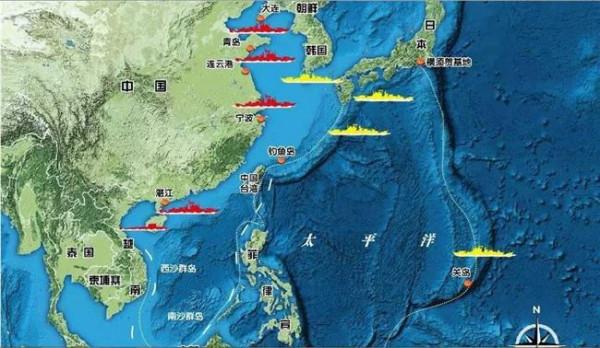费孝通差序格局 费孝通的中国老师 | 共同体精选
一九二九年夏,吴文藻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得该校“最近十年最优秀外国留学生奖”。翌年,他在美国人办在中国的燕京大学用中文讲社会学,前无古人。
大体同时,吴文藻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把学术改革推向纵深。业师开风气,费先生听到了号角。他自幼陶冶于父母为国家进步改革教育、改造社会风俗的言传身教,亦受父命熟诵苏东坡、范仲淹等名家诗文,其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无形潜入。吴文藻其人其事,他颇感亲切。

燕大四年,吴文藻家成其专业书馆,几乎读遍。费先生曾说,其社会学基本知识的基础,主要得益于这几年的阅读。
社会学欲中国化,须把中国社会的事实充实于社会学内容。为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学界讨论两种办法:一是用中国已有资料填入西方社会和人文科学理论框架;二是用当时通行于英美的“社会调查”方法描述中国社会。

吴文藻认为,无论是利用既有中国史料填充西方理论,还是借西方式样的问卷搜罗中国社会资料,都不能充分反映中国社会实际。
这时,燕京大学请来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派克(Robert E. Park)教授到校讲学。他向师生们介绍了研究者深入现实生活进行实地调查的方法。吴文藻敏锐意识到,派克讲的方法会对“社会学中国化”大有助益。

他又进一步得知,这种方法来自社会人类学,美国一批学者已用“田野调查”方法开创了美国社会学界的芝加哥学派。他决意引导学生往这个方向用功。
派克的讲学,推动了燕园学生下乡做“田野作业”。
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找到了支点,派克建立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经验可作借鉴样本。他有意借助实地调查的社区研究方法,培育人才,兴建中国社会学。

一九三三年,费先生毕业之年,他陆续发表多篇论文、译文、书评,在在是吴文藻号角的音符。吴文藻物色适合学人类学的学生,费先生入选。当时中国的大学,能提供人类学训练的,只有清华园社会学及人类学系。
吴文藻说服清华在当年招收人类学研究生。费先生考试过关后,被吴文藻特地带往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府上拜见,又经口试,终得登堂入室。后人很难想像,整个中国大陆高校人类学专业训练,曾经只有一位老师,一个学生。
一九三五年,费先生完成硕士学业。其毕业考试委员会阵容强大:陶孟和、吴文藻、吴景超、冯友兰、赵人隽、陈达、潘光旦、史禄国。费先生成绩为“上 ”。
依史禄国安排,费先生须在国内做一年实地调查,然后赴欧洲进修文化人类学。正巧,其时广西设立“研究特种民族(苗、瑶、侗、壮等)”课题,需要专业力量。
吴文藻向广西当局推荐费先生,得首脑人物李宗仁认可。
费先生由北京而广西,而江苏,而英国,得进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社会人类学顶级课堂深造。他到人类学系履行注册手续时,该系主任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正在美国参加哈佛大学三百周年校庆。吴文藻代表燕京大学出席庆典,也在现场。他与马林诺斯基晤谈,介绍中国社会学“社区研究计划”,包括费先生的课题,把学生亲手送到马林诺斯基门下。
吴文藻的学生何等福分?费先生说,吴师为学生成才,对其选什么方向、适宜到哪所学校、送到哪位名师门下,都有考虑和安排。除去专业背景、知识结构、研究能力、学术趋势等,连师徒各自的性格因素都在考虑之内。如,李安宅先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后往耶鲁大学人类学系;林耀华就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黄迪入芝加哥大学;瞿同祖跟随魏福特求学……
论著述影响,吴文藻或有不及学生处。论培养人才,吴门栋梁横陈,学生无人比肩。
中国老师(二)
潘光旦
潘光旦先生是费先生从清华开始师从的恩师。说及潘师,费先生有话 — “师从先生近四十年,比邻而居者近二十年。同遭贬批后,更日夕相处、出入相随、执疑问难、说古论今者近十年。”费先生晚年写出不少忆师念友的文章,各有精彩。
写潘师的文字尤其活现传神。太熟悉,太亲切,太知心。潘师天赋才华,梁启超由《冯小青考》一文洞察。在清华国学院“中国历史研究法”班上,梁激赏潘的“善为精密观察”,以批语鼓励:“以子之才,无论研究文学、科学,乃至从事政治,均大有成就,但切望勿如吾之泛滥。”
潘师早年教育受益家学渊源,国学根底始于庭训。又经清华预备,赴美留学,修生物学,师摩尔根,得以中西融通。
其留美之前,外文训练已相当充分。“据说他英语之熟练,发音之准确,隔室不能辨其为华人。”故虽“断一腿,成残废;而依然保送出国留学……学校和老师不忍割爱”。外语水准高,自可肩翻译大任。费先生回忆潘师文字中最精彩处,便是围绕其译事展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费先生与潘师在中央民族学院相邻而居。商务印书馆编辑拜访潘师,讨论译介西方学术名著事。潘师推荐达尔文著述,表示愿承担《人类的由来》一书之译。
费先生翻译过其英国老师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体验过译事甘苦 — “既要从人,又要化人为己,文从己出……译者要紧跟密随著者的思路和文采,不允许有半点造作和走样。凡是有含混遗漏的,就成败笔;凡是达意而不能传情的,就是次品;翻译的困难就在此,好比山要越,关关要破,无可躲避。”
潘师《人类的由来》一书译事,始于一九五六年。那一年,确定了党际关系准则,曰“政治自由,组织独立,法律地位平等”。彼时,知识分子有一小段相对平静的日子,费先生说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保存下来的潘师照片中,有一幅他和毛泽东的合影。两人对立于政协会议会场,潘师正侧面,圆头圆脸圆眼镜,谈笑风生。
毛泽东是背侧面,似是听的瞬间。此照摄于一九五一年,初见于一九九六年《老照片》第一辑。照片旁的文字说:“毛泽东与别人在一起的照片,大都位置显要,很‘露脸’,而这一张,却是个背影,且站在一旁。……从领袖谦恭的背影里,也不难看出国家爱惜人才……”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风暴殃及师生二人。费先生一度有灭顶之感,潘师泰然如初,狂潮稍息,即回归译事,认为此乃完成翻译达尔文巨著的好机会。有朋友好意提醒,即便译出,这书还会有出版可能么?潘师一笑置之。费先生从潘师定力中多有领悟,说:“他从戴上‘右派’帽子后,十年中勤勤恳恳做了两件事,一件是重读二十四史,一件就是翻译这本书。
这两件事都是耗时费日的重头工作。正需要个没有干扰,可以静心精细琢磨的环境,政治上的孤立正提供了这种条件。
”因比邻之利,费先生有机会常在潘师近旁观其译作。“每过一山,每破一关,自得之境,其乐无穷。潘先生每有得意之译,往往衔着烟斗,用他高度近视的眼睛瞪视着我,微笑不语。我知道他在邀我拍案叹服,又故意坦然无动于衷,以逗他自白。师生间常以此自娱。”
一九六六年年初,时近“文革”,山雨欲来。潘师如有感应,“干劲百倍地急忙整理抄写他业已基本译成的这部译稿。他的文章原稿都要自己誊写,蝇头小楷,句读分明。……全稿杀青。敝帚自珍,按他的习惯,必定要亲自把全稿整整齐齐地用中国的传统款式分装成册。
藏入一个红木的书匣里,搁在案头。他养神的时候,就用手摸摸这个木匣,目半闭,洋洋自得,流露出一种知我者谁的神气”。
费先生对这种斯文风范衷心仰慕,再加治学之需,往潘师家里跑得很勤。“每有疑难常常懒于去查书推敲,总是一溜烟地到隔壁去找‘活辞海’。他无论自己的工作多忙,没有不为我详细解释的,甚至常常拄着杖在书架前,摸来摸去地找书作答。这样养成了我的依赖性,当他去世后,我竟时时感到丢了拐杖似的寸步难行。”
潘师去世情节,十分悲惨。依费先生记录 — “浩劫开始。一九六六年九月一日,红卫兵一声令下,我们这些所谓‘摘帽右派’全成阶下囚。潘先生的书房卧室全部被封,被迫席地卧于厨房外的小房里。每日劳改,不因其残废而宽待。”
依潘师好友叶笃义记录 — “‘文革’开始后,我经常到他家去看他。他说他是三个 S 应付当时形势。一是 submit(服从),二是 sustain(支撑),三是 survive(生存)。……他的前列腺病症越来越严重,……医院里整天闹‘革命’,……没有人管。”
依潘师女儿潘乃穆记录 — “父亲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住院,六月一日出院回家,六月十日去世。……那天晚上,老保姆看他情况不好,急忙请费先生过来。
父亲曾经向费先生索要止痛片,费先生没有,他又要安眠药,费先生也没有。后来费先生将他拥在怀中,他逐渐停止了呼吸。”
中国老师(三)
费先生在河南新密农户询问增加收入的办法
某年春,费先生往珠江三角洲做实地考察。路过深圳,入住迎宾馆桃园。
深圳市市长到住地看望费先生,一起吃饭。席间,费先生准备了刚出版的《行行重行行续集》,签名,送给市长。
市长好学,当下翻阅。忽抬头,问:“费老,您这书里的这么多实例和数据,都是怎么来的?”
费先生说:“都是我一个一个问出来的。”
见市长神色似在说“愿闻其详”,费先生接着说 —“外出调查,我是出门找老师。要懂得中国社会,我的知识不够,可是人老了,没有学校肯收我这样的老学生了。我又需要学习,怎么办?只好出门找老师。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希望有什么样的生活,他们自己最明白。我们这些人要想知道,找他们问啊。所以说,我做调查就是出门找老师。我的老师遍天下。”
说到最后一句,费先生的笑意中,偶现几许自得。那神情,正是他回忆恩师潘光旦先生的文章里写过的 — “流露出一种知我者谁的神气。”
想起费先生访问衡水深州时一个座谈现场。
县里组织一次座谈。县委书记先讲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说到某村农民采用传统窖藏法保鲜,贮存水果,反季节销售,增加收入,费先生听出了兴趣。
书记重点讲数字,以表达政绩。费先生兴趣在别处,问书记道:“这个事,是谁最先想出来的?是怎么开始做起来的?”
书记答不出,扭身看看身后的县委、县政府职能部门领导,也没人能回答。书记圆场说:“我们会尽快了解情况,向首长汇报。”
费先生没有等汇报,当天下午去了那个村子。找到“最先想出来”办法的农民,请教了一连串问题 —你是怎么想到用这个办法的?电视里说的?听老辈人说的?
知道有这个办法后,怎么开始做起来的?
最初需要多少钱?你自己的钱够不够?
如果钱不够,用什么办法借到够用的钱?
找信用社?找亲戚朋友?
用信用社的钱,有没有利息?利息要多少?
如果找亲戚朋友,现在农村里借钱是什么规矩?还要不要保人?
如果还需要保人,保人要具备什么资格?
这些问题提出后,老乡一个接一个回答。此时,全场神情最专注、听得最用心的人,就是费先生。别人过耳,他走心。
本文选自《书生去——杂忆费孝通》一书,为“共同体别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