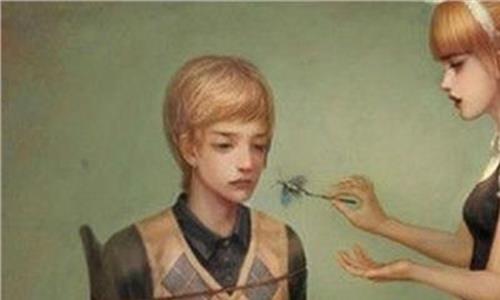冷知识科普 有哪些有意思的冷知识?
说个冷知识——震惊党和钓鱼绝不是现代的专利,而是古已有之。
先说假新闻的故事……
1899年,美国丹佛有四位隶属不同地方报纸的记者,在一个周末晚上碰巧在火车站碰头,碰面第一件事情当然免不了彼此吐苦水,抱怨各种地方小事了无新意、毫无新闻价值。他们中间有一位说:“什么路子都没有,晚点还得回去加班,活着有什么意思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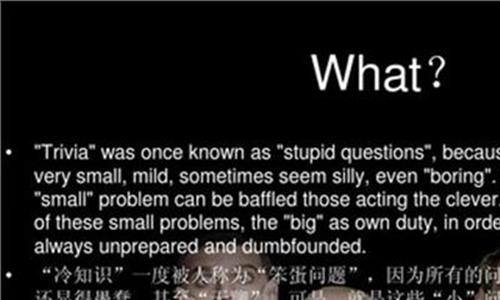
他厌世的发言,立刻得到其他人的认同。
“不如我们来做一条有趣的假新闻,不会伤害到任何人的那种新闻就没关系了吧!”
其他人思索片刻后,很快地也认同了他的提议。但是什么样的假新闻够惊世骇俗又不会伤害到任何人呢?他们想了想,原本立即想到的是假造一件绑架案,但绑架案实在太难不被马上查证出来是伪造的,所以他们决定这条“假”新闻必须发生在丹佛居民几乎不可能去但是又人尽皆知的地点。

地点选在欧洲?不行,那太容易被拆穿,何况很多美国人在欧洲经商。
非洲?美国人对非洲才没兴趣。
日本呢?感觉也不行,日本当时跟欧美国家已有很多商贸往来了。
中国?嗯!对!就决定是中国了,这个还充满神秘但又没什么人真的了解的国家。

那该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呢?
一阵争论下,他们最终决定要把号称月球上唯一能看见的人造建筑物(事实上根本看不到)——万里长城给拆了,定好即将在报纸出刊的标题。
“万里长城之末日来临!北京寻求与世界贸易! ”
报导内容大意上是说:“清朝北京当局不想继续锁国,希望能和欧美各国强国有贸易往来,所以第一枪决定要拆除境内的万里长城,公开征求各国投标兴建道路。”
报纸出刊后,立刻引起这座内陆城市居民的热烈讨论,这四位记者也沾沾自喜的享受自己“采访”到的头条新闻所带来的效应,本来以为这假新闻就该就此落幕,没想到过了几天后,美国东岸的报纸纷纷也刊出“长城要拆了”各种版本的新闻,而且报导内容都是原新闻没有出现的,甚至还有来自“中国官员证实长城要拆了”的第一手消息。
这些新闻也导致美国国内许多投资客的热烈询问,想知道要怎么样才能才能取得在中国兴建道路的承包权。更夸张的是,这则“假新闻”在几周后传到了欧洲与南美,亦在两处皆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
这则假新闻虽然引起轩然大波,但毕竟纯属虚构,很快地被隔年中国发生的更大新闻(而且是真实发生)义和团事件所压倒,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直到四十年后的1939 年,被一位词作家 Harry Lee Wilber 写成一篇文章收录进《Great Hoaxes of All Time 》书中,这则假新闻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脑海里。这篇文章声称这则假新闻引发了欧美各方人士决定前往中国寻求投资与开垦的机会,因而导致中国仇外的情绪,最终引发了隔年义和团事件。(虽然很扯,但成为美国民间著名的都市传说)
一则简短的假新闻流传了一百年,也真够冷的。
参考:
接下来我们来看钓鱼的故事……
20世纪初,蒙马特尔只是巴黎郊外的小聚落,许多一文不名的骚人墨客落居于此,夜晚聚于Lapin Agile小酒馆饮酒作乐。酒馆主人Frédé是个不太爱钱的风雅之人,既然小酒馆的酒客多为经济拮据的画家文人,就接受画家们以作品抵酒钱。
1905年,毕卡索给了他一张名为“au Lapin Agile”(Lapin Agile小酒馆)的画作,1912年,Frédé以一千法郎(当时约合20美元)卖掉(真是悲剧)。这幅画于1989年的苏士比拍卖会上以4100万美元定棰卖出,目前收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以上这些都无关紧要,重点来了。那群文艺青年中有一位作家罗兰·多热莱斯(Roland Dorgelès),并不苟同他的艺术同侪们热情拥抱的前卫画风,像立体画派(cubism)、未来派(futurism)和概念艺术(conceptual arts)等等,而评论家们对这类作品的赞扬更令他不齿,在他看来,有些评论家根本是欺世盗名的骗子。
为了取笑这些前卫画派,他和他的两名文艺界的朋友共谋了一出诡计。他们在酒店老板的驴子lolo的尾巴绑上画笔,并在画笔上抺上颜料,让lolo在小酒馆前面画画,lolo的尾巴每动一下,画布上就多了一抹颜色。为了取信,他们还请来当地官员到场见证。
1910年,一幅名为“亚德利亚海的落日”(Sunset on the Adriatic sea)的现代派画作出现在巴黎的独立画家展,作者据称是来自意大利的新锐画家波洪阿里(Joachim-Raphaël Boronali)。这幅作品果如预期般的佳评如涌,并在当时卖得400法郎的好价钱。
多热莱斯不久就在报端披露了这幅画作的始末,这幅画其实是lolo尾巴的即兴涂鸭,而新锐画家“波洪阿里”之名则是拉封丹寓言里的一头驴子“阿里波洪”(Aliboron)的倒音。
多热莱斯的爆料顿时让前卫画派和评论家们脸上无光,随后多热莱斯随后将这笔卖画所得捐给孤儿院,这幅画如今展出于巴黎郊外的一个文化中心。
以上是钓鱼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例子——
20世纪中叶,欧美乐坛开始兴起所谓“实验音乐”。创作悦耳的旋律、振奋的节奏,仿佛成了当时其他流行音乐类型(例如爵士、摇滚)的责任;“实验音乐”追求的是好听以外、更新颖的创作手法和理念。
这些“成果不可预知的实验创作”,诸如利用录音技术将声音素材结合演奏、通过《易经》卜卦编曲、甚至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声音的音乐等,虽然为音乐界催生出了许多新的想法,但每个时代都有所谓的保守人士,因此“实验音乐”被冠上类似“音乐式原子分裂(musical splitting of the atom)”的臭名,似乎是难以避免的。
就连当时的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第三频道(现在的BBC Radio 3),也为了带风向,通过广播设计了一场“实验”,但似乎并不怎么成功。
1959年夏天,德国作曲家施托克豪森发表了他的第九号作品——为打击乐手独奏所作的《循环》(Zyklus),并且获得广大的好评。根据美国历史学家Michael L. Kurtz的说法,“这首乐曲带动了为打击乐创作的风气。”
施托克豪森擅长的领域是“电子音乐”和“概率音乐”,后来都被归类于“实验音乐”的不同流派。而那首看了乐谱也是黑人问号的《循环》,其实代表着整首乐曲是首尾相连的;打击乐手可以从乐谱上的任何一个段落开始、并决定往左或往右演奏。这些设计的确符合“概率音乐”所强调的偶然性,由于不同演奏者就会演奏出不同的结果,不知道的人听下来就好像在乱打一样。
在这首《循环》获得成功之后,1961年六月,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第三频道的播报员Alvar Lidell在节目中播出了一首曲目:波兰作曲家皮托·扎克 (Piotr Zak) 的《为磁带与打击乐所作的常动曲 (Mobile for Tape and Percussion)》。
播报员解释这次的播音,是全国首播:
1939年出生于波兰的作曲家皮托·扎克,现在居住在德国。他早年的作品相当保守,但这几年开始受到约翰·凯吉和施托克豪森的影响。这首《为磁带与打击乐所作的常动曲》,创作于1960年的5月至9月之间,通过精确而复杂的乐曲架构,给予演奏者相当大的即兴空间。
虽然没有明说,不过这首作品的确和施托克豪森的《循环》有着类似的风格。然而,当时的乐评家对这首乐曲,却丝毫不留情面。当代乐评家Rollo Myers在《听者》杂志上发表评论,认为BBC播放这样的曲目,是相当严重的决策性错误:“根本不可能把这个称为音乐!”
而另一位乐评家Donald Mitchell则是在《每日电报》中指名道姓:扎克先生的这些打击乐、磁带、口哨声……相当无耻,它们不是音乐的根本。这让之后播出的莫札特《小夜曲》情何以堪?
或许“实验音乐”受到乐评家严厉批评并不奇怪,但真正让众人跌破眼镜的,则是BBC第三频道在两个月之后发表的声明:波兰作曲家皮托·扎克,其实根本没这个人!
原来,《为磁带与打击乐所作的常动曲》是BBC制作人Hans Keller和Susan Bradshaw的作品。他们通过剪接技术,将毫无意义的声响结合在一起。
至于目的,BBC发言人坚称,为的不是欺骗大众,而是一次实验。后来,BBC 甚至制作了广播纪录片“皮托·扎克的奇妙事件”,向大众解释:
“实验音乐”如此晦涩难懂,和胡乱敲打的录音带没有差别。我们只希望那些乐评上钩,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会对这些胡乱敲打的声音,给予高度评价。
多么心术不正的理由……
也还好当时的乐评确实给了这首乐曲严厉的评论,《为磁带与打击乐所作的常动曲》没有达到类似驴子尾巴名画的批判效果,也没有对当时的音乐发展造成太大影响。后来,“皮托·扎克的奇妙事件”被视为二十世纪最知名的音乐骗局之一。
隔年7月,一位属名彼托·扎克 (Pjotr Zak,拼法略有不同)的七百字乐评,被刊登在“音乐时报”杂志上。评论的对象,是施托克豪森当时(首演后隔了三年)才出版的《循环》总谱——
“这份乐谱,根本无法告诉我们即兴演奏,和类似我的《常动曲》实验有什么不同。…… 反而是我的《常动曲》影响了施托克豪森,让他后来才决定出版乐谱。当然,施托克豪森是不会轻易承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