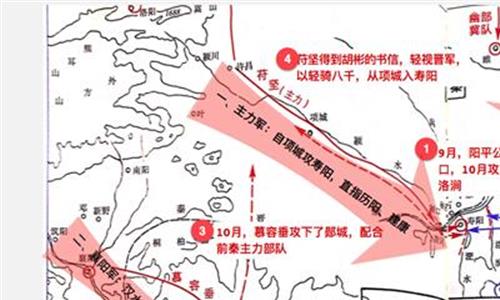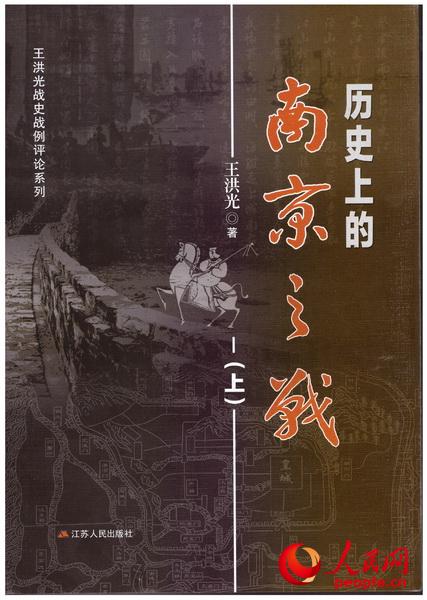涿鹿之战过程 汉简 | 历史上的“涿鹿之战”发生在哪里?
李学勤、刘国忠在《简帛学:古代文史研究的新增长点》(《光明日报》2016、6、29)中指出:“简帛资料的大量发现,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当今文史研究的面貌,简帛资料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和崭新的视觉,来重新研究中国辉煌的古代文明。”事实确实如此。

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
1972年四月间,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一号和二号汉墓里,发现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大批竹简和竹简残片。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云:“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

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孙武与孔子差不多同时代,时值春秋末期。《孙子兵法》亦当成书于这个时期。孙膑与孙武相去一百多年,为战国时齐人,约与商鞅、孟子同时期。《孙膑兵法》亦应成书于这个时期。

据《孙子兵法新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孙子》注释小组,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载: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下编:
《黄帝伐赤帝》云:“孙子曰:{黄帝南伐赤帝,至于□□},战于反山之原,右阴,顺术,倍(背)冲,大灭有之。{□年}休民,□毂,赦罪。东伐□帝,至于襄平,战于平□,{右阴},顺术,倍(背)冲,大灭{有之。□}年休民,□榖,赦罪。
北伐黑帝,至于武隧,{战于□□,右阴,顺术,倍冲,大灭有之。□年休民,□榖,赦罪}。西伐白帝,至于武刚,战于{□□,右阴,顺术,倍冲,大有灭}之。已胜四帝,大有天下,暴者……以利天下,天下四面归之。”
另据《孙膑兵法》(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文物出版社1975年出版)载:{见威王}云:“昔者,神戎战斧遂;黄帝战蜀禄”。
关于这两段佚文,吴九龙先生在其所著《孙子校译》中说:“从字体来看,其抄写年代当在秦到文景时期。”这样汉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抄写年代,比早期著录《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史记》、《叙录》和《汉书·艺文志》,都要早几十年至二百余年。可知汉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更接近本人的手定本,同时也使我们第一次得知西汉早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二书,是如何记述所谓“涿鹿之战”的。
一、所谓“涿鹿之战”是西汉以来牵强附会出现的谬传
与上述两段佚文有关的记述,在传世文献中亦有所见,现摘录如下:
《逸周书·尝麦解》与:“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一作‘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孔子家语·五帝德》云:黄帝“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克之。”
《左传·僖二十五年》云:“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
《山海经·大荒北经》云:“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庄子·盗跖》云:“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吕氏春秋·荡兵》云:“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故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
《大戴礼记·五帝德》云:“孔子曰:‘教熊罴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
《贾子新书·益壤》云:“炎帝无道,黄帝伐之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又《贾子新书·制不定》云:“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
《淮南子·兵略训》云:“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故黄帝战于涿鹿之野”。
《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
《战国策·秦策》云:“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
另外《管子·五行》、《韩非子·十过》等篇也谈到黄帝与蚩尤等,但非战争内容,与上述两段佚文关系不大,故不予摘录。
从上述传世文献记述中可以看出,谈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的有《逸周书·尝麦解》、《庄子·盗跖》、《史记·五帝本纪》和《战国策·秦策》,而《贾子新书》两段引文和《淮南子·兵略训》说的是黄帝与炎帝战于涿鹿,究竟炎帝与蚩尤是什么关系,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作讨论。我们重点研究的是结合佚文和传世记述探讨所谓“涿鹿之战”的地望。
1、我在拙作《黄帝的都城究竟在哪里?》中已经谈到,《逸周书·尝麦解》按李学勤先生的说法,作于西周中期(《新探古史传说时代·前言》);《庄子》成书与战国中晚期。它们在谈到“涿鹿”时分别比西汉初设置涿鹿县早六百余年和近百年,它们的作者生前怎么会知道将来有一个西汉王朝要设置涿鹿县呢?这种提法的依据和出处还需进一步考证。
2、《孙膑兵法》佚文云:“黄帝战蜀禄。”该书的注云:“蜀禄,即涿鹿,地名。《战国策·秦策》:‘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从佚文来看,战国时称“蜀禄”而非涿鹿。我们知道,“涿”字出现很早,甲骨文、金文和秦代印文都有“涿”字;“鹿”字也是一样,甲骨文、金文以及春秋石鼓文、竹简文都多次出现。
那么为什么孙膑不用“涿鹿”而用“蜀禄”呢?为什么西汉早期汉简本《孙膑兵法》不用“涿鹿”而用“蜀禄”呢?很明显在战国到西汉初尚未置涿鹿县以前就没有“涿鹿”这个地名,虽然有了“涿”和“鹿”这两个字,但还没有连用。
《逸周书·尝麦解》及《庄子·盗跖》所谓的“涿鹿”,则是在传世的过程中因汉代设置涿鹿县后人为的窜乱附会。《贾子新书》成书于文景以后,《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死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征和二年司马迁死前不久所写的《报任安书》来看,《史记》似乎还没有全部完成,《太史公自序》所说的“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大概仍是指草稿而言,到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
贾谊、司马迁或褚少孙受西汉初设置“涿鹿县”的影响采用了“涿鹿”一说。《战国策》是刘向校订和整理于西汉末年,该书就更是“人云亦云”了。
3、本来东汉服虔在给《汉书》作音义的时明确了《史记》以来的关于“涿鹿之战”的地望,《史记·集解》云:“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这实际上是告诉人们,虽然西汉有了“涿鹿县”,但与《孙膑兵法》所说的“蜀禄”是两回事,不要把“涿鹿县”误认为是黄帝战蚩尤的地点,既更正了《史记》所谓“涿鹿之战”的错误,也纠正了《逸周书·尝麦解》、《庄子·盗跖》流传中出现的错误。
然而三国时张晏注释《汉书》时则说:“涿鹿在上谷”。
这样黄帝与蚩尤作战的地点,司马迁或褚少孙始误之,张晏以正为错,以错为正又误之,司马彪等继误之,遂成千年疑案。张晏注释《汉书》早有学者指出问题不少,缺乏严肃精神。例如对于《汉书·司马迁传》的一些注释,就遭到宋代吕祖谦、清代王鸣盛等人的讥评,不赘言。
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曾十分中肯的说过:“黄帝邑于涿鹿之河。服虔云:涿鹿,山名,在涿郡(今河北涿县)。张晏谓在上谷(皆见《集解》)。盖因《汉志》上谷有涿鹿县云然。窃疑服虔说为是也”(《中国民族史》第10页)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说,黄帝与蚩尤之战的地望与涿鹿县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二者毫不相干。之所以出现“涿鹿之战”的误解,“盖因《汉志》上谷有涿鹿县云然”,纯属牵强附会,郢书燕说。之所以出现这种错误,不是偶然的。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传世先秦文献,几乎都是汉代复制的。因为经过秦火之后生活到汉代的知识分子,为恢复先秦文献作了大量的复制工作。应当说汉学为传承中华文明作出了伟大贡献,但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许多错讹,所谓“涿鹿之战”就是其中一例。
所以在研究传世文献时,需要首先做好辩伪工作。在这个问题上首先是服虔及吕思勉先生等真可谓是独具慧眼,辩伪存真。为了防止出现这类穿凿附会的错误,张孟伦先生特别提倡班固著《汉书》自作注的作法。
他说“作者不自作注,而让后人去解释,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还举例朱熹,就因为“‘春王正月’四个字之有各家不同的解说:‘某所以都不敢信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还魂亲说出’”(《汉书·地理志》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价值》)。
二、关于两段佚文中“武隧”、“斧遂”、“蜀禄”所蕴含的历史信息
《孙子兵法》佚文{黄帝伐赤帝}由于损泐严重,影响我们对文义的理解。据《吕氏春秋》十二月五行相配表和《礼记·月令》可知有“五方帝”之说,即东方帝太昊,西方帝少昊,南方帝炎帝,北方帝颛顼,中央帝黄帝。五方又配五色,《周礼·春官·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郑玄注曰:“五帝,苍(青)曰灵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黄曰含枢纽,黄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纪,颛顼食焉。
”如果说郑玄的解释不够通俗,《史记·封禅书》就好理解多了,该书云:汉高祖“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祀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祀’。
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帝,何也?’莫知其说。
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其实,五方帝、五色帝、五行帝的说法很早。《孔子家语·五帝》载孔子言:“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
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昊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昊配金,颛顼配水。”孔子说他是从老子那里听说的,老子曾经做过周王室的图书管理工作,可以推知周代的图书典籍中应有这类记载。
孙武与孔子生活在同时期,对于当时流行的五方帝、五色帝、五行帝之说自然有所闻了,只不过孙武作为一名军事家,是从军事的角度谈论黄帝与青白赤黑四帝的战争关系的,言不离本行。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佚文所说的青白赤黑帝是一个通用的名词,并非都确指那些人,而是对众多称帝者的泛称,是春秋战国人对正式朝代形成之前漫长古史的统称。《荀子·非相》云:“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久故也……传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
”《韩诗外传集释(卷三)》也说:“夫传者久则愈略,近则愈详。略则举大,近则举细。故愚者闻其大不知其细,闻其细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表明了两千多年前古人对远古五帝时期的茫昧无稽心情,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只能利用考古工作和简帛研究逐渐予以揭示。
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佚文《黄帝伐赤帝》中有“北伐黑帝,至于武隧”,“隧”通“遂”,“武隧”即今徐水区遂城。《括地志·易州》云:“遂城县,战国时武遂城也”。《元和郡县图志·河北道三》云:“战国时武遂城也,赵将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即此也。”
佚文《孙膑兵法·{见威王}》云:“神戎战斧遂,黄帝战蜀禄”。本书注“戎”为“农”,注“斧遂,或作补遂”。我认为注“斧”为“补”不准确,应为“釜”。一是“釜”、“斧”二字音同;二是“釜”、“斧”二字金文、战国简帛文字头相同,整个字形相似,可能是误写;三是“补”的原字为“補”,《说文·衣部》:“補,完衣也,从衣,甫声。
”据此“補”上古音读作“甫”声,故“斧”、“釜”、“补”三字音同。按古音韵学“同音相通”的原则,“斧遂”、“补遂”都应释为“釜遂”,则“神戎伐斧遂”即指为釜山、遂城一带。
再说佚文中“蜀禄”应是“濁禄”的简写,这在古文中并不少见。濁禄应为濁鹿山,也就是服虔所说的“濁鹿,山名,在涿郡。”《古本竹书纪年》也有记载:“燕人伐赵,围濁鹿,赵武灵王及代人救濁鹿。”如上所说,濁鹿应处在燕赵之间的西部山区,为双方争夺的关塞,《唐土名胜图会·涿州》云:“濁鹿山在州西十五里。
”实际距釜山、遂城不远。《名胜志》云:“黄帝蚩尤战于涿,即此。”佚文“黄帝伐蜀(濁)禄”所指就在这个地方。由此我们推定《逸周书·尝麦解》所云:“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这场战争的地点文献记载是“蜀禄”,其实际的地名为“濁鹿,”到汉代错误地附会为“涿鹿”,其真实地望为釜山、遂城附近,就是说神农和黄帝结成联盟与蚩尤作战的战场就在釜山、遂城一带,釜山、遂城在汉代属涿郡。
于此,我们通过对上述两段佚文的申解,正本清源,更正纠谬,澄清了千年疑案。做学问,特别是注解传疏,应秉“为学当有益于天下之公心。”否则就会弄成如洪容斋所说“以故解释传疏,自汉至今,不可概举,至有一字而数说者”(《容斋续笔·义理之说无穷》)。
三、釜遂发达的粟作农业是黄帝族团战胜蚩尤族团的经济基础
徐水县为什么有地称釜、遂呢?这是由史前这一带的社会发展状况和自然环境特点所决定的。“遂”字的金文字形从足、从
(坠落),本意是边做边播撒种子之意。《汉书·食货志上》云:“辟土植榖曰农”,表明这里是原始农业的发源地。“釜”的原字为“鬴”,其有二解,一是炊具锅,原为“鬴”说明最早的锅不是金属的;二是古代的容量单位,六斗四升为一釜。
其用途都与粮食有关,与粟作农业有关。徐水一带原始农业起源早已被考古所证明,距遂城十几里的南庄头新石器时期发现了植物的种子和茎、杆、枝叶,加工粮食的石磨盘、磨棒,证明这里的原始农业已经有万余年的历史。
遗址共发现了50多块陶片,由于烧制火候低,质地极疏松,难于复原完整的器物,不好找出陶釜。但发现了红烧土的灶塘,必然有与之配套的陶釜,南庄头人才能把加工好的粟米煮食。比南庄头遗址稍晚的并据此不远的北福地新石器时期遗址,出土的陶器典型器就是园底釜,也证明釜遂一带陶釜是最早出现的,确切的说陶釜是由南庄头人以及他们的后裔发明烧制的。
由于先有了陶釜的器型,以器比山,以山像物才会有“釜山”之名。可以肯定地说,“釜山”之名,是在南庄头人烧制陶釜以后才有其名的。
从釜遂一带的自然条件来说,属于太行山以东平原区,是由古黄河和易水河、徐河交汇的洪积、冲击而成,海拔在30米左右,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温度适宜,是农业生产条件最好的地带。由于有了优越的自然条件,也促使南庄头人较之其他地方更早的由采集渔猎发明了原始农业、制陶业和家畜饲养业。
北与釜遂毗邻的督亢,之所以在战国时期以“膏腴之地”著称于世,应该与南庄头人在这一地区世世代代创新发展、繁衍生息有直接关系,或者说督亢的富饶是南庄头人所创造的社会文明的积淀和传承。
按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论是历史社会还是史前社会,无论是阶级战争还是氏族之间的族团战争,经济物质基础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对此已经有了朴素的认识,他在《货殖列传》中说:“《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
’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民归之,襁至而辐凑。
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有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此外《平准书》又说道:“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河渠书》还说:“(郑国)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些精彩文字都明确地指出了经济发展在国富兵强、攻伐战胜中的基础作用,对我们研究问题是个很好的启发。
由此我们不难想到,佚文中所说黄帝“已胜四帝,大有天下”,“天下四面归之”正是有富饶的釜遂做基础,黄帝胜神农、擒蚩尤的原因也正是有釜遂沃野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保证了屡战屡胜。
我们常说经济是基础,有的地方热衷于“打造三祖文化,”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史念海先生早就说过,由碣石山向西南沿今燕山南麓,至于恒山之下,再西至汾水上源,循吕梁山而至龙门为农耕区与畜牧区的分界线(《河山集?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
试问,“三祖”部族为什么偏偏选择在蔓草疾风的游猎区生活?黄帝怎么在这里“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怎么“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怎么实现“土德之瑞”?这是令人琢磨不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