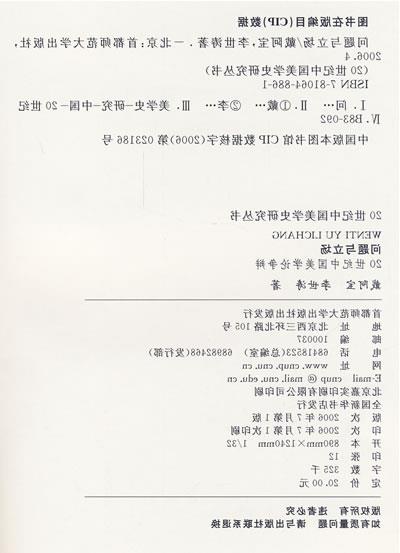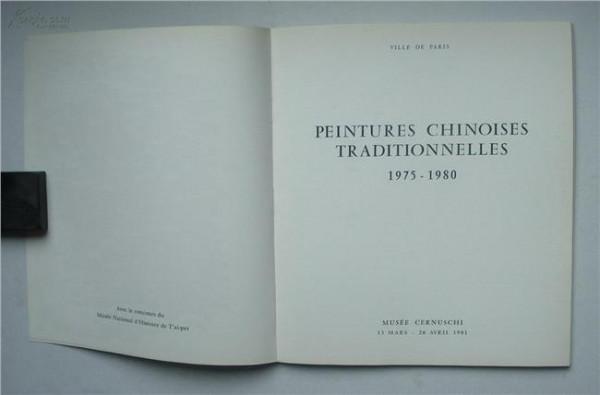李慎之批毛新宇 何家栋:20世纪中国的“新道统”——从梁启超到李慎之
三年前,我在喻希来《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欲把握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风貌,需全面了解它的政治家、学问家、企业家、军事家、艺术家,但提纲挈领的还是认识它的思想家。人们以往习惯于从孙中山(或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个“政统”的角度解析20世纪的中国,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增补由思想家们所构成的“道统”。

从某种意义上说,道统的重要性还在政统之上。如果在总结一个世纪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21世纪中国继续现代化、与世界接轨、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大方向,就需要确认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新道统”。

在笔者看来,其主链应是梁启超——胡适——顾准。再延续下去就涉及到活着的人,尽管会有争议,窃以为李慎之还是众多具有候选资格的思想家中领先的一人。
在90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义大旗,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在不久前怀念慎之的文章中,我更加明确地指出:新道统的主链应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一些朋友写信给我,希望对此略加申说。
在早期文明中,政统与道统是合二而一的,张灏称之为“宇宙王制”(cosmologicalkingship)。在这种体制之下,国王是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是人王也是法王。公元前十世纪至二世纪间(所谓“枢轴时代”),在以色列、希腊、波斯、印度和中国各地几乎同时出现以具有“超越”意识为特征的宗教与哲学运动,包括西方的希腊哲学、犹太教(和随后的基督教),印度的耆那教与佛教,以及中国的儒教等等。
这种超越内化的思想在政治文化中造成了二元权威中心的契机。
这个政治文化的契机在西方文明后来的历史演变中是逐渐实现了。但是这一契机在中国文明中的发展很不稳定,时隐时现,若断若续,以致二元权威的思想一直未能在思想传统中畅发与确立。
在汉代“独尊儒术”后形成的国家宗教,教主并不是孔子及其传人而是历代君王。一直要到韩愈、二程、朱熹,才逐渐把所谓“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的“道统”彰显出来。道统首先是思想学术的统系和精粹,认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所表达的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把道统从政统、皇统中独立出来甚至凌驾于后者之上,就可以用“圣人之言”来拒绝和匡正当朝执权柄者的悖谬之言和随意之政。
道统也体现为古来贤君良臣面临各种情形时的行为举止,构成一种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即使贵为天子,也必须从小学习和终生遵循。这样,道统一方面为政统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撑,另一方面对于皇权专制也构成一定的制衡。国民党把政统和道统系于孙中山一身,林彪给毛泽东加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顶冠冕,是对历史的一种反动、对思想的一种扼杀,是现代专制主义后来居上、达到极致的一种表现。
当中国文明的道统成型之际,西方文明的道统再次发生分裂。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西方的道统分化为教统和学统,教统掌控大众伦理,学统传承精英文化。而20世纪初的所谓“儒教”,仍是一种教统与学统的混合物,袁世凯、康有为、陈焕章等人把孔教国教化的企图,引起了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反弹,结果不仅没有把孔孟之道宗教化,连它的学统地位也被从根本上动摇了。
我在这里所说的新道统,主要是指新学统,至于中国的教统是否需要接续、或者再造、或者引进,或者扬弃,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同样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康有为想要在“创造性阐释”基础上复兴孔教的努力没有成功,反而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戴季陶把孙中山装扮成“继往开来,道统直承孔子”,结果却疏远了五四以后的中国知识青年,断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基业。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新学统对旧学统的替代,标志着中国传统思想的断裂与中国思想传统的蜕变。
新学统虽然还是用中国的语言文字来表达,也尽量用中国的典故事例来阐释,但其内涵思想的渊源却是西学。新学统影响所及,首先是精英文化或者说上层文化,至于中国的大众文化或者说下层文化,还有着根深蒂固的前“枢轴时代”巫史传统的遗存。
它们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譬如说20世纪初的义和拳情结,“文革”中的政治癫狂与社会迷乱,以及最近SARS疫情引发的种种民间反应。
新学统的核心话语是现代化,包括国家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而分歧最多、障碍最大的则是政治领域的现代化即民主化。如果我们把关注点聚焦在现代化尤其是民主化上,中国新道统(新学统)的鼻祖只能是梁启超。无论是同代人的严复,还是晚一辈的陈独秀、胡适、毛泽东,对此都是认可的。
梁启超不仅是将民族、国家、国民等新术语引入中国思想界的第一人,也是宪政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等新观念的权威阐释者。他不仅比其他人做了更多的引进和宣传工作,而且从现在的眼光看,他依然是这些思想在中国的“正宗”。
譬如说民族主义。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是基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也叫做“国族主义”。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国族主义势必是一种“大民族主义”。“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
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起初是“驱逐鞑虏”、“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的“小民族主义”。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开始向梁启超靠拢,从种族主义转向国族主义,从“小民族主义”转向“大民族主义”,但还留下一条民族同化的尾巴。此时他鼓吹:“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
”用现在的话来说,梁启超倡导的“大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孙中山心目中的“大民族”是同化了各少数民族的单一大汉族国家。又譬如说民主主义。
不管梁启超一生思想怎样多变,他在民国建立后始终没有离开民主、自由、人权的思想底线,而且是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清室复辟、再造共和的主要功臣。严复虽然是最先在中国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思想家,但晚年思想趋于保守,成为“筹安会”罪魁之首。
在孙中山晚年诠释的三民主义中,自由主义受到抨击,民权主义受到“先知先觉”论、“国民资格”论(接受国民党训政并宣誓效忠党义后才能获得国民资格)的阉割,由此开启了“党在国上”、“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
梁启超的某些洞见,为他的后辈所忽视或反对,因而直到今天,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他在《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中说:“讲到国计民生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的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
但我的意见,提倡这主义,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至于实行的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
……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欧洲面临的迫切问题是改善多数劳动者的地位,中国的迫切问题则是使多数人民变成劳动者,因为中国人十之八九尚处于“欲求一职业以维持生命,且不可得”的境地,国民的多数属于游民阶层。
如何使游民变成劳动者呢?“舍生产事业发达外,其道无由。生产事业发达,……我之需要品,不必仰给于伦敦、纽约、巴黎、大阪,然后我多数人之职业,不致为伦敦、纽约、巴黎、大阪之劳动者所夺,然后我之游民可以减少,而我之劳动阶级可以成立。
劳动阶级成立,然后社会运动得有主体,而新社会可以出现。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逾越之阶段,殆如此。”至于资本主义之流弊,可以“矫正态度与疏泄态度”加以克服。
前者即“奖诱资本家,唤起其觉悟,使常顾及劳动者之利益,以缓和劳资两级之距离”;后者即“设法使生产事业,不必专倚赖资本家之手,徐图蜕变为社会共同事业”。经过七十多年的历史检验,胡绳在去世前才对上述观点作出了比较公允的评价。可以说梁启超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见解,还在陈独秀与胡适之上;直到1990年代,吴敬琏和邓小平才接续了梁启超的思想。
从21世纪回溯以往,自然不难发现梁启超在一个世纪前的思想缺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受性别、阶级、学识限制的公民普选权还没有在欧美国家普及,因而梁启超在那时鼓吹的还不是“大众民主”而是“小众民主”,即以伸张“绅权”为目标的“宪政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积极推动“国民运动”,扩展了政治参与主体的范围,但出于对民初党争的失望,他不是用国民运动来辅助政党政治、议会政治,而是试图用前者来取代后者。他在研究系刊物《改造》的发刊词中宣称,“同人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五四以后中国政治的走向。
严复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时认为,为了“愈愚、疗贫、起弱”,避免在国际生存竞争中弱肉强食的遭遇,可以不考虑伦理道德的问题,“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然而,以“天演论”为思想依据,从政治功用和工具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宪政、民主,很容易因为一时的成败得失而发生动摇。
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都强调要以伦理学而不是进化论作为民主主义的思想根基。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认为,仅仅引进共和立宪的制度而不引进“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的“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那样的“伪立宪”就成了专制政府的“装饰品”。
“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胡适则鼓吹“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
胡适主张把宪政民主的政治诉求建立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他倡导“使各人自己充分发展”为“人类功业最高一层”的“易卜生主义”,或者叫做“健全的个人主义”。他把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分为三种: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Egoism),其性质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独善的个人主义,不满意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
针对独善的个人主义——“新村运动”鼓吹者所说的“改造社会要从改造个人做起”,胡适指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根本观念是: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从改造这些造成社会,造成个人的种种势力做起;改造社会就是改造个人;这种改造一定是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这种改造是要奋斗的,对于反对改造的旧势力,应该作正当的奋斗,不可退缩。
针对国家主义者所鼓吹的“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胡适向青年呼吁:“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种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少年的朋友们,不要笑这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思想!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
可惜的是,胡适的上述观点在五四以后就已经被认为是“落伍”甚至“反动”的思想。20世纪中国思想界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便是“趋新”,不肯老老实实地、脚踏实地地争取“一尺一步的改造”,总想来一个“大跃进”,“迎头赶上”欧美国家。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胡适的一班朋友倒向了共产国际和无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在欧洲崛起,胡适的另一班朋友又倒向了“德意模式”和“新式独裁”。惟有胡适,是上个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中国最坚定地维护宪政、民主、自由、人权的思想家。
他既反对孙中山、蒋介石的“训政”、“党治”,也反对陈独秀、瞿秋白的“阶级斗争”和“苏维埃政权”。陈独秀曾是最负盛名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帅,“德先生”最热烈的鼓吹者,但他后来走了很长的一段弯路,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到托洛茨基主义,晚年才回到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来。很多人推崇鲁迅,认为鲁迅的思想高于胡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