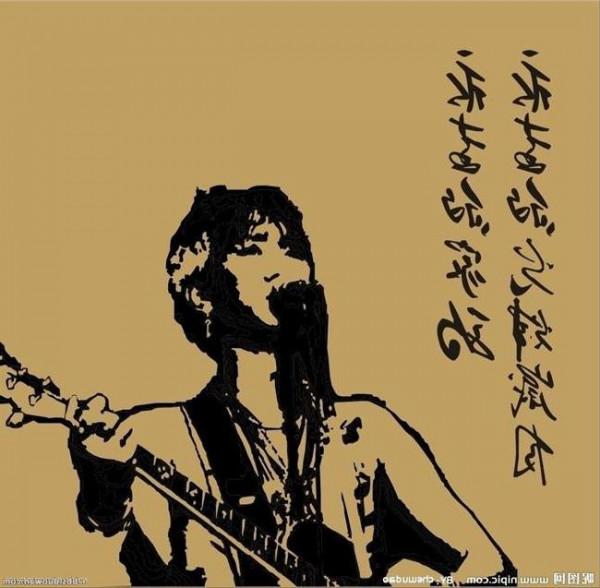朱哲琴现在去哪里了 朱哲琴:音乐的消失是因为没有了灵魂
4年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邀请朱哲琴担任“世界看见”亲善大使,发起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亲善行动。希望通过收集整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和手工艺,推动“中国制造”。朱哲琴最初的想法是,邀请一些国际上比较知名的民间音乐制作人把采集的中国民间音乐进行二次加工混音,通过国际唱片公司发行,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

但是当她踏上采风之旅,最初的想法也慢慢改变了,她没有想到会遇到诸多困难。4年后,当唱片《月出》制作完毕,她才知道,这个最初并没有列入到她工作计划的项目,改变了她很多想法。她也从一直以来的歌手角色转变成了制作人,过去接触民族音乐是为了制作一张唱片,现在让她意识到这是一种责任。

从1992年的《黄孩子》开始,朱哲琴就开始走向一条与众不同的音乐道路,她与何训田合作,尝试将当代音乐与民族民间音乐结合,创作中国式的NewAge音乐(新世纪音乐),朱哲琴凭借自己的演唱天赋,成了何训田作品的最佳演绎者。

这次“世界看见”采风之旅,朱哲琴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歌者,她必须把采集整理的音乐素材制作出一张唱片,通过唱片传递出一种可能,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音乐文化,而不是简单地完成过去那种纯粹的演唱工作。

虽然朱哲琴过去一直游弋于民族音乐和现代音乐之中,但是她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深入、系统地去感受民族音乐,这也让她慢慢明白此行的意义。她说:“中国早就应该有人,有更多的人,围绕自己的文化传统出发,真真正正沉浸进去做一些事,所以我不觉得自己是带个头,而是觉得我应该在这里。我想现在这个东西做完,包括这些素材还是可以找别的人来做,甚至我们希望会有更大、更多的动作,把这些音乐提供给中国的年轻一代。”
朱哲琴对自己能从民族音乐的原点出发完成长达4年的音乐之旅感到欣慰。过去,民族音乐是她音乐旅程的一条线,但是一条虚线,这次是一条真正的实线。她说:“其实在主题上,我也一直在不同的时代做一些不同的探索,我也希望在这条路上去做这么一件事,而且多走一步。
我觉得光为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这张唱片最初的出发点也不是为我做的,这张唱片关乎传统,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面向未来。我自己的目标是这样的。做这个题材,人们很本能地就会把传统的东西、民族的东西回到10年、20年、50年之前,但是我觉得那应该是80年代、90年代的命题,现在最重要的命题是怎么把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联系上。
新鲜的血液是决定它方向最重要的、最诚实的命脉,所以我合作的对象一边是传统,一边是一批新的年轻人,他们都在30岁以下。
他们把这些音乐带到另一个时空,这是我的一个心愿。我作为一个老人,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我有过去跟何训田这些大师的合作经验和经历,但是这张唱片在未来怎么在这些人心中去成长很关键。所以它的格局就出来了,一边是很纯粹的、原汁原味的采样和音乐,另外一边是这批做西洋音乐的年轻人。”
朱哲琴放弃请国际知名音乐制作人做采样混音,资金问题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她逐渐意识到,这样的做法在今天已经不新鲜了,更重要的是必须从自己的文化根源出发去做一些事情。她说:“我觉得中国非常缺少学习本土文化从新起点开始创作的一批人,非常缺。
就拿我自己做例子,我完成《黄孩子》、《阿姐鼓》这批东西后就停下来了,停下来的原因是我意识到如果去创新,从哪里创新?我觉得对自己的文化不了解,你怎么做原创?90年代比见识,比如谁有很敏锐的国际触觉,找到一些新的方法。
光有这些还不够。当然这是一个起点,很好,但是更要往前走。你看看日本、欧洲的文化,都是对自己的文化有很深的亲近、了解,再蜕变出新的东西来,它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文化的流。
我觉得现在中国正处在这个潮流方向中,但是要出来东西,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诚实的事,你没有这个底蕴,你做的东西就是还不够。印度在全球有很多知名音乐家,他们都是对自己血液里的东西很清楚,然后再去国际化,这样人家会尊重你,因为你是有根源的。
我这个采集之旅,原来是文化保护,亲善大使的行为,但对我个人来讲是一次真正的学习过程,这个太重要了。你真的在感受了解中国的东西,包括手工艺的采集,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在自己的文化面前就是文盲,你文盲怎么再往前面走呢?可能有些有限的源动力、敏感的触觉,对音乐的感受可以发挥一阵,但是再往下呢,你就弹尽粮绝了。”
在旁人看来,朱哲琴过去20多年的音乐生涯达到了中国当代音乐家少有能企及的艺术成就,在中国的音乐版图上坚守住一块能称之为艺术的阵地。但她能意识到从这块阵地给她带来的光环中退出来,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以及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之间的差距,这确实难得。
与朱哲琴同时代出道的歌手现在还活跃的已经没有几个了,她之所以能有这么长跨度的艺术生命力,是因为她走了一条与常人不同的路。她说:“我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我的成长经历正是中国变迁的时代,我基本上经历了所有的变化。
我3岁开始学样板戏,慢慢到学习古典音乐,再到流行歌曲,到‘新空气’乐队的时候唱自己的歌、自己创作,然后再到国际化。我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创造者。现在,到了中国特别期待原创音乐的时候,尤其在这个模仿泛滥、复制泛滥的时代。但我觉得偏偏这个时候,我要做这个事情。”
“我是一个很希望有希望的人,我觉得永远有希望在,而且让你看见。”朱哲琴说。在经历了4年多后,终于把唱片做出来了。她希望通过身体力行,能让别人去参考和借鉴。她说:“首先,它是一个双CD,把最原始的采样和依据采样创作出来的东西放在一起对比;其次,这些民族文化的基因,每一首歌曲都是通过原来的采样或者数个采样发展出来的,整个音乐里既有传统的基因,又是一个新的东西。
我们去看传统的时候,老是觉得它是属于过去的。
我不能说它不对,从某个角度上是对的,但它是有局限性的。而我们这次的命题,一方面是要保存这些,更大的方向是我们怎么把它们带到现在和未来的时空,让这些文化真的活下去,真的去形成文化线条,生生不息地参与、影响、互动,成为一个中国自己文化的脉络。所以通过这些创作,我觉得它是成功的。”
朱哲琴是一个很随性的人,她最初也没想过把唱歌当成自己的事业,甚至她在与何训田合作之后还想过去当导游,那样可以看到更多美丽的风景。何训田说她天赋这么好,不唱歌太可惜了,与何训田合作也是以何训田为主导,朱哲琴只是在扮演做水到渠成的事情。但这次不同,她从一个配角变成了主角,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
“在采集之旅的过程中,每到一处,听到那些音乐,就会让我想太多,让我很感动。他们没有受过音乐教育和训练,为什么他们一唱出来就那么美?那些音乐为什么那么灿烂?这太真实了!所以在制作唱片的时候,我不希望以某个作曲家、艺术家的角度去做这些东西,我觉得欢乐就很欢乐,这种东西经得起时间考验。
这个行程教会我太多东西,你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就是不归路,你一定要把它做出来。这就是我的想法。所有这1000多首采样我们以后会捐赠出来,或者通过不同的人、不同的平台带到更远,这是我们的希望。原来是我们去保护这些东西,后来我发现,其实当代文化传承在一个危机中,我觉得我们应该在一起互相协作、互相扶持,才会走出一条新路。”
在采集之旅还未开始时,朱哲琴就面临一个问题,原来计划投资的一家公司决定放弃投资。可能在投资方看来,这类民族文化保护项目不会有期待中的商业回报,所以,最初的费用只能由朱哲琴自己掏钱。后来,中国银行出了一部分资金,让采集之旅得以继续。
在途中遇到的问题往往出现在录音环节上,这些音乐录音必须还原到最原始的状态,比如田间、山坡。朱哲琴说:“在村子里录音时,经常有鸡叫鸭叫。鸡鸭叫都不是问题,但是比如拖拉机、发电机的声音就非常要命,因为是工业声音,所以就要去到远一点的山坡上。
在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长调之乡,我们在蒙古包里录音,但是现在内蒙古人冬天都住楼了,蒙古包就在楼边上,电器声又很容易录进去,所以我们后来把一个60年代的蒙古包移到草场远一点的地方,拉上一根电缆,我们所有的录音都要回到他们原来的生活场景中。包括我们所有的图片记录、资料记录,对每一个音乐传承人有肖像拍摄。这些东西留下来,在未来就是这个时期的活的音乐地图和实况。”
采集过程遇到最多的情况是当地文化馆的人把他们直接带到旅游区,让他们去“欣赏”“旅游民歌”。这经常浪费不少时间,这些从事当地文化工作的人已经失去了对民族文化的判断意识。朱哲琴说:“为什么现在人不喜欢民歌?就是因为我们让人接受的都是伪民歌,都是赝品。
”在黔东南采风时,当地县长很热心地把他们带到了苗寨旅游区,最后他们只好放弃黔东南,去了另一个地方。等团队离开后,县长又给朱哲琴打电话,说找到了他们要的民歌。
采集团队重新返回,终于录到了想要的东西。朱哲琴说:“在《月出》这首歌里,你能听出蜜蜂翅膀颤动的声音。他们的歌声唱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苗族音乐就是有生命的源动力,原始荷尔蒙基因的味道。这个东西可能在别的文化里找不到,只有在这种野性的、自由的文化中才能找到,这种文化造就了一种对原始和野性的保护。
我觉得特别棒,只有在非洲曾经听过比较接近这样的东西。每个地方都有他们自己的核,我们都找到了。我们回来后,面对这么一大堆素材,最后整理素材也是一个困难。”
后期素材整理和音乐合成对朱哲琴来说是更大的挑战,究竟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些素材整理出一个完整的音乐形态,着实让她费了不少心思。面对这些采样,她能回忆起来的就是在采集过程中的一些场景,这些场景在不断触动她,让她慢慢清晰起来,中国文化的多元造就了每一处文化都有自己的“核”。
她回忆说:“在喜马拉雅山的定日县协格尔乡,一个歌手在我面前弹琴唱歌,就是一个单音在弹,他面无表情,目空一切,没有任何传达的意图,这种感受我觉得真是太好了,他不是一个表演者。后来问了一下歌词,就是对自然的崇敬,就是雪山永远都那么壮美。那个时刻,一下子就印在我的脑子里面。”
后期制作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录音合成。朱哲琴在和母带混音师冯炜国谈到母带处理时说:“我绝对不追求一张发烧唱片,这不是我的目的,我要做音乐,要把这张唱片的制作特点传递出去,这是最重要的。传递这些采样的时候,应该是淋漓尽致的,我不希望把采样变成录音室音乐。
”朱哲琴说:“这就给制作带来很大的难度,因为它一直在采样和录音室中穿越。当时我们在北京做过一段,觉得不对,又找一个香港的录音师做了几首,出来质量好一些,但是传达出的音乐又不一样,像流行曲了。
后来我们又找苏前,他以前和我合作过,但是他一做就变成录音室音乐,少了很多东西,他觉得很多音质有问题,就会拿掉。我又不想做成《阿姐鼓》那样的东西。后来我们的编曲蒙柯卓兰又找了一个做民乐比较不错的录音师,做完了还是不满意。
又找到一位年轻的录音师范郡哲,拿到母带的时候,我们觉得还是不够,因为有些曲子一首里有好多不同采样,而不同采样都带着不同的采样环境。冯炜国跟我说,唱片的最大问题是采样的空间互相抵消这个关系怎么解决。我说我要体现这些原初的基因的美,这些基因的美其实是带着土壤来的,这是我们最珍贵的地方。”
朱哲琴在回忆她制作这张唱片的时候说:“当我一个人走进工作室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特别欣喜,我觉得我回零了。过去做唱片,有唱片公司投入制作,有完整的团队来帮助你,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音乐回到了一个心愿——就是你想做这些事。
当音乐成了你自己的事情时,就像回到了十几、二十来岁的一个喜欢音乐的年轻人的状态,什么都没有,就是喜欢。这个让我挺感动的,它让我有很强的生命力。我没有任何挣扎,我这儿没有选择题,只有肯定句:我要做,我要怎么做,我能怎么做。
在现在音乐这么低迷的情况下,音乐家需要通过创作过程让人感觉到音乐还有生命,这个太重要了。音乐的消失是因为没有了灵魂,没有音乐家而消失,而我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灵魂。
不单是我,蒙柯卓兰他们那群年轻人也是,他们找到了那种灵魂,所以他们现在像雨后春笋般成立乐团,又在演出,其实不是为了任何唱片公司商业的目的,就为喜欢这个。这就是一种原创的精神。我们这个小团队,找到了这个东西,这个太珍贵了。它是一种清流,而且我希望它能影响很多年轻的来者。”









![>朱哲琴新乐府[WAV/百度网盘]](https://pic.bilezu.com/upload/9/68/9684d9522a1e431fd15310975ecbc6b0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