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哲琴我是歌手 歌手朱哲琴:西藏让我找到自己的声音
到目前为止,朱哲琴和她的音乐采风小组已经走了贵州、云南、内蒙古、西藏、新疆,采访大量当地民间艺术家,录制了五百多首民间歌曲(乐曲)。按照她原来的计划,在考察工作结束以后,朱哲琴将出版两张CD,一张是她采集来的音乐原样,另一张是请西方著名音乐家以采样为基础重新编写的作品。

本文为朱哲琴专访下。
张英:这次音乐采风的成功说明时候能够出来?
朱哲琴:还在素材整理阶段,我需要足够的时间,对音乐素材进行整理,我可能会出版两张CD,一个是是我们采分录制到的原始的素材;一个是我邀请世界知名音乐家利用这些素材做出的音乐。

张英:尝试音乐的多种可能。
朱哲琴:实际上我对传统文化有两个观念。一个是保护态度,一定要求真求实。现在很多东西说是原生态,其实有很多伪民俗,伪原生态的东西。我们这次的行程很认真,从影像、文字、图片、声音,多做实地的详尽的记录。

同时,这些传统应该介入到当代的创作,影响当代人的生活。传承如果只是在一个僵硬的博物馆,或者是一个被人为隔绝的一个区域里面去延续的话,这个传承本身是一个死的传承。
所以我做这个事情是两个观念,一个是保护,一个是怎么激活,怎样让这些东西介入当代、影响当代。西方的古典音乐由教堂音乐慢慢发展出来,意大利美声唱法是民歌发展出来的,美国的摇滚是从黑人种棉花的布鲁斯音乐发展出来。如果一个文化和他前面的传统完全没有关系,这个文化本身就有问题的。

回到中国,中国在世界上经济崛起,人们在期待中国发出什么声音,中国现在有西方的爵士、古典、美声、摇滚乐,中国人总结的声音呢?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古老的历史,就只有这些外来的东西吗?
要提中国当代声音,可能我们更应该、更多的目光聚焦在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上。这不是说把民俗拿出来,模仿一通,再去拷贝,或者说是去做一个赝品。这些民族的音乐是怎么样在血液里影响我们的?如何让这些元素介入我们的时代脉搏,发出我们的声音,代表我的背景、代表我的文化,这是我现在一直在思考的。
张英:目前,这些民族音乐正在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朱哲琴:原来我觉得也就是一个自生自灭,从2003年开始,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工作以后,各个区域确实开始了保护和摸底,很多地方对自己区域的音乐进行记录和整理。
但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怎么去有效保护和和传承这些音乐。因为这些民间的音乐家就是耕田或者是放牛的,从小有人教给他,或者家里这样传下来唱,完全是即兴和天然的。高兴了就唱,不高兴了就不唱,每一天的身体状况、他的喜好,都在变化。
所以,我们到每个地方,都鼓励这些老的一定要带年轻人,把自己学会的音乐一定要教会年轻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对活的音乐传承进行保护,但具体实施计划比较困难。
西藏让我找到自己的声音
张英:拿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过的像你音乐学院的同学或者是一起获奖的歌手那样,呆在北京进入文艺院团或者签约音像公司当歌手呢?
朱哲琴:参加完大奖赛,我是有可能成为其他的那样的歌手留在北京,参加各种晚会,出专辑,全国巡回演出,这跟原来我音乐的理想差很多。当时我很清醒,那些东西不能满足我,那个方向不是我希望的。
我从小看过的艺术著作,听过的很棒的音乐,我觉得他们是我的坐标。我应该创造出来很棒的音乐。比如我去西安那个厂矿演出,那种噪音、那种音响,那个环境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即使名誉再大、出场费再多、场次再满。很多人都是靠这个赚钱,在这个行业里支撑着。但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种折磨。
张英:你的坐标是哪些人?
朱哲琴:我原来看的一些小说,听过一些古典的音乐,那才是真正的作品。我看过《卡拉马佐夫兄弟》,我知道文学真正有高度的东西在哪里:陀思妥也夫斯基把自己放在所有角色的背后,去谈论一个事情。在我原来接触的所有作品,都是作者我要通过这个人在讲述什么。
其实一个艺术也好,对一个事情认知的角度也好,他是可以有很多种,他不是只有单一的标准,到西藏也给我这样的启发。人生有很多种活法,有很多种价值观,唱歌不是 为而来比赛、赚钱、出名,唱歌本身就很愉快,让你的精神很快乐。我们今天一群人约到你们家,听你唱的好,就很高兴。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兑换成一个有形有价值的东西的。
我到西藏的时候,遇到许多藏民、喇嘛,在路上转经的人,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每天能吃多少东西,穿多少,然后住在多少个房子里。我听到的音乐,非常质朴,真挚动人,没有任何价值,却让人心灵震撼。
张英:何训田在你的音乐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朱哲琴:歌手大奖赛完了以后,我去四川跟随何先生学习音乐。不是学习怎么唱歌,而是学习音乐欣赏。他给我听很多中外的、古典的、现代的、流行的、当代的、民间的音乐,让我充分吸取不同的音乐土壤的营养。
当时很多人纳闷,这个人一得奖,怎么就不见了?好多朋友都给我写信说,你怎么这么早就过隐居生活?逃到你理想的伊甸园,和现实不发生联系。但在我看来完全相反,我是在实践我的人生和梦想。
我七岁就在儿童合唱团,什么古典的、和声、合唱作品,从童年就开始有认知,更早的时候听样板戏、中国传统戏曲,我那时可以模仿《红灯记》里大段大段的唱段,十几岁的时候,流行音乐进入中国,我们开始模仿邓丽君,再过来就是欧美音乐,认识何训田以后,我开始听到民间音乐的声音,极大的丰富了我的音乐视野,后来我去阿坝、云南、四川、西藏旅行,后来是全世界。
当我听了那么多的声音的时候,我想发出自己的声音,然后就做了《黄孩子》,到《阿姐鼓》的时候,我的声音才真正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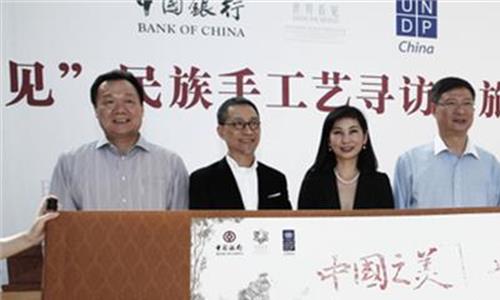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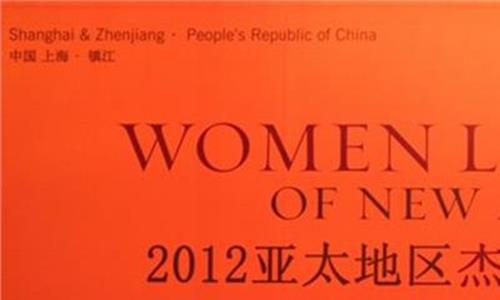









![>朱哲琴新乐府[WAV/百度网盘]](https://pic.bilezu.com/upload/9/68/9684d9522a1e431fd15310975ecbc6b0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