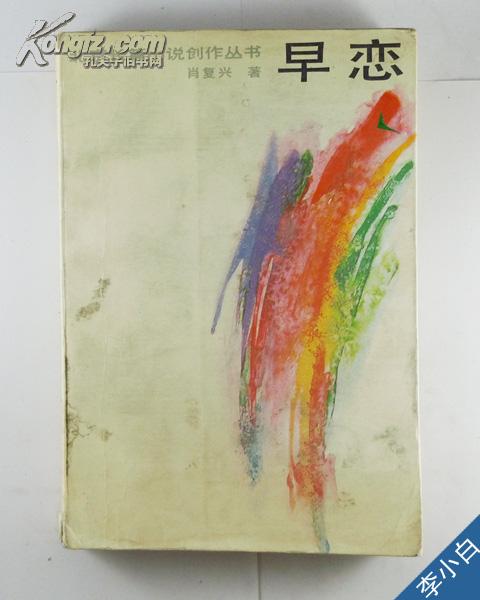早恋肖复兴 我和小尹在猪号的日子 | 肖复兴
冬天猪号的记忆,对于我,总是和那口井,和那口锅,和小尹相连在一起的。
那口井,在猪号前面不远,我最怵头上那口井。冬天,井沿结起厚厚的冰如同火山口,又滑又高,爬到井口已经很困难,偏偏打水时又常常把水桶掉进井里。那是我最尴尬的时刻。重新把掉下去的水桶捞上来,要用一个大铁钩子钩住水桶,井很深,挂钩子的井绳子飘飘忽忽的,不听你使唤,要想捞上水桶,比鱼儿上钩还难。那时,我干活儿真的挺笨的。
每逢这时候,小尹总会出现在我的身后,轻轻地说句:我来吧。好像他未卜先知,早知道我又把水桶掉进井里。他双手攥着井绳,左右摆动几下,井绳悠悠的像蛇一样蠕动着,铁钩就已经听话地钩住了水桶。每次小尹帮我把桶捞上来,我的尴尬面对的常常是他抖动结满冰霜胡茬上宽厚的笑。
我是秋天得罪了队上的头头,被发配到猪号干活儿的,和他住在猪号的一间小屋里,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他不爱讲话,我们两人基本上是白天干活儿,晚上睡觉,谁也没什么多余的话。好像在此之前演出的都是哑剧。冬天到了,天寒地冻了,大雪飘落了,井口结冰了,水桶掉进井里了,人物才开始张口讲话了,仿佛才活了起来。
在我的印象中,小尹的胸前总是系着一个围裙,那围裙很长,几乎拖到了地。他走路像是没有腿,只有上半身,飘浮在半空中。
北大荒的冬天,人们都在屋里猫冬。猪号的外面,就是荒原,显得越发的荒凉。到了夜晚,除了风的呼啸和猪的哼哼叫声,没有一点儿声响,更有一种远离万丈红尘之外的感觉。收工之后,我一般都是闷头在屋子里看书,写东西,打发时间,沉浸在万里荒原之外的想入非非中。我睡得晚,小尹睡得早,我俩相安无事。那时,还没有电灯,一盏马灯如豆,万里荒原似海,心像是漂泊无根的小船,不知哪里可以拢岸。这是那时我写下的拙劣诗句。
我们住的小屋,和烀猪食大屋是连在一起的,中间只隔着一道木门。烀猪食的大锅硕大无比,猪食是一直在锅里煮着,灶火一直不灭。小尹一觉起来,看马灯还亮着,披衣下炕,跑出小屋。我以为他是跑到外面撒尿,他回来的时候总会带来一块热乎乎的烤南瓜,塞在我手里,让我趁热吃。他是早在烀猪食的大柴灶里塞进了南瓜,那种只有北大荒才有的南瓜,烤得喷香,面面的,甜丝丝的,味道很像北京的沙瓤白薯。
几乎每天帮我捞水桶和烤南瓜,让我对小尹心存感激。谁能够几乎每天都这样想着你,帮着你,默默地伸出温暖的援手,像伸出一根缆绳,挽住你已经漂荡不定东倒西歪不知所往的小船?那一刻,我觉得万里荒原不那么荒凉,一灯如豆也有了跳动的生气。
我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注意到他,开始和他交谈的。他是从山东跑到北大荒的,那时管这样的人叫作盲流,从最开始开发大兴岛住地窨子的时候,他就在我们二队干活儿了,便也就从盲流转正,成了农场正式的农工。他的年龄比我大许多,那时得有三十多了。
叫他小尹,是因为他长得个矮,其貌不扬。小尹命苦,儿子才一岁多一点儿,他老婆带着儿子突然不辞而别,甩下他像一条孤零零的老狗。在农村,老爷们儿甩女人可以看作是长脸的事,被女人甩掉是被人看不起的,脸一下子掉到地面上了。
一气之下,他只身闯关东来到北大荒。开始在场院里干活,有好事的泼辣女人们常拿他寻开心,甚至当众解开他的裤带,说是看看他里面那玩意儿是不是有毛病,那女人才甩了他。他不吭声,死死地抓住裤子。拽不下来他的裤子,她们就往他的裤裆里灌满鼓囊囊的豆子。和我被发配到猪号来不一样,他是主动离开了场院,要求到猪号来的,可以只伺候猪八戒,不和那么多人打交道。
当我听他讲述了他的经历之后,非常后悔刚到猪号时对他的怠慢。每个人都是一本书,打开来,一页页翻开之后,才会发现每个人活着的不容易,都很挣扎,都有一种难言的苦楚,蛇一样时不时会爬出来咬噬自己的心。我很惭愧,只是顾影自怜,舔着自己的伤口,没有发现睡在身边的小尹比我还要不幸。
小尹是个扎嘴的葫芦,话都憋在心里头,能够对我讲述他的伤心往事,很不容易。讲完这番话之后,我们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下子亲近了许多,即使晚上还像以前一样,彼此一句话都不讲,但已经心思相通,知道了彼此心里想的是什么,要说的是什么。
他还是早早地睡下,我还是点着马灯写字看书,一觉醒来,他还是起来,跑到外面撒泡尿回来,给我从灶火里拨出一块烫手的南瓜。有时候,他跑回来,躺在炕上睡不着,就抽一袋关东烟,问我一句:炝不炝你?我说句:你抽你的,不碍事!然后,不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着了,就是他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睡着。
日后,我常常想起在猪号冬天的那些日子。在那些夜晚,即使朔风呼啸,大雪弥漫,都是万籁俱寂,静得你只能够感受到夜的深处和荒原深处隐隐的律动,像是呼吸一样轻微而均匀,烟一样笼罩在你的心头,仿佛有女人的手心或鼻息似的,柔和地抚摩着你,吹拂着你,呵气如兰的那种感觉,让你哪怕是没有笼头的野马一样的心,也俯首帖耳地安静了下来。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再也没有度过如同在猪号里那样安静的日子。我才发现,喧嚣其实是容易的,安静却是很难的,那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作用。
我也常常想起关东烟的味道。我不抽烟,但那关东烟的味道,因为觉得说不上好闻,而是一种让我难忘的味道,只要一想起它的味道,就立刻把我拽回到猪号的日子,小尹,便系着拖地的围裙,浮现在我的身边。
很久很久以后,我听正读高一的儿子在房间里大声高唱一首叫作《味道》的流行歌曲,唱到这样几句歌词的时候:我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的袜子,和你手指淡淡烟草味道……不知怎么搞的,心里一热,很有些感动,禁不住想起了小尹。
想起小尹,还不仅是他手指间关东烟浓烈呛人的味道,还有那一年刚刚开春时节他从草垫子里抱回来的一只兔子,是一只受伤的野兔。那时,积雪还没有化干净,春寒料峭,风还很硬。那只受伤的兔子,躺在猪号外面的荒草丛中,灰色的毛间有发黑的血迹。
小尹放猪的时候,发现了它,把它抱了回来,在猪号烀猪食的大屋里,用破木板替它搭了个窝。每天,小尹有活儿干了,找些冻白菜叶子和胡萝卜,或者从猪食里拨拉出来兔子能吃的玩意儿喂它,甚至拿来南瓜喂它,甭管吃不吃,有了小尹操不完的心和好多说不出的乐。
每天夜里起来跑到外面撒完尿回来,也不会忘记看看他宝贝的兔子。屋子很大,又暖和,野兔的伤很快就好了,能够满屋子跑,追着小尹玩了。那是小尹最开心的时候。
大约有一个来月之后,我记得正是最后一场埋汰雪下过并化干净之后,那天清早起来,小尹照旧先去看他的宝贝兔子。那只野兔已经跑了,屋里屋外,我陪小尹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不知它是怎么拱开了大门,跑出去的。小尹自责说都怪自己,肯定是半夜跑出去撒尿回来没把门关好!然后,他又自我宽慰说,早晚得走,这儿又不是它的家!尽管这样说,我看得出来,小尹心里有点儿伤感,挺舍不得的。
1974年,我离开北大荒的时候,小尹还在猪号喂猪。1982年,我大学毕业重返北大荒,回到队里,找不到猪号了,那里只剩下一片茂密的野草。我很想念分别8年的小尹,打听他的下落,知道他到场部打更去了。我折回场部找他,他家的门敞开着,好像知道我要来似的。我大叫一声:“小尹!”出门是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对我说:“我爹不在。”
我几乎是愣在那里,小尹的儿子找到了!这个比小尹高出一头的小伙子,真的就是他的儿子吗?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告诉小伙子,我是他爸爸一起在二队猪号干活儿的好朋友,让他爸回来晚上到场部的招待所找我,说我很想念他。当我说完这番话以后,我发现,小伙子无动于衷,愣愣站在那里,好像他也不相信出现在他面前的我,真的是他爸爸的朋友。
天还没擦黑,小尹就跑到招待所找到我。那一晚,因为第二天我就要离开大农场,陆陆续续来叙旧告别的人很多,他一直默默地坐在旁边,等别人走尽,只剩下我们两人,他也站起来,说:“快歇着吧,你也怪累的了。”我说我不累,使劲儿拉他,他还是转身走出屋。
我跟着他一起走出屋,递给他一包从北京带来的香烟。他说他不抽,我以为他抽惯了关东烟,不习惯这种香烟。一问,才知道他已经戒烟了。儿子来找到他之后,他就戒烟了。“省点儿钱,给他娶媳妇用。”说完这话,他笑了,笑得有些腼腆,像个小孩子。
我又问他:“媳妇呢?怎么没跟孩子一起来?”他说:“儿子来了就行了!”
那一晚,星星特别的多,低垂着,仿佛一伸手就能摸得到。站在明亮的星空下,很想和他多待一会儿,问问他新的生活。他却一再催促我回屋,不断说着同样的话:“快歇着吧……”然后,他转身离开了。望着消失在灿烂星光月下他瘦小的身影,我心里替他高兴,他说得也对,毕竟儿子来了,父子团圆了,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亲骨肉。有了年轻的儿子,再衰老的父亲也有了依托和支撑,日后的日子会逐步好起来的。
回到屋里,我才发现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大海碗,一看,是几块烤地瓜,尽管已经凉了,在灯光下,油光发亮,闪动着黄中泛红的光斑,散发着丝丝的甜味儿。还是记忆中的颜色和味道。
我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见到他的最后一面。
2004年,我重返大兴岛,打听小尹的消息,乡亲告诉我,他早已去世多年。他死得非常惨,是死在自家的炕上两天之后,才被人发现。
我问他的儿子呢?
他的儿子早奔到外面挣钱去了!
乡亲说完,和我一起运气。要这个儿子有什么用,跟他妈妈一样,拔腿就走,就那么不管不顾,把小尹像条丧家犬一样孤零零地抛在家里。
有时,我会想,小尹还真不如一直在喂猪,起码还有一群猪八戒能够陪着他。
如今站在大兴岛上,我再也找不到小尹了。就像再也找不到小尹为我烤的南瓜,再也找不到猪号的那口井,再也找不到猪号,再也找不到那些风雪呼啸或星光灿烂的夜晚,再也找不到那些春寒料峭或埋汰雪尽后的野兔子一样。
小尹!猪号里跟我睡在一铺热炕上的朋友小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