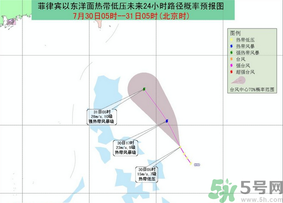伍秉鉴广州的家在哪里 夹缝中的奇葩 ——广州十三行富商伍秉鉴
事情还得从好几百年前的大明说起。1368年,逆袭成功的草根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其时,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政权仍然面临强劲挑战:北面是退到蒙古高原的残元势力,东部沿海是张士诚和方国珍的残部以及不时骚袭的倭寇。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像个尽职的老农一样守护着自家的园子:北面,他一面修整长城,一面调驻了大量军队;东南沿海,为切断张、方残部与大陆的联系,他将沿海居民内迁,片板不许下海。在朱元璋的海禁铁幕下,唐宋时曾创造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海外贸易几乎禁绝——仅作为一种礼仪象征的朝贡贸易,还被允许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说句题外话,一直困扰明朝的倭寇,其中不乏武装贸易的商人,所以倭寇兴起的一大原因,就是海禁。

清承明制,二者同为内敛的、内省的、内陆的帝国。清朝立国之初,郑氏割据台湾,不时骚扰大陆,为此,明朝的海禁政策持续执行。直到清军攻占台湾之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一代英主康熙认为“海洋贸易有益于生民”,方下旨解除海禁。次年,清政府先后设立粤、闽、浙、江四大海关,作为外商来华贸易的指定地点。

四大海关中,以地处广州的粤海关最为重要,其余三大海关监督皆由地方官兼任,只有粤海关监督系专任,其级别与作为封疆大吏的总督和巡抚相同,直接向皇帝和户部负责。更为重要的是,广州自唐代起就是亚洲最重要的商贸大港和货物集散地,朝廷一旦开放海禁,原本处于走私状态的海上贸易成为合法,广州立时重现了唐宋时期的辉煌。

从康熙开海到四口通商结束前的175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到中国各口岸的商船共计189只,其中到广州的就有157只,占总数的83%。
其繁盛景象,明朝遗民、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有一首浅白的小诗描绘道:“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外洋。五丝八缎广丝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粤关志》则称:“东起潮州,西尽番禺,南尽琼崖,凡分三路,在在均有出海门户。”
权力和油水都极大的粤海关监督,向来由皇帝钦派,除了负责海关工作外,还有另外两项重要职掌:一是监视地方大员,二是为皇宫购买来自西洋的各种玩艺儿。缺少监督的权力和恣意妄为的合法伤害权,使得以粤海关监督为首的海关官员对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洋商土商大肆敲诈勒索。
不堪其苦的洋商开始把商船发往宁波——另一用意则是为了开辟更为广阔的市场。如此一来,到达广州的商船急剧减少,海关官员的灰色收入与海关税收均呈直线下降。为此,有关官员向乾隆提出,将宁波的关税翻一番,以便使洋商“自愿”留在广州。
乾隆皇帝的反应出人意料:他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旨,洋船“只许在广州收泊交易”。这道上谕,意味着大清帝国从“四口通商”变为“一口通商”。
此后,英国派出洪任辉前往天津,通过行贿的方式,把一纸诉状送至乾隆御前。洪仁辉在诉状中控诉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等人敲诈勒索,希望天朝改革贸易制度,保护正常贸易。乾隆阅罢,大为恼怒——他恼怒的并非官员贪墨敛财,而是这个非我族类的夷人,竟找到中国人帮他写状纸,此中的隐情必定是朝廷十分警惕的“中外勾结”。
更何况,在乾隆的观念里,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之所以四口通商,不过是皇恩浩荡,念在西洋各国没有天朝特产的茶叶、瓷器和丝绸,才恩加体恤,准许通商。
现在你们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吹毛求疵,成何体统?恼怒的乾隆下旨将洪任辉押往澳门关押,至于那个帮写状纸的中国人,下场是斩首示众。
洪任辉的几条罪名里,最奇怪的一条是:擅自学习汉语。乾隆的逻辑也看似理直气壮:夷人一旦会说汉语,他们就有可能和汉人一起,图谋不轨。这种简单的推理,在特殊的年代里,却少有人质疑其荒谬——“文革”时期,不是也有不少会说外语的中国人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吗?
四口变一口,对外商来说是灾难,对广州来说却是天赐良机。正因为有了一口通商,才有了后来十三行的辉煌。粤海关既是位高权重的天朝第一海关,同时也是唯一的海关,按理应该对前来贸易的外商进行管理,但在天朝的意识形态里,官员亲自与夷人打交道,是严重违反礼仪和祖制之事,因而,作为天朝和外商之间中介与桥梁的行商便不可或缺。
过去和现在我们常说“十三行”,似乎充当中介和桥梁的行商是固定的13家,其实不然,行商多时有26家,少时只有4家。“十三行”这一称谓起源于明朝,这说明尽管有朱元璋严酷的海禁政策,但到了他的子孙掌权时,地下或半地下的海外贸易仍不绝如缕——铁幕一旦违反世道人心,必然会被撕开若干大洞。
西方人将行商形象地称为“清朝管理外国人的警察”,那么,行商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首先,行商是唯一得到清政府认可的外贸代理商。至于谁有资格,政府亦有明文规定,必须是“身家殷实,赀财素裕”者。但作为一种潜规则,仅仅拥有大量财产还不够格,必须花费20万两银子才能买到这份执照。
作为钦定的外贸代理商,行商控制了广州——也意味着就是整个天朝——的外贸,洋商从行外的中国人手里买来的货物,如不通过行商就无法运出,行商则从他们经手的每一批货物中,提取一部分手续费作报酬,并用他们的名义报关;其次,行商负责向粤海关纳清相关货物的进出口关税;第三,行商是外商和朝廷之间的中间人,“凡夷人具禀时间,应一概由洋商代为据情转禀,不必自具禀词”;第四,充当洋商的担保人。
朝廷规定,每一个外商自登岸起,就必须找一家行商充当担保人,担保人对洋商的一切行为负有连带责任。美国人亨特在《广州番鬼录》里说:“行商控制了广州口岸全部的对外贸易,每年总额达数百万元,受益固多,责任亦重。外国商船或其代理人如果违犯了‘规条’,俱由行商负责……由于这种关系,我们戏称他们为‘我们的假教父’。”
很显然,责任重大的行商从事的是一门超级垄断生意,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生意不可能不火。在风急浪高的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航道上,西方各国的商船竞相驶往迢遥的中国广州。
作为朝贡贸易向自由贸易的转折,行商制度原本乃非驴非马的怪物,就像《清代十三行纪略》所说的那样:“开海贸易之后,原来接待外国贡使的怀远驿是不能接待外国商人的,按清代礼部贡典,欧洲商人在礼部贡典无名,又无金叶文书,不能用官方形式接待,只能投居洋行商人的行栈或租行栈等办法来解决。
于是,广州的洋行商人纷纷在广州城西的珠江边被称为十三行的地方建房租屋,供外国商人居停贸易。外国商人称之为商馆,中国人称之为夷馆。”
商馆也好,夷馆也罢,总之,在朝廷既要保留一个同洋人贸易的窗口,又要顾及天朝脸面的前提下,在广州城外的珠江边,出现了一排排整齐漂亮的房舍。这里华洋杂处,人声鼎沸,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可以说,十三行就是大清帝国辟出的“经济特区”。
在大清的财政收入中,关税是仅次于地丁和盐税之外的第三大税种,而粤海关的税收,占了全国关税的1/4。至于来自广州的这些关税收入,其中有24%归皇室所有。从某种意义上讲,粤海关其实就是为圣上的小金库效劳的敛财部门,所以,皇帝总是派他信得过的奴才来充任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