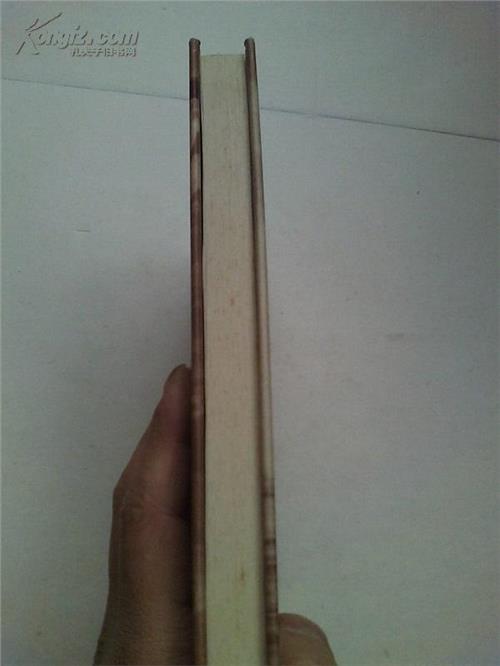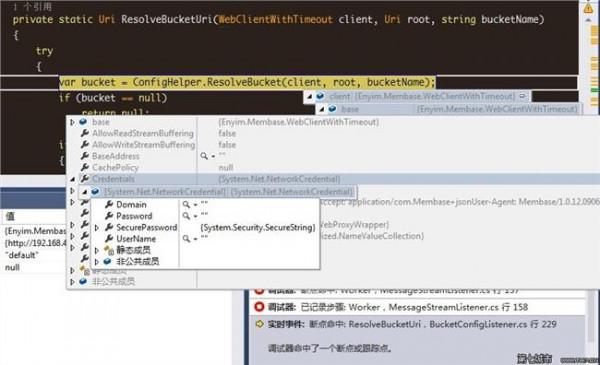余英时中国转身很难 余英时的“中国情怀”:尝侨居是山 不忍见耳
《明报月刊》要出关于”中国的情怀“专页,承编者雅意,让我参加一份。我很喜欢”中国的情怀“这个动人的名称。但是什么是”中国的情怀“呢?仔细一想却不好回答,因为这不是可以通过形式化、概念化的途径来解决的知识性的问题。

怀疑主义的哲学家甚至还可以问:究竟有没有”中国的情怀“呢?”中国的情怀“和其他各国的情怀到底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呢?我不想这样”煮鹤焚琴“地煞风景。我的直觉告诉我,”中国的情怀“确实是存在的一一它存在于每一个受过中国文化熏陶的人的身上。

但是这种”情怀“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却有不同的表现,因此又是无从”一言以蔽之“的。”情怀“是属于整体感受方面的事,这也许便是佛经上所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吧!
屈指算来,我住在美国的时间早已超过住在中国的时间,而且照现在流行的说法,我也只能自称”美籍华裔“。但是惭愧得很,从下意识到显意识,我至今还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后来我逐渐明白了:原来”中国人“自始即是一个文化概念,不是政治概念。而我的”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国,不是西方,虽然我对西方文化优美的一面也十分欣赏。

1978年10月,我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离出国的时间已整整29年了。从东京飞北京那几个小时,心情真是有说不出的激动。那正是我的”中国的情怀“全部流露的时刻。但是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萦回在我脑际的却是丁令威化鹤归来的神话,那时我才真正体味到”城郭如故人民非“的意思了。
我们是代表美国官方的学术访问团体,接待我们的当然也是中国官方的学术界。接待的热情和诚恳是令人感动的,可以说做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但是既属官方交往,”官腔官话“彼此都是无法避免的。
这种情况对我来说,却真感到有些”难以为怀“了。后来承接待人员的好意,让我有充分的机会和家人亲友相聚,听到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当然也更加深了化鹤归来的感受。
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在中国先后旅行了整整一个月。我们的任务是访问汉代遗迹,所以足迹所至大致以”秦时明月汉时关“为主,在洛阳、西安、兰州、敦煌、昆明、成都等地各停留了两三天。在旅途中,我特别察觉到我自己的心情与同行的美国朋友迥然不同。
他们所全神贯注的是怎样通过这次访问来改进他们的专题研究:或证实或修正他们已有的”工作假设“。中国对于他们只是一个客观研究的对象。我虽然也有此客观的一面,但是我的心情主要是一个千载后的子孙来凭吊祖先所踏过的足迹。
从西安到敦煌这一段火车行程尤其使我神游于千载之上,时时体念到汉唐时代的祖先怎样开拓了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国家,创造了这样一个绵延不绝的文化。我的心情不但与美国同行者完全不同,甚至和伴随我们的中国朋友也截然异趣。
这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意识已相当彻底地政治化了。他们透视中国史所运用的一些概念范畴,如”奴隶“、”封建“、”阶级斗争“等,对我而言是非常陌生的。例如在西安霍去病墓前,我们看到著名的”马踏匈奴“的西汉石雕,但是这个石雕的正式名称却变成了”马踏匈奴奴隶主“。
我们再三地端详,始终无法看出马足下那个模糊不清的匈奴具有何种社会身份。这个标签也许和大陆的”民族政策“有关,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但是这毕竟是歪曲历史来迁就政治现实。”马踏匈奴奴隶主“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例子,但观微却可以知著。
二十年前我曾研究过汉代的中外经济交通,河西走廊正是我的研究重点之一。但当年只是纸上谈兵,对这条”丝路“并没有亲切的认识。这次从西安经兰州去敦煌才使我了解祖先创业的艰难。这是程伊川所谓的”真知“。在兰州至敦煌的途中,我有《河西走廊口占》一诗。诗曰:
昨发长安驿,车行逼远荒。两山初染白,一水激流黄。
开塞思炎漠,营边想盛唐。时平人访古,明日到敦煌。
诗不足道,但可从其中看出一点我的”中国情怀“。
从敦煌回来,要在清晨三时左右乘汽车赶到柳原。残月在天,在横跨戈壁的途上先后遇到多起骆驼车向敦煌的方向进行,也许是赶早市的村民吧。我当时不禁想到:这岂不是两千年前此地中国人的生活写照吗?除了我们乘的汽车,两千年来的敦煌究竟还有些什么别的变化呢?至少以这个地区而言,汉代的敦煌是比今天要繁荣热闹得多了。我的”中国情怀“禁不住又发作了,这也有诗为证:
一弯残月渡流沙,访古归来兴倍赊。
留得乡音皤却鬂,不知何处是吾家。
限于访问团的性质,我们的行程基本上不包括我少年时代所熟悉的江南。其中虽预计在南京停留一天,访问紫金山的天文台,但又因班机延误而临时取消了。以我们的学术任务而言,此行可谓了无遗憾,即以开阔眼界而言,此行也收获至丰。但是失去重到江南的唯一机会,对我个人而言,则实不胜其惆怅。所以在离开北京的前夕,我曾写下这样几句诗:
凤泊鸾飘廿九霜,如何未老便还乡。
此行看遍边关月,不见江南总断肠。
这显然又是我的”中国情怀“在那里作祟了。
尽管29年后化鹤归来,发现”城郭如故人民非“,我的”中国情怀“不但未曾稍减,似乎反而与日俱增。正因如此,我才不能忘情于故国,而往往要以世外闲人的身份,与人话国事,说些于己无益而又极讨人嫌的废话。我曾屡次自戒,而终不能绝。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二记载了他的朋友所说的一段佛经上的故事。
这个故事说:
昔有鹦鹉飞集他山……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周亮工的朋友接着发感慨说:
余亦鹦鹉翼间水耳,安知不感动天神,为余灭火耶!
这个美丽的故事虽出于印度,但显然已中国化了。“知其不可而为之”,“明其道不计其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些话和上面那个神话在精神上不是完全一致的吗?不过不及神话那样生动感人罢了。大概“尝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几个字可以说明我在这一方面的“中国情怀”吧!
不但对中国大陆如此,对香港我也一样有“侨居是山,不忍见耳”的情感。最近为文涉及香港的文化问题,责之深也正由于爱之切(见《明报月刊》1985年4月号)我先后在香港侨居了六七年,何忍见其一旦毁于大火。但在抱有狭义的地方观念的读者看来,便不免要疑心我看不起“香港文化”了。
我这只飞集他山的鹦鹉竟因此变成了“能言鹦鹉毒于蛇”的鹦鹉,岂不冤哉!最近看到我的朋友刘绍铭所写的一篇关于大陆“游学生”文学的文章,其中引了王蒙《相见时难》中的一段话,颇耐人寻味。王蒙说:
一个几十年来没有对祖国、对祖国的多难的人民尽过一点义务的“美籍华人”,却有资格来向他提出问题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你芝加哥的和纽约的、旧金山和洛杉矶的美籍华人都加在一起,能懂得这两句诗的含义吗?(《明报月刊》1985年4月号,69页)
这样义正辞严的话,像我这个“美籍华人”读来安能不羞愧欲死。不过羞愧之余,我也发生了一个无法解答的疑问:为什么换了“新天”的今天,忽然产生了这许多“美籍华人”呢?王蒙文中的“美籍华人”显然都是1949年以后出现的。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1927年国民革命以后,甚至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都没有听说过世界上有所谓“美籍华人”这种奇怪的动物。今晚偶然读到陈援庵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看见下面一节文字。姑且抄出来,算作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去国必有可爱之道,而后能令人爱之,天下有轻去其国,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矣。《硕鼠》之诗人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何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长思也。(《民心篇》第十七)
援庵先生的学问是我所敬佩的。他在1959年以80髙龄加人了共产党,因此他必然也是大陆的作家如王蒙先生者所推崇的。这是一个难得大家都欣赏的人物,尽管欣赏的角度也许彼此有异。援庵先生既然说“其故可深长思”,那就让我们都暂且冷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