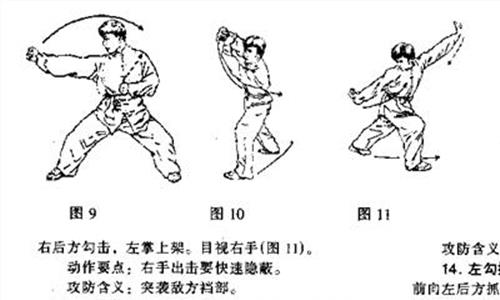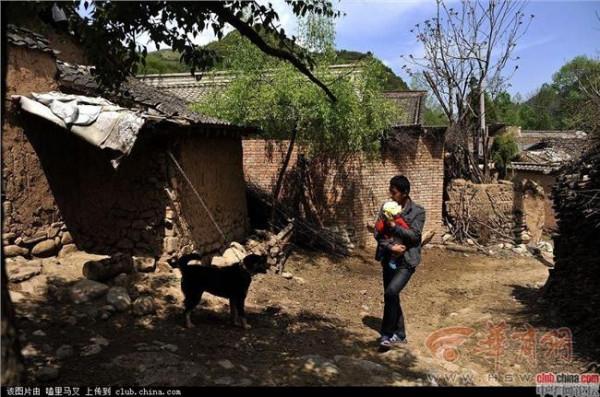邓晓芒妻子肖书文 邓晓芒文章转载
编者按:邓晓芒是残雪(邓晓毛)的哥哥,哥哥对妹妹自然有理解,而且文章写完后,残雪是过目的。
一般来说,我们是凭借文字(原文或译文)来学习文学史的,但领略文学史中的“文学”,却必须借助于“心”。然而,由于心和心难以相通,这种情况极少发生。所以数千年来,文学史对文学的领略完全不成比例。人类的艺术家所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全体人类就是再诞生和绝灭好几个轮回也领略不完,那本身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心灵撞击的火花偶尔能在黑暗中向人们揭示它的无限性,旋即就熄灭了。人们无法借此看清人心的底蕴,但却由此而受到启发,知道在黑暗中并不是一无所有,而是有另一些和自己一样摸索着、渴望着的灵魂,只要凝视,就会发现它们在孤寂的夜空中悄然划过天际。

因此,在二十世纪初的西方和世纪末的东方,两位具有类似艺术风格的作家卡夫卡和残雪的相遇,是一件极其有趣、甚至可以说是激动人心的事情。这件事如何能够发生,实在是难以想象。这两位作家的时代背景、地域背景、文化背景和思想背景是如此不同,甚至性别也不同(而性别,在今天被一些人看作一个作家特点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有“女性文学”一说),他们凭什么在文学这种最为玄奥的事情上达到沟通呢?这种沟通是真实的吗?假如人们能证实或相信这一点,那就表明人的精神真有一个超越于种族、国界、时代、性别和个人之上的王国,一个高高在上的“城堡”,它虽然高不可攀,无法勘测和触摸,但却实实在在地对一切赋有人性的生物发生着现实的作用,使他们中最敏锐的那些人一开口就知道对方说的是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王国或城堡其实并不在别处,它就在每个人心中,只是一般人平时从不朝里面看上一眼,无从发现它的存在罢了。但即使一个人拼命向内部观看、凝视,也未见得就能把握它的大体轮廓,它笼罩在层层迷雾之中,永远无法接近,只能远远地眺望。
虽然如此,人们毕竟有可能认定它的存在,并为之付出最大的、甚至是毕生的心血,去想方设法地靠近它,描述它。这种努力本身就是它存在的证明。
毫无疑问,残雪是用自己那敏感的艺术心灵去解读卡夫卡的。在她笔下,卡夫卡呈现出了与别的评论家所陈述的、以及我们已相当熟悉和定型化了的卡夫卡完全不同的面貌。这个卡夫卡,是一个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家,一个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判家。
当然,他也有几分像哲学家,但这只不过是由于纯粹艺术本身已接近了哲学的缘故。只有一个纯粹的艺术家才有可能对另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作这样的长驱直入,撇开一些外在的、表面的、零碎的资料,而直接把握最重要的核心,而展示灵魂自身的内在形相,因为他们是在那虚无幽冥的心灵王国中相遇的。
在这里,感觉就是一切,至少也是第一位的。这种感觉的触角已深入到理性的结构中,并统帅着理性,为它指明正确的方向。
在残雪看来,没有心的共鸣而能解开卡夫卡之谜,或者说,撇开感觉、站在感觉的外围而能把握卡夫卡的艺术灵魂,这无异于痴人说梦。一切企图从卡夫卡的出身、家族、童年和少年时代、性格表现、生活遭遇和挫折、社会环境和时代风气入手去直接解读卡夫卡作品的尝试,都是缘木求鱼。
正确的方向勿宁要反过来:先真诚地、不带偏见地阅读作品,读进去之后,有了感受,才用那些外部(即心灵王国外部)的资料来加以佐证。至于没有感受怎么办呢?最好是放弃,或等待另外更有感受力的读者和评论家来为我们引路。天才的作品需要天才的读者(或评论家),现代艺术尤其如此。
现代艺术与古典艺术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艺术视野转向内部、转向那个虚无幽冥的心灵王国。因此,现代艺术只有那些内心层次极为丰富、精神生活极为复杂的现代人才能够创造和加以欣赏。这就注定现代艺术的读者面是狭窄的,而且越来越狭窄。
它与大众文化和通俗艺术的距离越来越远,它永远是超越它的时代、超前于大众的接受力的。由此也就带来了现代艺术的第二个重要特点,这就是作品的永远的末完成性。这种末完成性,并非单指许多作品本身处于末完成的、正在制作过程中的状态(这一点卡夫卡的作品尤为明显,他的主要作品《城堡》和《审判》都未写完,许多作品都只是片断);更重要的是,现代艺术本质上离开评论家对它的创造性评论,就是尚待完成的。
这些作品作为“文本(text)”只是一个诱因,一种召唤或对自由的呼唤,作者用全部生命所表达出来的那种诗意和精神内涵,绝对有赖于并期待着读者的诗性精神的配合,否则便不存在。这一点,充分体现出了精神本身的过程性和社会性本质。
精神是什么?精神就是永恒的不安息、自否定,精神就是对精神的不满和向精神的呼吁,这是由精神底蕴的无限性、即无限可能性和无限可深入性所决定的。因此,安定的精神已不是精神,自满自足的精神也将不是精神,它们都是精神的沉沦和“物化”。正如精神只有在别的精神那里才能确证自己是精神一样,现代艺术的作品也只有在读者那里才真正完成自身。
残雪在连续几年多产的写作之后,于1997年开始进入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创作,即逐篇解读她心仪已久的卡夫卡。这的确是一种“创作”,我们在这些作品中,可以发现残雪所特有的全部风格。实际上,残雪从来就不认为创作和评论有什么截然分明的界线,她自己历来就在一边写作,一边不断地自己评论自己,如在《圣殿的倾圮——残雪之谜》(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就搜集了8篇残雪正式的自我评论和创作谈。
甚至她的作品本身也充满了对自己写作的评论,她的许多小说根本上也可以看作她自己的创作谈,而她的一系列创作谈大都也本身就是一些作品,即一些“以诗解诗”之作。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她是这样做的唯一的人,而在世界文学中,卡夫卡则是这种做法的最突出的代表。
艺术和对艺术的评论完全融合为一的这些作品是理解残雪和卡夫卡这类作家的最好入口(想想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约瑟芬和耗子民族》等名篇,在残雪,则有《天堂里的对话》、《突围表演》、《思想汇报》等等)。
如果说,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因为没有“合胃口的食物”绝食而死的话,那么残雪则比这位艺术家要幸运得多,她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合胃口的食物”。当然,这种食物并不能止住饥饿,反而刺激起更强烈的饥饿感,因为这种精神食粮不是别的,正是饥饿本身。
但毕竟,这种“对饥饿的饥饿”比单纯的饥饿艺术更上了一层楼,它成了饥饿艺术的完成者,因为如前所述,卡夫卡的饥饿艺术是一种呼吁,残雪的解读则是一种回应,因而是一种完成:残雪“完成了”卡夫卡的作品。
卡夫卡的作品中,分量最重、也最脍炙人口的是《变形记》、《审判》和《城堡》。但残雪这本评论集中却没有讨论《变形记》,这决不是偶然的疏忽。相反,这表现出残雪对卡夫卡作品的一种特殊的总体考虑,即《变形记》属于卡夫卡的未成熟的作品,当后来的作品中那些主要的核心思想尚未被揭示出来之前,这篇早期之作的意义总要遭到曲解和忽略。
在残雪看来,全部卡夫卡的作品都是作者对自己内心灵魂不断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即鲁迅所谓“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痛苦的自我折磨之作。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立场,那么我们的确可以看出,《变形记》正是这一历程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方向似乎还不明确。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这一事件是意味着控诉什么呢,还是意味着发现了什么?通常的理解是前者。人们搬弄着“异化”、“荒诞”这几个词,以为这就穷尽了小说的全部意蕴。
然而,即算从社会学和历史哲学的眼光来看,异化是如此糟糕的一种人类疾病,但从文学和精神生活的角度看,它却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一种自我意识和自我反省的功课。不进入异化和经历异化,人的精神便没有深度,便无法体验到人的本真的存在状态;这种存在状态不是某个时代或某个社会(如现代西方社会)带给人的一时的处境,而是人类的一般处境,即:人与人不相通,但人骨子里渴望人的关怀和爱心;人与自己相离异,但人仍在努力地、白费力气却令人感动地要维护自己人格的完整,要好歹拾掇起灵魂的碎片,哪怕他是一只甲虫。
然而,《变形记》中的“控诉”的色彩还是太浓厚了,尽管作者的本意也许并不是控诉,他对人类的弱点了解得太清楚了,他只是怀着宽厚的温情和善意在抚摸这些累累伤痕的心灵,但人们却认为他与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差别只在于手法上的怪诞不经。
因而这一“批判现实”的调子一开始就为解读卡夫卡的艺术方向定了位,人们关心的就只是他如何批判、如何控诉了。
这种偏见也影响到对卡夫卡其他一些作品的阐释,最明显的是对《审判》的解读。流行的解释是:这是一场貌似庄严、实则荒唐无聊、蛮不讲理、无处申冤的“审判”,实际上是一次莫明其妙的谋杀;主人公约瑟夫·K尽管作了英勇的自我辨护和反抗,最后还是不明不白地成了黑暗制度的牺牲品。
在中文版的《卡夫卡全集》(叶廷芳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中,“审判”被译为“诉讼”,似乎也是这种社会学解释的体现。然而,残雪的艺术体验却使我们达到了另一种新的维度和层次,即把整个审判看作主人公自己对自己的审判(“诉讼”的译法杜绝了这种理解的道路)。她在《艰难的启蒙——读〈审判〉》一文中开宗明义就说:
“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这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
K从最初的自认为无罪,自我感觉良好,到逐渐陷入绝望,警觉到自己身上深重的罪孽(不一定是宗教的“原罪”,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即把自己当罪人来拷问),最后心甘情愿地走向死亡并让自己的耻辱“长留人间”,以警醒世人(人生摆脱不了羞耻,应当知耻):这决不是什么对法西斯或任何外在迫害的控诉,而是描述了一个灵魂的挣扎、奋斗和彻悟。
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肮脏和污秽,灵魂的内部法庭遍地狼藉,恶毒和兴灾乐祸的笑声令人恐惧,形同儿戏的草率后面隐藏着阴谋。
这是因为,这里不是上帝的光明正大的法庭,而是一个罪人自己审判自己。罪人审判罪人,必然会显得可笑,暧昧;但它本质上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甚至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严肃的事情。真正可笑的是被告那一本正经的自我辨护,当然这种自我辨护出自生命的本能,是每个热爱生命的人都必定要积极投入的;但它缺乏自我意识。
不过反过来看,正是这种生命本能在促使审判一步步向纵深发展,因为这种本能是一切犯罪的根源。
没有犯罪,就没有对罪行的审判;而没有在自我辨护中进一步犯罪(自我辨护本身就是一种罪,即狂妄自傲),就没有对更深层次的罪行的进一步揭露。所以从形式上说,法律高高在上,铁面无情,不为罪行所动摇;但从过程上看,“法律为罪行所吸引”,也就是为生命所吸引。
法为人的自由意志留下了充分的余地,正如神父所说的:“你来,它就接待你,你去,它也不留你”。但生命的一切可歌可泣的努力奋斗,如果没有自审,都将是可笑的。
然而,自审将使人的生命充满沉重的忏悔和羞愧,它是否会窒息生命的灿烂光辉呢?是否会使人觉得生和死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甚至宁可平静地(像K一样)接受死亡呢?这就是卡夫卡的问题,也是残雪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城堡》中给出了另一种回答。
“城堡”是什么?城堡是生命的目的。人类的一切生命活动都隶属于它,它本身却隐藏在神秘的迷雾中。残雪写道:
“与城堡那坚不可摧、充满了理想光芒的所在相对照,村子里的日常生活显得是那样的犹疑不定,举步维艰,没有轮廓。浑沌的浓雾侵蚀了所有的规则,一切都化为模棱两可。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理想(克拉姆及与城堡有关的一切)在我们心中,神秘的、至高无上的城堡意志在我们的灵魂里……而城堡是什么呢?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
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K对自身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理想之光——读“城堡”(之一)》)
其实,只要我们按照残雪的眼光,把《审判》中的“法”不是看作外来的迫害,而是看作心灵自审的最高依据,我们就可以看出,“法”和“城堡”本质上是一个东西。就是说,人的自审和人的生存意志、和对理想的追求是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在《审判》中读到的神父所讲的那个晦涩的故事,实际上已经是《城堡》的雏形了。故事说,一个乡下人来到法的大门前,请看门人让他进去见法,守门人说现在还不行,乡下人于是在门口等待,等了一辈子。临死前守门人才告诉他:“这道门是专为你而开的,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
乡下人错就错在,他不像《城堡》中的K那样胆大妄为,那样充满活力,他不知道,只有犯罪(如冲破守门人的阻拦,闯过一道道门卫)才能接近法,才能按照法来评价和审视自己的生活。
《城堡》中的K却是一个醒悟过来了的“乡下人”,他径直强行闯入了城堡外围的村落,并努力通过一道一道的关卡:老板和老板娘,弗丽达,信使巴纳巴斯,奥尔伽和阿玛丽娅,助手们……这些都是城堡的守门人。
如果你服从他们,他们便把你挡在门外,让你一辈子无所作为;如果你骗过他们、征服他们,他们就成为你的导师和引路人。但这种生命的冲撞需要的是创造性的天才和临机应变的智慧,以及“豁出去了”的决心。《城堡》中的K与《审判》中的K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不再自以为纯洁无辜,他的自审已成为他内心的一种本质结构,因而极大地释放和激发了他的生命本能。正如残雪说的:
“K永远是那个迟钝的外乡人,永远需要谆谆的教导和不厌其烦的指点,他的本性总是有点愚顽的,可是他有良好的愿望,那梦里难忘的永恒的情人伴随着他,使他闯过了一关又一关,在通往城堡的小路上跋涉。但是K不再是纯粹的外乡人了,在经历了这样多的失望和沮丧之后,他显然成不了正式的村民了,他仍然要再一次的犯错误,再一次的陷入泥淖,但每一次的错误,每一次的沦落,都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放心的思想,这便是进村后的K与进村之前的K的不同之处”(《梦里难忘……——读“城堡”(之二)》)
然而,不论K的思想境界有怎样的提高,不论他进入法的大门多么远,挨近城堡多么近,他与城堡或法的对峙是永远也无法完全解除的。直到最后,他与老死在法的大门外的那个外乡人并没有根本的区别。“K又怎么料得到,那高高在上,永远也无法进入的圣地,竟是只为他一个人而存在的呢?村民们究竟是要引导他明白这一点,还是要阻碍他达到这个认识呢?”(《城堡的形象——读“城堡”(之五)》)《城堡》与《审判》始终构成一个悬而未决的矛盾,双方谁也不能归结为谁,哪一方也不比另一方更高明,因为这是人类永恒的矛盾:没有自我否定(自审),生命就会沉沦;但没有生命,自我否定就无法启动;自我否定将否定生命,走向死亡;但走向死亡的自我否定(向死而在的生存)不正是强健有力的生命的体现吗?生命本身就是在这种自相矛盾和自身冲突中从一个层次迈向另一个更高的层次,哪怕其结局同样是死,但意义却大不相同。
一朵娇弱的玫瑰比整个喜玛拉雅山更高贵。
除了对上述两个长篇的评论外,残雪对其他一些作品的评论也是饶有兴味的,它们向我们展示了卡夫卡内心世界的多面性。但万变不离其宗,贯穿于其中的核心思想是对人类在现代社会中所暴露出来的人性之根的思考。这种人性之根在过去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中一直是潜伏着的、被掩藏着的,在今天却以赤裸裸的、骇人听闻的、无法忍受的真实向人呈现出来,再次逼问人类一个终极的问题:活,还是不活?
《走向艺术的故乡——读卡夫卡“美国”》一文,揭示了卡夫卡艺术的这个人性之根的背景。卡夫卡在《美国》中,以象征的方式描述了现代艺术、包括他自己的艺术所得以立足的那个现代人格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的前提就是“被抛弃状态”。
用残雪的话来说:“抛弃,实际上意味着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但这是个多么痛苦的过程啊!
矛盾与恐怖缠绕着他,对温情的向往和回忆瓦解着他的决心。卡夫卡本人的惨痛经历最清楚地说明了这种历程既锻炼人、又摧毁人的残酷性。他一次又一次地梦想结婚,企图用世俗的快乐来缓和内心激烈的冲突。但他每次都毅然挺立起来,决心独自一人承担命运。
夺去他生命的肺结核既是世界的象征,又是人性的象征。人生就是一场和自己与生俱来的疾病相持不下的消耗战,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如果你自己撑不住了,那就是你的死期。
由这种观点来读《美国》,它就透现出一种悲壮的意义,而决没有狄更斯小说中那种可怜兮兮的“暴露”和“公理战胜”的满足;它勿宁是对“公理战胜”的一种反讽,是对真实的自由的阴郁的体认。在小说中,“卡夫卡正是一步步走向自由,走向这种陌生的体验的。
他的体验告诉他:自由就是孤立无援之恐怖,自由就是从悬崖坠下落地前的快感,对自由来说,人身上的所有东西全是累赘,全都是要丢失的”。以为卡夫卡在揭露美国式自由民主的虚假性,这种解读是多么肤浅!
卡夫卡确实在“揭露”,但更重要的是他在承担。这不是什么“虚假的”自由,这就是自由本身,即自由的丑陋的真相,就看你有没有勇气去承担它!现代艺术的故乡完全是建立在这种自由之上的,其创作和欣赏不光需要天才,而且需要勇气。
《无法实现的证实——创造中的永恒痛苦之源,卡夫卡“一条狗的研究”读后感》这篇文章,同样切合“走向艺术的故乡”这一主题。这里直接谈论了艺术创作的实际过程。《一条狗的研究》这篇小说与《饥饿艺术家》属于同一题材,小说中也有作为艺术家的“狗”通过饥饿、绝食来创造美的情节,但所涉及的问题更加广泛得多。
我们看看残雪在文章中开头所开列的那个象征(隐喻)符号的能指—所指清单,便可见出卡夫卡艺术精神的内在构成的复杂性。
只有残雪,凭借她那细腻的艺术感觉和在作家(尤其是女作家)中罕见的强大的理性穿透力,才能深入这个结构的内部去作如此明察秋毫的解剖。这实际上也是残雪对自己的艺术自我的分析。理性与非理性,生命的本能冲动与科学原则,个体与社会,现实和理想,生的体验和死的召唤,这是整整一部艺术心理学,但不是诉之于概念和论证,而是对感觉的理性掌握或对原理(原则)的直接体悟。
在其中,目的不是阐明艺术创造的隐秘机制,而是借助于对这种机制的揭示来表达一种浓郁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情绪。
这种情绪在《永恒的漂泊——读“猎人格拉库斯”》一文中更为直接地呈现出来,这就是在人世和地狱之间永远流浪、永远无归宿无着落的苍凉之感。猎人格拉库斯本应去地狱报到,但载他的船只开错了方向,他只好在世界上到处漂泊。
这是残雪和卡夫卡对于做一名艺术家共同的内心体验:“漂泊,除了漂泊还是漂泊,独自一人”,“欲生不可,欲死不能”;人间的生活他已无法再加入,天堂又绝无他的份,“猎人的生活历程就是一切追求最高精神,但又无法割断与尘世的姻缘的人的历程”。
这种对创作情绪的自我分析或通过自我分析表达出来的创作情绪,同样也贯穿于残雪对其他几个短篇的解读中。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着“描述者的艺术自我”、“艺术良知”;《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和祈祷者谈话》中,“祈祷者和‘我’是艺术家内心的两个魔鬼,既相互钳制,又相互鼓励、支撑,结成同盟来对付那摧毁、覆盖一切的虚无感”;至于《地洞》,在残雪的解读下也不是什么现代社会下人无处可逃的处境的象征,而是艺术家内心的本真矛盾的体现,即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双重的恐惧使他在有与无之间来回奔忙,耗尽了精力,构筑出奇巧宏伟的艺术工程,同时“体验到了它那无法摆脱的生存的痛苦”(引文均引自残雪各篇文章)。
艺术家的生涯是人类一般生存状态的集中体现,艺术家是当代人类一切苦难的精神上的承担者,是背负十字架的耶稣;同时,艺术家又是人生意义的创造者,是黑暗中的光明、虚空中的存在。
我们甚至可以说,由于有了艺术家,所以才有了人。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卡夫卡和残雪都把艺术家灵魂的自我分析、自我深入当作自己艺术的最主要的题材了。
这决不是什么“脱离生活”、“脱离现实”、“闭门造车”和“主观虚构”,而正是一种最深刻、置身于人类生活最尖端的生活。因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灵魂就是人类灵魂的代表(如鲁迅被公认为“民族魂”),哪怕大众很难理解他、接近他,他也在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和创造在为大众做一种提高人类尊严、促进人类自我意识的工作,没有他们,大众将沉沦为精神动物。
现在我们要谈谈残雪和卡夫卡在气质上和精神生活上的一致性了,没有这个前提,一个艺术家即使带有美好的愿望,也是很难走进卡夫卡的精神王国的。残雪和卡夫卡则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两人都有一种桀傲不驯的内在性格,有一种承受苦难的勇气和守护孤独的殉道精神,都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敏锐和透视本质的慧眼,有一种自我反省、自我咀嚼、“向内深入”的坚定目标和忍受剧痛的坚强耐力,有一种置身于自我之外调侃自身、调侃自己的一切真诚的决心和痛苦的眼泪的魔鬼般的幽默,有一种阴沉、绝望、一片漆黑然而却自愿向更黑暗处冒险闯入的不顾一切的蛮横,有一种自我分裂、有意将自己置于自相矛盾之中的恶作剧式的快感……当然,也同样遭受到同时代人的误解和非议,卡夫卡被视为现代社会的批判者或法兰克福学派的传声筒,残雪也被说成是一个时代的“恶梦”和变态人格的妄想者。
从作品来看,两人的作品都展示了灵魂内部的各种层次、关系、矛盾冲突和不同阶段的反省历程,都体现了艺术家的、因而也是全人类的生存痛苦和理想追求,都如此主观、内向、阴暗、充满忏悔意识,但也都如此强悍、不屈不挠,遍体鳞伤却永远在策划新的反抗。
这真是本世纪世界文学中一种最有趣的奇观!这一奇观的产生,也许是因为他们代表中、西文化在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中共同走入了“世纪末”的意境,并对两种文化中的人性之根进行了最彻底的反省的缘故吧。但这同时也就带来了两人之间的一些微妙的差异。
这些差异主要植根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心态。先从表层的艺术风格上来看。残雪与卡夫卡在风格上是十分接近的,例如两人都有大段大段滔滔不绝的议论和叙述,但语言又同样的干净、纯粹,没有多余的话;他们都善于通过对话(包括内心的对话)来泄露说话者的心情;他们的每个人物都是象征性的,为的是表达一种情绪化的哲理;他们的激情都很含蓄,而理智却很强健,至于感觉,则是全部写作的润滑剂。
然而,卡夫卡仍然明显地继承了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他能将不论多么怪诞不经的情节描写得如同身历其境,纤毫毕现;而他的对话是如此合乎逻辑,几乎没有跳跃,凡是晦涩之处必定是思想本身的复杂和深邃所致。
相反,残雪不大看重外部的细节,其手法近似白描,其语言和对话跳跃性很大,甚至类如禅宗“公案”;在许多作品中,她致力于诗的语言的锤炼和诗的意境的传达。
她有时让主人公的内在自我直接现身乃至于抒情,这是卡夫卡决不可能的。后者在内心最深层次上仍然保持着客观描述的“心理现实主义”原则。
文化心态的影响在更深层次上表现在主人公灵魂的塑造方面。西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罪感文化”,这一点在卡夫卡的《审判》(及《致父亲的信》)中体现得特别明显。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主要就体现在“知罪”上。在残雪的作品中,这一点被大大地弱化了。
残雪可与《审判》相提并论的作品是《思想汇报》,其中的主人公A君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不是体现为“知罪”,而是体现为“知错”;他虽然也有忏悔、甚至不断忏悔、永远忏悔的主题,但“忏悔神父”其实不过是主人公自己,顶多是他的另一个自我,而决不代表彼岸世界的声音。
因而这种忏悔基本上是对自己的愚顽不化、自以为是和不自觉的虚伪这些痼疾的启蒙;其中的痛苦是追求不到真正的自我的痛苦,其中的恐惧只是面对死亡和虚无的恐惧,而不是面对地狱和惩罚的恐惧。
实际上,如果真有地狱的话,残雪的主人公甚至会很高兴,因为终于可以摆脱虚无的恐怖了,地狱的惩罚毕竟也是一种“生活”,它也许还可以用作艺术创造的题材!
相反,在卡夫卡那里,对存在的恐惧和对虚无的恐惧几乎不相上下(见《地洞》及残雪对它的评论),所以约瑟夫·K在知罪时可以如此平静地对待死亡,甚至有种自杀的倾向。因此,总体看来,残雪的作品虽然也阴暗、邪恶、绝望,充满污秽的情节和龌龊的形象,但却是进取的,在矛盾中不断冲撞、自强不息的。
卡夫卡的作品则是退缩的、悲苦的、哀号着的,他的坚强主要表现在对罪恶和痛苦的承担上,而不是主动出击。他的座右铭是:“每一个障碍都粉碎了我”。
与此相关的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天人相分的传统,卡夫卡对理想的追求是对一个彼岸世界“城堡”的追求,这个“城堡”是固定的,一开始就隐隐约约呈现出它的轮廓,但就是追求不到,对它的追求构成了尘世的苦难历程;相反,残雪所追求的理想却是随着主人公的追求而一步步地呈现出来的,在她的《历程》中(可与《城堡》相对照),主人公(皮普准)对将要达到的更高境界在事前是一无所知的,只有进入到这一更高境界,才恍然悟到比原先的境界已大大提高了,但仍然有另一个未知的更高境界在冥冥中期待着他。
只有主人公内在的生存欲望是确定的,这种欲望推动着他从一个“村镇”到另一个“村镇”不断提高、不断深入,这些村镇本身勿宁说对他显得是一些不断后退的目标。
再者,在人物的相互关系上,卡夫卡的人物总是被他人拒斥、抛弃和冷落,一切关系都要靠主人公自己去建立,即使如此这种关系也是不可靠的,随时会丢失的;残雪的人物却总是处在不由自主的相互窥视、关怀和相互搅扰中,想摆脱都摆脱不掉,主人公常常是一切人关注的焦点。
因此,当卡夫卡和残雪鼓吹同一个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时,他们的情绪氛围并不完全相同:卡夫卡是对一切人怀着无限的温情,从“零余者”的心情中努力站立起来,鼓励自己走向孤独的旅途;残雪却是一面怀着兴灾乐祸的恶毒从人群中突围出来,一面从更高的立足处(即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克制着内心的厌恶去和常人厮混,去磨砺自己的灵魂。
当然,这不光是文化的作用,而是与他们两人的不同性格有关:卡夫卡的清高孤傲使他生性脆弱,容易受伤,残雪则更为平民化、世俗化,更为坚韧和理性地面对生活。
因此,毫不奇怪,我们在残雪对卡夫卡的评论中没有发现西方宗教精神对卡夫卡艺术创造的深刻影响。尽管卡夫卡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应当是无法根除的,它事实上使卡夫卡后期转向了对犹太教的浓烈兴趣。
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在这本书里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残雪的卡夫卡”,或者说,残雪把卡夫卡“残雪化”了。这是中国人一般说来可以理解和感觉到的一个卡夫卡。然而,正因为残雪所立足的人性根基从实质上说比宗教意识更深刻、更本源、更具普遍性,所以她对卡夫卡的把握虽然没有直接考虑宗教这一维,但决不是没有丝毫宗教情怀;另一方面,也正由于绕过了西方人看待卡夫卡所不可避免的宗教眼光的局限,她的把握在某些方面反而更接近本质,它是一个中国人在评论卡夫卡的国际性论坛上所作出的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