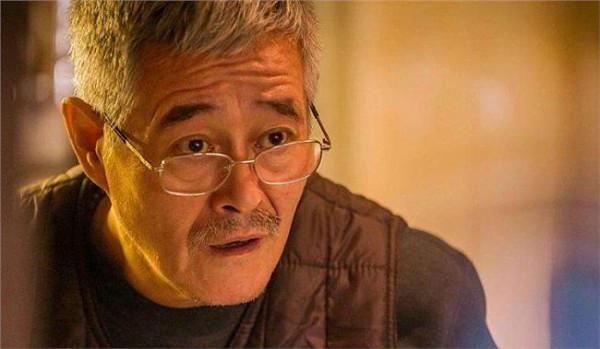许地山的女儿 许地山女儿许燕吉的“麻花人生”|有读10
“你们要像花生,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不是外表好看而没有实用的东西。”
数代中国人,谁未读过这质朴的句子?语文课本收录了散文名篇《落花生》,笔名“落华生”的许地山也就这样被人们代代所知。
许地山用花生这种食物讲述做人的道理,他的小女儿、80岁的许燕吉则在自传《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中用另一种食物形容自己的一生:麻花。

“麻花是形容它的被扭曲。国内的同龄人几十年来也未见平坦风顺,只是我的人生被扭得多几圈而已”。
1941年,父亲猝死,同年,日军占领香港,7岁的许燕吉和家人踏上北归逃难的旅途;
1958年,25岁的许燕吉从石家庄奶牛场的畜牧技术员变成右派、反革命“双皮老虎”,判刑六年,孩子在出生前十几天夭折,丈夫为划清界限,一再坚持与她离婚;

刑满后,无路可走的许燕吉在监狱里就了业,1969年,36岁的她被疏散到河北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改造,之后为谋生计嫁给陕西一位年长她10岁的目不识丁的老农;
1979年平反、复职,两年后,年近半百的许燕吉进了江苏省农科院,在生产第一线上干到退休。

许燕吉的故事曾被多次报道,“记者毕竟不是亲历者,且注意力多在我不寻常的婚姻上,我自己动手,将真人真事和盘道出,也许能给别人一点儿人生的借鉴,而且,朋友们跟我说,你经历过这么多事,一生跟国家的命运结合紧密,写写这些也很有意义。”这是许燕吉自传的由来,她说想把这本书送给渐渐老去的与自己有相似经历的人们,也送给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年轻人。

在这本写了三年的书里,有近百年的历史烟云、时代风浪,有名流与普通人的生命片段,有一代知识分子的曲折命运,有无数细碎细致的悲喜沉凉。这些被大历史一带而过的个体记忆如同注脚,填补在正史叙述的骨架上,让我们得以了解诸多未曾听闻的细节往事——“我希望你们既看到水面上的花,也看到下面那些不怎么好看的根。”
麻花扭上一圈,是贯穿许燕吉整个少年时代的战乱和颠沛流离。香港、长沙、桂林、贵阳、重庆……对于1933年出生的许燕吉和其同龄人,日本侵占中国点燃的战火是他们成长的首要背景,逃难则是主要内容。
1941年圣诞节,香港沦陷。难以维系生活也不堪做亡国奴,许燕吉一家决定返回内地。乘船离开时,许燕吉看到临海的干诺道上,一座座英国国王铜像倒在街边,想起父亲许地山生前曾指着这些铜像说这是英国人示威的东西,等香港回归中国,就会把它们搬下去,她不知该高兴还是悲哀:“它们都下来了,却是敌人干的”。
她回忆,在当时广州边境的寸金桥,桥东是法租界的岗哨,桥西站着中国士兵。人们路过时,都自发地给中国士兵鞠大躬,为的是泄给日本人鞠躬的愤,也是表达踏上自己国土的激动之情。年幼的许燕吉和哥哥也郑重地鞠了躬。
到湖南衡阳读小学,临毕业,长沙被围,学校只得提前放假。在最后一堂课上,师生们都想起都德的《最后一课》,站起来喊“抗战必胜”“中国不会亡”!
从湖南逃到桂林,还没落脚,就卷入湘桂大撤退,接着逃。逃难的人群挤满、挂满了火车内外,铁道沿路都是死人。许燕吉想起日本占领香港后饿死街头的人,她的母亲在收尸队的报表上看到,收尸队一天曾收过900多具尸。逃亡路上接连所见的惨相使许燕吉这样理解战争:“战争就是死老百姓”。
跟着家人,她从桂林逃到贵阳读中学,没过多久,日本又打了过来,只得继续奔逃,落脚重庆,考进南开中学,在一逃再逃的日子里长大成人。
书里,许燕吉描述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街景:有人大喊,有人大笑,有人抱在一起转圈,饭店里桌子上下都站着举杯的人,陷入人海的公共汽车上有人探出身子,举着酒瓶跟车下的人敬酒,有人从窗户伸出手逢人就握……那是真正的狂欢。
1952年,还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的许燕吉和哥哥一起去吴晗家。当时正流行批评尊师重道,吴晗跟他们讲北京城里有小学把老师按在板凳上,让学生们排着队打老师屁股,说完哈哈大笑,“我不明白这位曾是教授的副校长笑些什么。”命运的吊诡,在于没人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境遇会是什么。
接踵而至的运动中,口无遮拦、好提意见的许燕吉被捕入狱,麻花的人生又狠狠扭上了一圈。
回忆往事,她取笑当年的自己是“傻蛇出洞”“瞎蛾扑火”,“可是性格在那里,不太好改,我就是有话必说的那种人,我妈就说我头脑特别简单。”
在狱中,许燕吉见识到人性的复杂与命运的多变。她哭着写信恳求在大学里相识相恋的丈夫念及六年多的感情不要离婚,说出狱后会以一生报答,得到的回复是“我就是要划清界限。”
回头看时,她把丈夫的爱称作“算盘珠子拨出的爱情”,却也明白“我还是爱他的,若不是生活的变故,我们也能凑合过一辈子。”
“生活在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说不清有多少人身不由己。人生被历史的巨刃割得七零八落,如同衰落在地上的泥娃娃,粘都粘不起来。”
许燕吉从不把牢狱生活视为羞于提及的耻辱,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坏人,这点信心还是有的”,而她在狱中体会到的,也常是人性不坏的一面。
1960年到1962年,狱里饿死不少人。许燕吉看到劳改队大队长亲自给犯人们烧火煮汤,确保这锅汤在分下去前不会打折扣,更为当时通过关系偷偷买菜的犯人们担着风险“护航”;劳改队的书记找来粮食局长,在门道里拔河一样拉他去看病号室躺着的犯人,局长不肯进门,但监狱里浮肿的“大头人”和饿成干的“干瘪人”自此每天有了6粒救命的黄豆。
因要立志学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其乐,入狱后,许燕吉很少哭,却在离开劳改队、下放农村那天一脸泪水。她给在劳改队就业期间相处数年,谈及感情的男人留了张纸条,说“只要有一线的可能,你就是我丈夫”,打算在农村等待对方刑满释放,却在半年后发现,在那个穷极的山村,一个独身女人,像最不吝惜体力的老农那样拼命干活,上满了工,省着过活,也还是养不活自己。
1971年,许燕吉投奔陕西的哥哥,“我要找个出路,只好嫁一个人。说句挺悲观的话,我就靠是一个女人才找到了一碗饭。”
麻花再拧一圈。经过挑选和“谈判”,许燕吉嫁给带着个小儿子的陕西农民魏振德。这段婚姻来得太像生意,以至于她的嫂子把他们的结婚证称作“发票”。
多年后,不少人劝平反、复职的许燕吉离婚,她说即使没有爱情,婚姻也是一个契约。和老头子和平相处了十几年,对方没做伤害自己的事,自己也不能因为地位高了就伤害别人。
那个时代,许燕吉的遭遇并非孤例。她在狱中的朋友万斯达因家庭出身被定为特务,在狱中自杀未遂,刑满后也受生活所迫嫁了一个没文化的农民,平反复职后,依然和丈夫住在农村。改革开放后,万斯达带着村里人办工厂,赢得了拥戴,被选为人民代表,当了石家庄市政协委员。
即使生活破碎如粘不起来的泥娃娃,也要拾起来,过下去。大半个世纪前,许地山在小说中写过这样的话:“人就像一个蜘蛛,命运就是一张网。蜘蛛第一次放出来的丝不晓得要被风吹多远,可是等粘到别的东西的时候,它的网便成了。它不晓得网什么时候会破,一旦破了,它就安安然然藏起来,等有机会再结一个好的。人的命运何尝不是这样?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或完或缺,只能顺其自然。”
回溯往事时,许燕吉总抿着下唇,带着笑,目光明亮,好像这辈子有太多快乐。“我性格乐观、脑子简单,哪怕坐牢时,也还是挺开心的。你不开心又能怎样呢?我父亲在他的小说《商人妇》中说过:‘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让我选择,我就选开心,仅此而已。”
她说自己这辈子活得最有意义、最有成就的时候,就是在狱里。那时,她总是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让大伙过得好一点,尽力做个落花生般“有用的人”。她是女犯们家书的代笔、倾诉的对象,还做过戏班子的班头儿,领着大家排剧。在气氛压抑、人人垂泪的困难时期,她把女犯们都拉到院子里做操、编顺口溜、搞联欢会,逗大伙开心,驱散沉闷,那年妇女车间里没死一个人,许燕吉因此记了一大功。
“麻花虽经扭曲油炸,仍不失可口。”许燕吉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一生。痛苦和不幸没有成为摧残她的东西,而是变成了生活的力量。
写完一生的故事,许燕吉说,历史有的不只是大人物、大事件,更多的是普通人的辛劳、痛苦和隐忍,“那是历史的伤口,也是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