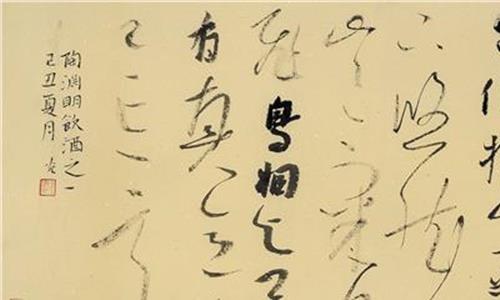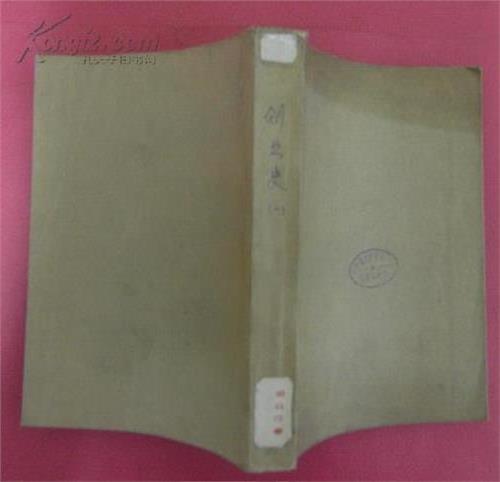后人对谢灵运的评价 著名作家鲍鹏山散文名篇《生活在别处:谢灵运》(下)
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后,有一段类似于中国文学史概说的文字,他可能隐约觉得谢灵运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我的这组文章至此,也将告一段落——既是我在《寻根》杂志一年连载的段落,也是一个自然的段落:从汉末党锢至陶、谢,也是一个完整政治历程。我们略作回顾。

党锢群英实际上是一群政治精英。他们试图恢复政治秩序和权力运作规范,从而维护皇权的纯洁性,维护皇权与士大夫的联盟,维护政统与道统的和谐。但不幸的是,破坏秩序和规范的正是皇权自己,宦官权力实际上是皇权的自然延伸。

因而,他们和宦官的生死搏斗,就必然冒犯皇帝。这里用得着一个成语:投鼠忌器。宦官之鼠隐身器侧——这岂是一般的“器”?这是神器。结果便是,清流士大夫们要投宦官这个“鼠”,却往往不惜冒犯也不得不冒犯皇帝这个“器”。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必然失败。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被排除在政治之外,他们遥望着政治,遥望着政治权力后面的富贵荣华,流着一丈长的口水。但政治权力于他们,乃是“禁脔”,哪容他们染指?所以,他们只有艳羡与嗟呀,甚至连野心都不敢有。他们是在精神上被挫败而让自卑压垮的一群。

到了建安时期,情形为之一变。社会的大变动,旧有秩序的崩溃造成权力、地位、财富的再分配,建安作家在经过颠沛流离之后,一下子成为身处政治中心的人物,并且与最高权势者有良好的互相信赖与支持,甚至等同僚友,一时间他们焕发出了极高的政治热情。
而正始作家呢,他们虽一样处在政治中心,但由于权势者内部矛盾的激化,他们所支持的偏又是注定要灭亡的腐朽的曹魏,他们所厌恶的司马氏却又大权在握,操纵一切生杀予夺,这不能不令他们尴尬而进退维谷: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者吾不及,来者吾不留。
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
(阮籍《咏怀》三十三)
王闿运说此诗的意思是表明自己的态度:“不为魏死,耻与晋生。”(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引)到了这个份上,当然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从而显示出对政治的一种离心力。这种离心力显示了阮籍及其他正直的正始作家的一种政治品格:当政治演变为权力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时,这种政治已肮脏不堪且残酷无比。如果无力改变这种现状,只有高蹈远引。嵇康与钟会的矛盾以及他后来与山涛的绝裂,就是因为钟会和山涛缺少这种政治品格。
概括地讲,建安作家和正始作家都是关心政治的,但关心的内容不一样了。关心的目的也不一样了。建安作家关心的是政治中的正义原则,他们关心的是建立一个清明和强有力的政治,从而建立一个公正而稳定的社会。因此,他们关心政治的目的是为了平定天下,廓清宇宙。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王粲《七哀诗》)就是对有力而清明的政治的呼唤。而正始作家关心的是政治中的权力斗争,以便窥测方向,保住生命,躲过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政治斗争的风浪袭击。
“万事无穷极,智谋苦不饶”(阮籍《咏怀》三十三)就是对这种变化无常政治斗争的无可奈何劳神竭虑的应付。建安作家是不大谈哲学的,他们有现实的具体的事要做,满目荒芜需要他们去清理与开拓;正始作家却大多趋于玄思。
象阮籍“发言玄远,口不论人过”,现实已不容他们多嘴多舌评头论足,他们便只好退回书斋或小场合(如竹林),养起哲学的盆景,精致固然是精致了,但也失去了建安时期春色满野的大气象。“建安风骨”在内容上的特质——对社会大乱的真实描写及建功立业的抱负,在“正始之音”里,便为另外两种特质所代替——忧生之嗟和愤怨之情。
建安作家是不大感慨自身遭遇的,只把自身遭遇作为黑暗社会无数不幸的一个例证来写,落脚点仍在感慨社会,是对社会的愤怒控诉。
女作家蔡琰便是如此。正始作家呢,他们不敢有任何政治作为,也不敢控诉谴责任何人,只好在抽象的人生痛苦中徘徊,退避竹林,于洒酣耳热之际扪虱而谈玄理,或中夜不寐,于清风朗月之际独怆然而涕下。
此时的政治,不但不能用来建功立业,反而是一把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之剑,随时可以使他们人头落地,对政治的信赖荡然无存。所以,阮籍说他要“上与松子游”或“乘流泛轻舟”,这也就是陶谢远避政治的伏笔了。
西晋,仍在政治中心沉浮挣扎的人纷纷灭顶,如张华、陆机、潘岳、石崇等等,这些人都很难说他们有嵇康阮籍那样的政治品格。而试图进入政治中心的不知深浅天真热情的乡巴佬左思,虽然自以为才兼文武,德行高尚,仍不免在无公正的政治厚墙面前碰壁而死。
他还有些不满与抗议,这是他的价值。而大多数同时代人,其中很多是他的朋友们,则连对政治的不满与去意都没有了,他们既不象建安作家那样对政治抱有信念与热情,也不象正始作家那样对无道无秩序的政治抱有反感甚至反抗,他们若有不满,那是在政治分赃中分得不够多。
山涛、王戎、张华等人都已成为政治大员,连陆机也曾统领过二十多万的大军,超过了乃祖乃父,在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已经成为管仲乐毅式的人物。
张华在他的诗作里还表现过一些谦逊及对官事鞅掌的厌倦(如《答何劭》);而陆机,这样一个以作家名世的人,这样一个经历了杨骏之乱、贾后之乱、八王之乱的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而最终灭顶其中的人,在他的诗赋中竟无一语道及时政。
他不是一个远避政治对政治麻木的人,他也不是不在乎他在官场上的沉浮,但他的作品中就是不涉及政治。为什么?很简单,他内心里颇不以政治为然,他把文学看成是雅的,是关乎德行人品的,而政治则是脏的,政治已经肮脏到不能成为文学的对象了。
在诗赋中涉及政治,就是亵渎文学,是政治对文学的猥亵。就他保护文学的贞操这一点而言,他比用文学去歌功颂德的潘岳之流,还是有值得褒奖的地方。陆机内心对政治的评价及他热衷于官场的态度,显然可以看出他已经把政治看成一纯然谋求功名富贵的工具。这不是理想的政治,这种政治已经没有理想,只有欲望。
这种政治是“站队”政治,站对了队,就富贵胜达,站错了队,就人头落地。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张华在废贾后问题上站错了队,潘岳、石崇错站到了贾谧一边,左思一直没有站好队,他总是若即若离,所以谁也不喜欢他,可谁也不把他当成敌人。
陆机错站到了成都王司马颖一边——不过,谁能永远站得对?官场既如翘翘板,城头变幻大王旗,今天对了,明天就未必对。今天杀人,明天被人杀;今天我整人,明天人整我。我们还是别太过分指责他们,给他们以怜悯吧。因为这样的政治让我们身处其中,也会首鼠两端,无所措手足。我们不缺少这样的体验——道德堕落往往是政治逼的。
有了这样血写的历史,陶渊明与谢灵运对政治的逃避也就不难理解了。陶渊明创造了“尘网”这样的词来指代官场,包含了肮脏和凶险两层意思,这是他对当时政治的感受与概括。于是他由避人而避世而避喧,完全隔绝于政治之外;谢灵运也试图用逃避的方法来舒解内心中对政治的的失望和残酷政治斗争造成的焦虑和紧张。他未能做得像陶渊明那么彻底,一步三回头,反复无常,终于还是死于政治斗争。
综观以上文人与政治之关系,可以这样说,关心政治是有多种方式和多种目的的。以上古诗十九首、建安作家、正始作家、西晋文人就给我们提供了四种范式:关心政治权利背后的荣华富贵、关心政治中的正义原则、关心政治中的权力斗争和站队政治。
这后两种没有明显的界限,关心权力斗争就是为了决定自己站在哪一边。区别在于,正始作家决定站在哪一边时,考虑到了正义,如嵇康、阮籍,特别是嵇康,他是自觉地站到必然失败者的一边,而承受个人毁灭的。
而西晋文人的站队则纯然没有是非,只有得失。中国古代文人是几乎没有不关心政治的(只有像陶渊明那样在关心中失望而逃避的),但有价值的关心有多少呢?或者说,真正以政治中的正义原则为关心对象和目的的又有多少呢?即使有,又有多少不遭流放,贬斥甚至杀戮呢?
三、四世纪的文人在政治问题上走了一个怪圈:由古诗十九首的渴望进入政治中心而最终到陶、谢的试图走出政治中心。他们在政治的漩涡中亢奋、畏惧、颓丧甚至堕落,然后又在这种堕落中清醒。这是一个大大的怪圈,发人深省而后人又没有真正深思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