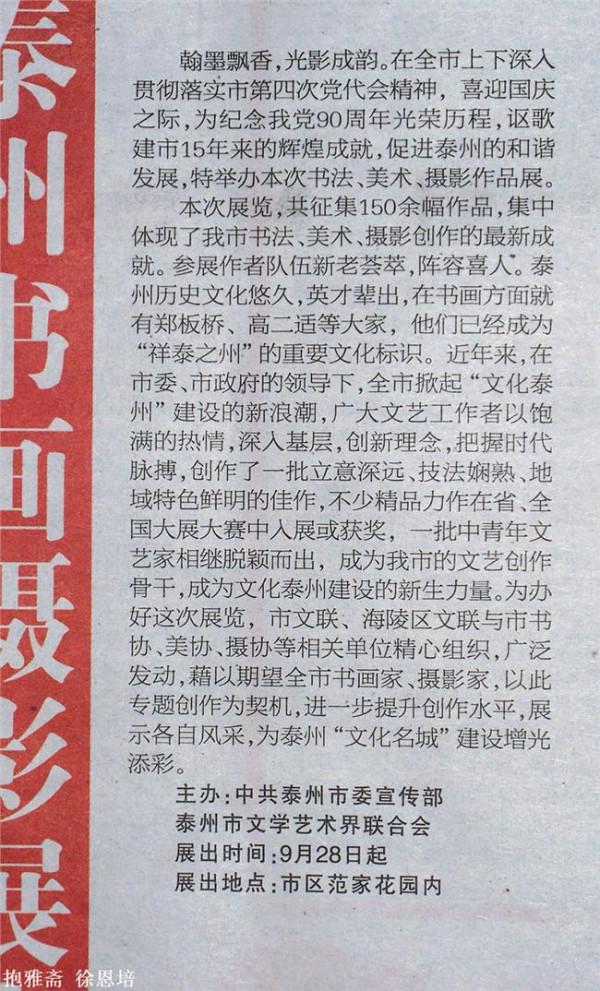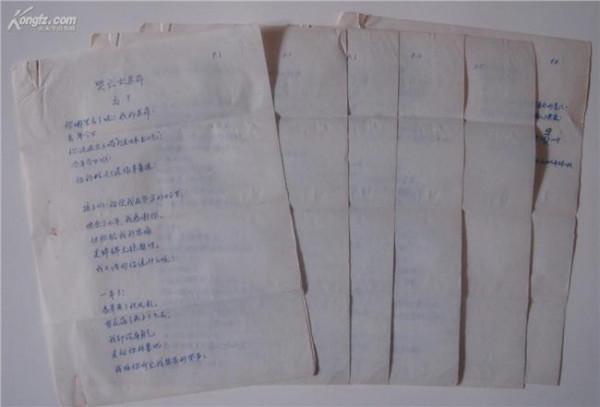少年说梁启超 梁启超逝世90周年:知我罪我 让天下后世评说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家喻户晓,他既是清末民初的政坛重镇,也是其时的学界枢纽。对于后来者而言,阅读梁启超也就成为进入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场并把握其间内在逻辑的绝佳方式。
政治活动家梁启超以“善变”闻名。清末民初的国耻世变中,他的政治生活云变波折,政治活动大多数并不成功。梁启超严于自我省察,其“善变”是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辞世后,墓碑上未写任何生平事迹,“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梁启超在其不足五十七年的个人生涯中,留下了不下1400万字的各类著述,几乎涵盖了近代中国——这一被他称为“过渡时代”的历史阶段——的所有重要议题。凡诸政治、经济、思想、学术、社会、文化、教育、出版等领域,皆有其建树存焉。

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文字,更是已经超越了个人观察与思考的层面,直接而深刻地介入到了历史进程的肌理与脉络之中。他一方面积极入世,另一方面又自觉追求在“实事的理论”之上建构具有穿透力与启示性的“理论之理论”,因此在知行的双重维度上都为这一云谲波诡的“过渡时代”提供了一个不得多得的意义坐标。

梁氏之一生:变中求索的时代图谱
梁启超以置身“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人物”自居。1873年出生的他,在晚清政治改良运动中,以康有为弟子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1896年,他出任《时务报》主笔,很快便凭借其汪洋肆恣的系列政论文章《变法通议》而成为一代舆论巨子。不久,康梁即开始并称。在随即展开的维新运动中,梁启超大显身手,奠立了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先后创办了《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继续发挥其引导舆论的优长。与此同时,他在日本近代文明的冲击下,“思想为之一变”,开始逐渐从康有为的笼罩中独立出来。这一时期,在《新民说》等文章中表达的“新民”主张,是其基本的思想立场。
他将“新民”作为建立现代国民国家的首要任务与根本途径。在他看来,“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梁启超在流亡中的政治实践与学术活动也直接受此支配。在《新民丛报》时期,他达到了个人生涯的巅峰,此后在二十世纪中国登场的各家各派,几乎无不受其影响。
但在1903年后,梁启超的号召作用却大为下降。革命在其时日益成为共识,而在他的“新民”体系中虽然也有激进面向,但与章太炎等人提出的“以革命开民智”的行动方案相比,终究十分不同。此时的梁启超认同“开明专制”,而与清政府中的立宪派秘密接触,并为“出洋五大臣”代拟宪政折稿,正可见出他的这一努力。
1912年民国鼎立,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活。回国后的他主张“不争国体而争政体”,在尊重共和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政治改革。他先后出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与财政总长,参与“倒袁运动”,反对“张勋复辟”。在众声喧哗的民初政坛上,以他与蔡锷为代表的“青年支那党”一度被日本方面认为是“支那将来永远的中心势力”。至此,他在思想立场上也与康有为彻底分道扬镳。
不过,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却大都并不成功。意兴阑珊的他,最终在1917年决意退出政坛。次年他出游欧洲,开始反思西方现代文明。1920年归国后,他形成了自家的“新文化运动”思路并投诸实践,同时完成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多部重要学术著作。1925年,他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与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导师,此后在教学与著书中更加勤勉,直至1929年不幸病逝。
当然,晚年的梁启超也并非与政治绝缘。且不说其学术与文化关怀的背后多有政治追求,仅是1919年欧游途中助力“五四运动”的开展以及推出“党前运动”的构想,便意义深远。
在清末民初的时代风云中,梁启超可谓“善变”,时人也因此对其多予诟病。但倘若放长视线,则不难发现其变中亦有不变。其所“不变”者,大略约有四端:一是始终坚持“新民”主张,毕生致力提升国民素养;二是以政治与学术相互发明,将“议政”与“论学”彼此熔铸;三是在心态上兼及“觉世”与“传世”,追求“常识”与“创见”之统一;四是借助其“新文体”,通过与现代报刊而合作产生广泛影响。
梁启超的一生纵横捭阖,波澜壮阔,可谓一部变中求索的时代图谱。其涉及的面向之多与层次之广,在二十世纪中国即便还有能出其右者,恐怕也实在不多。平生如此,称得上完满。但如果细究,则无论其从事的事业,还是提出的命题,却又多属未及完成之列。是故,梁启超也在近乎天然地召唤后来者。
梁启超研究当然首先是一种历史研究,其旨归在于还原一个真实的“梁启超的整体形象”。但不应忽略的是,由他命名的“过渡时代”事实上迄今尚未结束。所以,阅读梁启超也就是一个与之展开精神对话并从中汲取思想资源的历史过程。不同代际与立场的学者都可以在其间带入各自的时代命题,探求取法与出路。换句话说,梁启超研究正是对于梁启超的思想脉络与精神传统的接续与阐扬。
2016年6月,梁启超研究史上的名著——美籍华裔学者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的过渡(1890-1907)》再版推出。此书英文本初版于1971年,其命名受到了梁启超的《过渡时代论》的影响,而其核心观点是发生于1890年代中国的改良运动是“一场真正的思想运动”,自此“西学和传统文化之间建立起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交流”。
在张灏的论述中,梁启超的意义在于其“可被看作是古老的儒家经世致用传统和当代寻求新的思想方向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纽带”。此说经过日后数十年的反复检验,如今已然成为共识,但在当初立论的北美学界,却堪称“创见”。
在“二战”以后北美的近代中国研究中,费正清建立的“冲击-反应”的阐释模型一家独大。这一思路以西方的知识观念与制度经验为现代化的唯一标准,认为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是在西方的冲击下不断作出反应的产物。而在张灏看来,费正清模式对于中国自身的能动作用与更新能力的估计严重不足。而梁启超作为儒家经世致用传统的当代传人,其一生在思想史上留下的屐痕正显示了中国文明本身具有的潜质与活力。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既是一部梁启超研究的力作,同时也是张灏个人学术生涯的起点。在完成梁启超的个案之后,他又对同一时期的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与刘师培进行了深入研究,集成《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1890-1911)》。
两书合而观之,其反思西方“现代化”理念的用意便十分明显。道德精神与超越意识是在中国历史转型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两种价值内涵,但为西方“现代化”理论奠基的韦伯的“理性化”概念则在其中无处容纳,而在梁启超等人身上这些面向正有集中体现。
此后,张灏又相继推出了《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与《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两部中文本著作,以梁启超研究发端的近代中国思想史论述大致完成。如果说“中国思想的过渡”是梁启超以“历史中人”的身份对其所处的历史进程作出的敏锐感知,那么张灏即是以同样具有历史意识的方式对此进行了认真重审。其间有学术推进与思想创获,也有作为海外学人的家国情怀与遥深寄托。
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再版推出之际,日本学者狭间直树的《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也在同月问世。两者尽管一再版、一新刊,但在追寻梁启超这一“过渡时代”的意义坐标,且从历史经验中抉发当代启示的层面上却是异曲同工。同时,两者之间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对话关系,更是饶有意味。
狭间直树是日本“京都学派”在“二战”之后的重要代表人物,以主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梁啓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共同研究班(1993-1997)、出版报告论文集《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参与日文版《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编注工作而著称。
《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是其2012年秋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所做“梁启超纪念讲座”的讲义。全书计有正文八讲,附录三章,原题“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以梁启超与日本在文明史上的关系为中心”,所有内容紧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凸显了这位日本学者的学术敏感与研究专长。
讲座评议人张勇称道狭间直树治学具有一种“细密”功夫,而这也正是学界对于高水平的日本学者的普遍印象。此书在这一方面自然堪称“本色当行”,其首要贡献便是在若干梁启超生平与思想的关键问题的考辨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例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以后流亡日本,不久他便开始从康有为的思想覆盖中独立出来。对于这一现象,学界通常以其逐渐形成的“国家主义”主张与康有为的“世界主义”理想发生冲突进行解说。但狭间直树通过校勘梁启超其时撰写的两种《谭嗣同传》——《清议报》本与国民报社的《仁学》单行本,发现“康梁关系演变的背后还有另外一层围绕谭嗣同的纠葛”,从而将两人的思想角力落实到了现实层面。这是以往梁启超研究中少被提及的关节。
再如,狭间直树经由考察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的笔名使用情况,揭示了其散落在不同栏目中的文章原本具有的有机联系,整合出了其在这一时期以《新民说》为主体的思想体系。他进而作出判断,伴随着“中国之新民”这一主要用于写作《新民说》的笔名被弃用,后期的《新民丛报》“已经不是刊登《新民说》时候的《新民丛报》了”,不但栏目进行了调整,“性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还有,在细读梁启超完成于东渡期间的国家构想时,狭间直树十分注重辨析其使用概念的实际意涵。他发现,梁启超笔下的“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等词汇的含义不仅与当时及此后的一般用法不同,在其思想演进的不同时期也存在差异。具体而言,梁启超此时提及的“帝国主义几乎相当于今天专业术语的绝对主义”,而“民族主义大约等同于国民主义”。这些发现对于准确理解梁启超的国家观与国民观无疑十分关键。
对于梁启超为何在1906年选择迁居须磨,长期未有恰如其分的解释。须磨是位于神户郊外的偏僻村落,远离当时日本的政治中心东京。作为寓居日本的中国政界的核心人物,梁启超此举可谓反常。在狭间直树看来,这与其秘密为“出洋五大臣”代拟宪政折稿直接相关。在浅原达郎与夏晓虹的研究基础上,他指出“梁启超移居须磨,对应的是与预备立宪一起产生的他与清政府关系的变化”,赋予了这一事件以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凡诸此类妙笔,在《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中还有很多。狭间直树善于见微知著的学术功力,由此也可见一斑。此书通过细节处的考辨与阐释缀合了梁启超思想展开的历史现场。在梁启超的思想探索、个人出处、时代语境与历史进程四者之间,狭间直树建立起了一种有效的内在关联。这也就使得全书在立意与用心上超越了一般意义的考据之作,其背后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追求随即呼之欲出。
狭间直树认为“如果用一句话来介绍梁启超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称他为将中华的传统文明改造为近代文明的功臣”。这一判断无疑与张灏所见略同。而这也就使得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的延长线上阅读《东亚近代文明中的梁启超》具备了可能。
张灏的研究策略是通过整合梁启超的个人著述建构其思想世界的“内部视景”。尽管他已经注意到,晚清思想改良运动得以成为“一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化运动”得力于“一种新式报纸的出现”等外部因素的催化作用,但由于兴趣及学术条件等方面的缘故,他并未对此展开考察。待到狭间直树处理这一问题时,“内外兼修”已经成为必由之路。
当然,报章媒介与域外资源等角度的引入,并不仅是策略层面的调整。例如,狭间直树对于“梁启超与日本在文明史上的关系”的探讨,就远未止步于开掘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虽然梁启超的“文明改造”工作在很多时候都以明治维新以降的日本近代文明为触媒,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只有“影响-接受”的简单对应。
梁启超的“过渡”作用既体现为呈现了世界史视野中的“近代”是“西方文明领先并影响世界”这一基本态势,更突显了东亚在这一潮流的激荡之下发生的更为复杂的实际状况。狭间直树对此加以重新认识与发凡的努力,表现为他从张灏式的“思想史”研究到自家的“文明史”框架的移步换形。
狭间直树从中日两国“语言和文字、文章”的等级秩序出发,将“东亚近代文明史”划分为了“始发期”、“发展期”、“成熟期”与“决裂期”四个阶段。梁启超的主要活动集中在1895至1919年间的“成熟期”,但他与“发展期”和“决裂期”的兴替也具有重要关系。
前者是中日各自发展的历史阶段,这也就决定了置身其中的梁启超在学习日本的“洋学”时,旨归其实是在对抗两国共同面对的“西学”带来的压力。因此他对于“洋学”的理解与接受自然受到其“西学”想象的很大影响。
而梁启超在民初调整了对日态度,从“觉日人之可爱可钦”转向“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也对1919年后“决裂期”的悄然来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梁启超的个人选择,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东亚近代文明史”的走向与展开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狭间直树既超越了现代国民国家的理论视野,立足于东亚文明的整体视景中对梁启超加以审视与考察,同时对于中日之间在文明层面上的对话与互动也多有观照。例如,与梁启超改变对日态度相伴生的,是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在“一战”以后对于本国侵略政策的支持。
而狭间直树却注意到,在这一情形下,仍有吉野作造等人坚持应“以更大的同情和尊敬对待支那的事情”。在狭间直树看来,“‘同情和尊敬’是现代化人际关系的根本。由于吉野确立了这一基本精神,所以他在中国的革新运动中发现‘活着的精神’的时候,能够与这些运动者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所谓“活着的精神”,指的正是其时活跃在中国政坛上的包括梁启超在内的“青年支那党”的力量。狭间直树的发挥,俨然是在追寻一种思想经验的当代启示,从而对其自身感应到的时代命题作出郑重回应。
“过渡时代”的魅力在于其面向未来无限开放。而梁启超在百余年的中国思想与东亚文明的历史实践中得以始终“在场”,凭借的正是其包孕的思想能量。在近半个世纪中,从张灏到狭间直树的不断阅读与阐释,对于这一能量而言,既是汲取与释放,也是累积与涵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