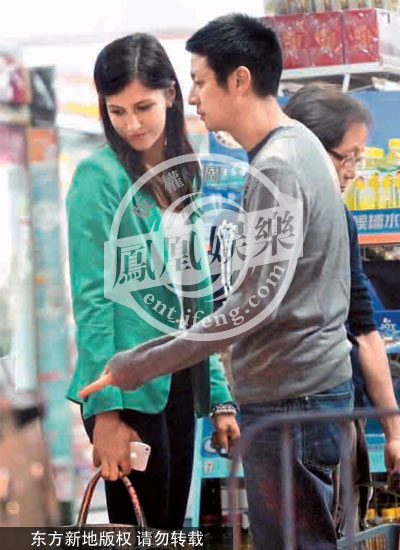陈丹青:我是一个职业的“抄袭者”
陈丹青:总得用一点。因为我是画画的,所以总是离不开图像。比如我说鲁迅好看,也是跟他照片有关。那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五四时期人物照片给我的印象,我第一看到的时候还是小孩子,可是小孩子也会有判断,鲁迅的八字胡一弄挺好看。现在我对图像的看法当然比以前多得多,我总觉得有一部分我认知的事物,实际上是图像告诉我的,文字再说也没有用,它不顶一张图像。中国古人写文章时写着写着就说“有诗为证”,我写着写着是“有图为证”。有时候看郭沫若或者林语堂的脸,呼之欲出觉得林语堂是这样的性格,但说不出来,可将图片往那一放,大家就一眼明了他是这个性格。
主持人文坛:所以新书里有很多图片,以便让网友品读图片的时候品读鲁迅,是这样吗?
陈丹青:在我谈到的人事当中,只要有图片,我都愿意放。假定读者当中可能有一个人跟我小时候一样,看到图会是那样一个反应。模样对我来说性命交关。因为人类对样子的需求比文字要早,图像史比文字史早大概好几万年。我相信一个动物在看东西一定跟人一样,动物虽然没有文字语言,但是它非常清楚危险迫近了,主要靠看。我到现在一直信赖对图像的辨认和判断,让图像跟文字在一起发生,会让这本书更有意思。
主持人文坛:说到鲁迅,前段时间在网络上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事情,就是同样写鲁迅的汪晖的“抄袭事件”,不知道两位老师关注过这个事情吗?
张大春:我到了上海、香港、北京,朋友们都提这个事情,我们对前后文不是很清楚。我跟汪晖先生过去有过一小段时间在香港的认识。他是一个极有发明能力的思考者。我觉得一个人的学术成不应该单纯地从某一个个别的片段上去做整体的论断。我看到了某一些引述,我觉得他所谓的“抄袭事件”,其实属于用典式的抄袭——把那个典故放在某些论述里,或者说改变了原先典故的样貌。这个你要说他是假的,那毫无疑问在学术严格的规格上面来讲,他这样比较大名气的学者,看起来有思想家架式的人,这个错误似乎是好像伤害很大。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包括台湾的某一些随时在报章杂志上移译或者介绍西方的某些思潮、论点,甚至成套成套的理论架构的学者作家,也常常做这样的事,只是大家会注意怎么样让自己的借用和转用看起来不着痕迹,并且有的时候还带点发明的意味。我不是一个学术人,所以我没有学术规格上的严格的禁忌。用典好像也是中国人从古以来都在做的事,而且大家也挺习惯用典。学术界有他的判断,我是平常人,我有我的判断。
陈丹青:您可不是平常人,你非常会用典,一肚子的典故。用典和抄袭是两回事情。我没有看过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我也没有看过汪晖先生的其他著作。所有学者的文章我都没有看过,抱歉。我在他们的范围里,我无法判断这件事情是有还是没有,甚至是对还是错。 我只能告诉大家我自己是一个职业的抄袭者,至少我从1989年开始到现在,几乎所有我自己的创作,而且可以说中年以后最重要的创作全部是在抄袭,全部是抄袭经典的、古典的绘画图像,如巴罗克的绘画等。还有抄袭新闻照片,抄袭我所能找到的,我认为值得抄袭的图片,非常多。但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你这是抄袭的,会在下面标明这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出于道德,而是告诉大家我在抄袭。而且这是有道德支持的,这是后现代的被确认的一种方式,他们有个词叫“挪用占有”。所以在这方面,如果你可以换一个词叫“抄袭占有”,也可以。我是职业地在做这件事情。而且我特别喜欢抄袭,我说过如果我老后实在没有创作力,我最希望做的事情就是去临画。我刚刚从俄罗斯回来,大概抄袭了30件以上的董其昌的东西,我自己就是喜欢,我没有道理,在抄袭过程中,我像董其昌一样好。
张大春:我最近在写毛笔字,练书法,也有这样的体会。我读帖大概有30年,几乎天天读,在家的时间,每天晚上会读帖,有的时候读几个字,有的时候不见得临,现在养成习惯,说话的时候手都会临。这个“临”感觉会让你更贴近原创者,原苏东坡、米芾,猜想他是使用硬的笔、软的笔,毛笔是长的还是短的,笔如果转了的话,转了多少角度,这种“临”好像比创作还要灵。
陈丹青:相当于从生理层面进入身体,把它再嚼一遍。我非常向往罗兰·巴特用引文来写作,从不同的作者来引,他自己也没有做到。我最近刚刚做了小的尝试,去俄罗斯给画家写一个游记,在写以前,就想好了,要用所有的托尔斯泰引文穿起这篇文章来,大部分是我自己来写,如果没有他的引文,会乏味很多,我也没有资格谈这么大的俄罗斯,但是很多事情我觉得他谈得太好了,我得停下来听托尔斯泰是怎么说的。但是我不知道用得好不好,这些游记我正在写,没有写完,上篇已经发表了,下篇正在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贝贝特总编辑刘瑞琳
刘瑞琳:贝贝特为何要举办“理想国文化沙龙”
主持人文坛:刚才谈了作品、谈了关于抄袭,接下来还要谈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开始的时候说得“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刘老师刚才一直在倾听,现在特别想听听刘老师怎么说。作为出版社,去做这么大的年度文化沙龙,真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刘瑞琳:说起来其实是水到渠成。因为有这么特别好的作者,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于是想到做一些日常的都是沙龙式的互动活动,比如我们会在今日美术馆、一些小的书店及其他场所做读者和作者的见面会。另外每年在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生日的时候,公司都开party,设媒体专场,大家坐在一起自由聊天,这两个结合起来,就是年度沙龙。只是从一开始做到现在,今年想把它做得更有开放性,更有社会性,才有了“理想国文化沙龙”的想法。
主持人文坛:为什么不叫“贝贝特文化沙龙”而叫“理想国文化沙龙”?
刘瑞琳:“理想国”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要做的一个重要品牌。广西师大出版社在出版书籍方面得到同行的普遍认可,但是在出版品牌方面,如果想做更多的事情或者能有更大的发展,可能需要有一个更具包容性、前瞻性,同时内涵更丰富的文化品牌,我们就想到叫“理想国”,为什么选择用“理想国”?我们感觉它应该能把跟年轻人的心相互感应,相互沟通,因为这个词是固有词。我们现在用它是想跟原来的意义有所区别。我们的理念是“想象另一种可能”。这个意思不是说理想国要倡导某一种理想或者要给人一种类似乌托邦似的东西,什么意思呢?比如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但是让我们想一想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是这样的意思。 这样的意思,我们觉得是年轻人愿意思考和想象的,“理想国”对我们来说是开放性的,每个理想都是平等的,很多很多理想聚在一起,五彩斑斓,那就是一个理想国。
主持人文坛:所以这次活动很庞大,有这么多名家对话,包括大春老师要跟小宝老师对话,丹青老师要跟谢泳老师对话。
陈丹青:不一定会庞大,但是会蛮丰富,因为请来这么多人,每个人都不一样。忽然将他们聚到一起大合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声部。
主持人文坛:那将会是一出很好的交响乐。在台湾也有“印刻文学营”等等,丹青老师之前可能也参加过类似的沙龙,对这次“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两位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对这样的文化沙龙的形式有什么样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