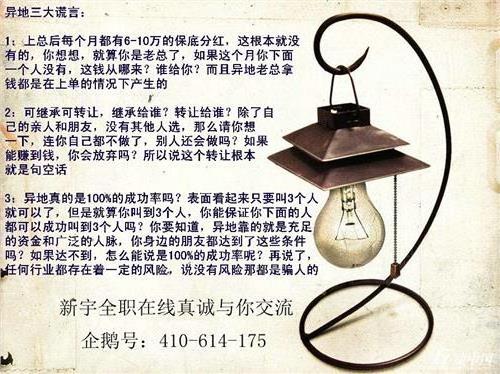国民党反动派 国民党分裂真实内幕:派系争斗各为私利
我租房住在武昌,房东住在后层,我家住在前栋,临时把屋子大门钉牢,利用后门出入。这样从大街上看,好似一所空宅;后门又非常隐蔽,可以避免许多麻烦。开城之始,进城的唐生智部军纪就非常的坏,有两个下级军官模样的人闯入我住的地方,说这房子很好,我们借来用用,随手又把房东的被子拿了两床;走到客厅看到我挂着谭祖安(延闿)的对联,就问我“你认得谭军长?”我说是的,他们才拿了被子离开,要不然,乱子不知要闹多大!

当时宣传革命军军纪如何如何好,我亲见这种样子,心里很是难过,就赶紧搬家到汉口贯忠里六十号,张南皮(之洞)第九公子住六十一号,人称张老九。
后来共产党人捉我张怀九,却误将张老九捉了去。那时一切都是共产党的作风,学校解散了,秩序紊乱,人身安全也谈不到。

到处充满恐怖。报纸上又登刊所谓“不革命,反革命,假革命”的口号,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被安上一项罪名。就是与他们混在一起的人,也很可能给套上假革命的帽子,受到生命的威胁。我又看到报上刊出什么“怀九派”,就赶忙弃家乘小驳船离汉口。
还记得围城之中,我现在在美国的那个小孩出生,连接生的人都找不到。度过那种生活,回想起来真是不容易。
十六年九月宁、沪、粤三方面合作,汉口方面的中央政府瓦解,左倾人士离开,谭祖安(延闿)、李协和(烈钧)、居觉生(正)、邹海滨(鲁)等都到南京,组织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成立后改组各省省党部,不久发生讨唐(生智)之役。后来讨唐军事进展,底定武汉,国民政府特于武汉成立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任程潜为主任委员,我受命为委员兼民政处长,那时上海法政大学甫经恢复,规模粗具,匆遽离校,不胜依依。
湘鄂临时政委会第一次开会,程潜就和我争吵一番。原来我提出该会组织条例,他说我们搞我们的,要什么条例。我说没有条例,就没有法律根据。他又说要什么法律根据。我气愤退席,他的秘书长李某再三来说好话,他本人也来说好话,次日我才继续开会。程潜颇讲权谋术数,他与湖南军人叶开鑫、何键接头,想要他们拥护,自己另成一套。不料给第四集团军的人知道了,就进军湖南,把程氏企图中的力量消灭了。
(二)我和桂系的关系真相
十七年五月,湘鄂政务委员会撤销,武汉政治分会成立,由李宗仁任主席,我及程潜、白崇禧、胡宗铎、张华辅等为委员,此为我与李相识之始。
第一次开会之前,各委员在休息室交谈,听到摇铃开会,进会议室坐下,但李宗仁和程潜迟迟不来。等了半个多小时后,李宗仁忽然进来说:“程潜反革命,我再三劝他做第四集团军副司令,住在汉口,他一定要做湖南省政府主席,并且说不给他做主席,他也要做。我现在已经关起了他,希望大家赞成。”
现在讲起来很滑稽,但当时我们都大吃一惊,默默不讲话。我心中却大不以为然,无论如何,总不能把一个委员就这么关了起来,在座大家都是政委,以后安全又有什么保障?倘或议论不合,难道不步程潜后尘?当晚想到深夜,我没有睡着。我当时对李宗仁的批评,是“质美而未学者也”。后来我起草宪法时,所以提议军人退伍未满三年者不得任行政长官,也多少受到这次程潜被关的影响。
先是十六年十一月,蒋先生自日返沪,十七年一月复自沪抵京,宣布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准备再度北伐。四月间,任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其时阎锡山之第三集团军从正太路,冯玉祥之第二集团军从京汉路,蒋先生亲统第一集团军从津浦路,均开始向北方攻击。
白崇禧时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有一天来省政府(按:张知本先生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详见下章)对我说:次日即须领兵北上,希望我立刻筹借军费五十万,供发饷之用,准于一周内归还。时省库财政困难,只湖北堤工经费保管委员会尚有存款,白崇禧希望我去挪借。
我说:“那个机关不属省政府及水利会管辖,省府无权动用他的存款。而且最初所以如此规定,也就是为了增加它的独立性,避免经费受到挪移拉借,水涨时无从应急。如果现在开一先例,以后来的援例借用,则此一机构体制将完全破坏。”
我又说:“既然你负责一周归还,可以向银行去借,由我作保。”当即邀约银行界人士,三方面当面说明此事,将五十万军费如数借到。
白一周内果然予以归还,这也许就是我和桂系的一点关系,足见当时军界人士不乏明情达理者。后来第四集团军和一、二、三集团军会师北京,白崇禧率领军队一直打到山海关。
十八年初,国军编遣会议开会,李宗仁赴宁出席,不久即到上海。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由我代理。李到上海后,通电要蒋下野,电文上由他领衔,把我名列第二,世人以为李不通文字,电文必为署名第二的我所草拟。其实这个电文是郭肇黄所作(事后据他们说),郭在汉口总商会任职,我事前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我认为即使是蒋先生不好,也不应以武力解决。李宗仁通电发表后,武汉政治分会开会,我向军界人士询问事态真相。
据他们说,在江西袁州地方搜获到蒋给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一封信,并附有一百万现洋及枪械,说是帮助他“剿除”共产党。他们认为“剿共”只是幌子,用意是要对付第四集团军,先接济鲁涤平,准备动手。他们以为:湖南受第四集团军方面节制,真心“剿共”,为什么不经由正常指挥系统,偏要由江西偷偷进行?我则问:对付方法很多,何必先军事行动?他们却说:我们不动手,他们先发制人,就要编遣我们了。
后来蒋先生写信给胡宗铎,说明他对武汉并无歧视,要他代为解释,免动干戈;信后并附笔“怀九先生处请代致意”。
此信由岳阳交涉员李芳转交,李是湖北法科大学毕业,是我的学生,他不敢将信交给胡宗铎,先来看我,由我打电话邀胡来。
见面后李心怀恐惧,解释道:“我只是传信的人,因为我是湖北人,希望家乡不要打仗,所以来送这封信。”
胡看信后说中央已下讨伐令,我们已经通电要蒋下野,现在私相授受,事情不简单。正谈之际,陶钧进来,怒气冲冲,认为这样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先去找他。李芳非常害怕,我又为他缓颊,晚上叫他睡在我处,等第二天再走。睡了一刻,李芳爬起来说,此行任务已经达成,还是立刻离开的好。我说你自己想想决定,在我这里没有人会来为难你的,但如果不放心,现在走也可以。他就当夜走了。
十八年三月,中央讨伐桂系军队未至武汉前,李宗仁部下都已跑走,我太太到他们那里去看看他们怎样打算,才发现房子空空如也。这样我们才找房子搬家,我个人预备将书籍文件稍加整理,几天后再离开武汉。
这时蒋先生有信给我,托贺国光转交。我有一个在湖北省党部做事的学生,以为鄂省军政分治,我在政治上成绩好,蒋先生有意要我继续帮忙,是件好事,于是他自告奋勇,带着信来找我。
我说:“你去见贺先生,就说没有找到我。这两天报上大骂桂系,如果我附和着也骂昨天的朋友,说不过去;如果我不附和,省主席又如何做法?颇难接受此信,不如你就说人没找着,将原信带回去。”
这位学生走后,我书也不理了,抱着沉痛的心情,马上乘轮离汉赴沪。
我以为国民革命军分裂,无异为共产党造机会,区区之愚,犹冀留双方他日复合的余地。
以上是我和所谓桂系的一般关系,其中有许多地方是外人很少知道的。我说的话绝对负责;不过当时桂系是反共的,站在这个立场,我与他们合作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三)扩大会议
我在上海,曾受到第二次开除党籍之处分,乃避居租界,亦欲趁此空闲,潜心写成若干著作。适会文堂编印法学丛书,约余写宪法,先给稿费壹仟元。当时参考书仅一、二元一本,我用这笔钱买了几百本书,包括日本各派的宪法理论,及译成日文的各国宪法著述。
我先把这些书全部翻阅一遍,摘出要点,然后才动笔撰写。此一阶段,是我一个很好的研究机会,除《宪法论》以外,后来还写成《社会法律学》、《民事证据论》、《土地公有论》等书。至于《破产法论》则写成较晚。
十八年四月离鄂以后,五月到上海,经十九、二十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其间经过扩大会议、中原大战,直到宁粤合作,第一、二、三届中委合并,我才到南京。
我之参加扩大会议,还是覃理鸣等人的关系。汪精卫因为西山会议的关系,原是和我们不对的,邹鲁(海滨)、覃振(理鸣)等当时携眷住在北京。十九年他们写信叫我去,我久住上海也觉无聊,就抱着玩玩的态度,乘船经青岛转大连乘车至天津、北京。
那时南京在中央政府之下,是不便经过的。至大连下船时,很少看见日本警察,但立即有便衣人员约我们到一个地方谈谈。我化名为张致远,是教员,在上海某校教书,正在假期旅行。那个地方好像是秘密警察办公处,里面的人拿出一本照相簿,其中我看见一张我年轻时的,但他们没有对出来,照相簿前有柏文蔚、赵恒惕的签名,秘密警察告诉我,这是他们经过本地时的签名留念,他们最先也不愿暴露身份,但终于给发现出来,而且愿意签名留念,希望你也坦白告诉我们,签个名在簿子上。
我说字写得不好,他们也就算了,但说总会查出来的。又劝我乘火车去天津,因为火车时时有,不像船有定期,要等数天。我于是乘车前往,一下车,天津报上已刊出张知本抵达的消息。推测一定是日本警察机构提供的消息,深深感到他们特务部署的周密。
抵津不久,即赴北京参加扩大会议,凡是出席的,都为会议的委员。该会议曾发出通电,主张反专制与反共党并重,部署妥当后,才请汪精卫北来。因为汪自知以前亲共的不对,所以我坚持须同时以反共为号召,如此则于汪本人,于会议全体均属有利。
扩大会议又曾通过一项约法草案,计八章二百十一条,而以中山先生之建国大纲列诸首章,此项草案在北京时已拟妥,后退至太原时始公布,故世称之为“太原约法”。该约法由前国会议员、民党老同志吕复主稿(其弟吕咸,今在台,供职“中央银行”,前台北市女议员吕润璧即吕咸之女),复经余及邹海滨、汪精卫、郭春涛、经亨颐、陈树人等六人几次斟酌而成。
该约法对于人民之自由权利义务,均详为规定与保障,不受其他法律之侵害与限制,以视前此之各项宪法草案,是较为进步的。
汪精卫聪明有余,但稳重不足。有一次在保和殿开会,汪担任主席,南京飞机投弹,汪竟抓了皮包就跑。其实他只需宣布“现在停止开会”就好了,但他慌张得什么都顾不得,我想起来还觉得好笑。清末炸摄政王之举,有人说完全因为汪临事神色紧张,启人怀疑才告岔事的。
证之以保和殿我亲见的情形,不免相信这传说是可信的。戴季陶氏曾经批评胡汉民欠一个“厚”字,汪精卫欠一个“重”字,也就是说胡太刻薄,汪太轻浮,我觉得这批评非常深刻。中山先生在世,有时叫汪撰文,有时叫汪演讲,但从未任之以实职,是中山先生对人能用其所长的地方。
扩大会议的失败,与张学良军队的入关大有关系,扩大会议派去的人是薛笃弼(子良)。阎锡山悭吝,连路费都未给他;但对方派了吴铁城、张岳军、宋子文等,带了大批金钱陪张学良嫖赌吃喝,终于使张投向南京。张的军队一入关,南京得此生力军,才获胜利。但东北边防因此空虚,日本即于此年“九一八”乘机爆发沈阳事变,所以张军入关,对当时政府有大助,对后来国事则有害。
阎锡山的小气,还见之于一件事上。当时在山东、河南一带,有红枪会的组织,向阎要数万块钱,阎不给,蒋给了几十万,结果这些地方武力都给南京方面收买了过去。
扩大会议在军事上是失败了,但它在政治上的主张,却引出了南京召集国民会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否则是不会有的。这会议也引起胡、蒋意见相左,终之胡被禁汤山之一幕。胡被拘后,汪精卫竟在香港《南华日报》撰写《哼,也有今天》一文,加以讥刺,我觉得此种幸灾乐祸的态度,未免胸襟过窄,有失政治家之气度。
中原大战既失败,阎冯下野,扩大会议委员纷纷离开平津及山西,我也回到上海,续度亡命生涯。后来因胡氏被扣,开非常会议于广东,以及宁粤议和于上海,我都参加。当广州、南京、上海三方面均于二十年十一月间,分别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就在广州方面参加。
当宁、粤双方在上海举行和议后,政府不久便于二十年底改组,由孙科任行政院长,陈友仁任外交部长。其实那时汪已暗中与蒋谈妥合作条件,由汪出任行政院长。
某次开会,汪因已与蒋方妥协,附和其主张,故手持报纸,一会看到蔡廷锴、蒋光鼐抗日的消息,说:新闻自由怎能自由到此种地步,公开刊登军事秘密,应该取缔;一会又看到外交部长陈友仁的抗日言论,他说也要取缔。我心里暗想这是行政院长的交换条件,就中途退会。
果然到了二十一年一月,政府又改组,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罗文干任外交部长,孙科和陈友仁任职不到一个月便下台了。
后来中央发表我为民众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我受任之始,发表谈话,指出近年之民众训练,不是采煽动的方式,就是采麻醉的方法,都是愚民政治。后来我受命取消抗日救国团体几十个,我不能赞成,就辞职又回上海。是年四月,政府召集国难会议于洛阳,我虽被邀,但未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