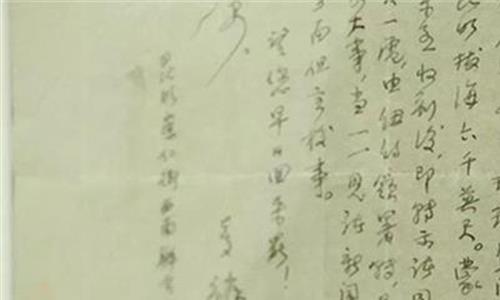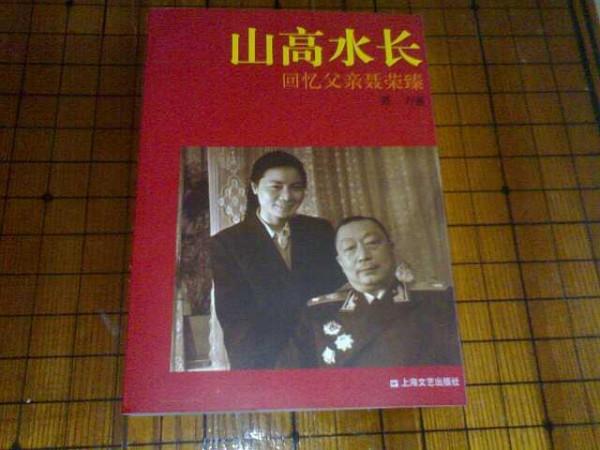张申府学术论文集 张申府之女回忆父亲:半生辉煌 半生黯淡
1906年的正月十四,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十四岁的父亲跟着他当时在京师大学堂读书的七叔,坐着一辆骡子拉的轿车,从献县来到北京求学。父亲在他自己的回忆中说,那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件大事。
到了北京之后,父亲先在识一学堂上了小学,半年之后升到东城的崇实学堂读高小。刚到北京的时候,父亲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学校里就有些纨绔子弟讥笑他为乡下佬。当时父亲只是一心读书,对于那些整日吃喝玩乐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根本不加理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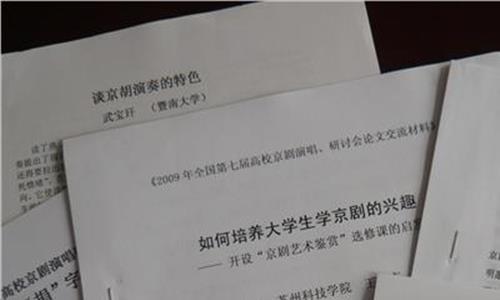
1908年,父亲考入公立的顺天高等学堂,那是当时北京很有名气的一个学校。当时的同学有梁漱溟、汤用彤等人,不过梁先生他们相对年长,年级也高,父亲在那时跟他们跟他们交往并不多。父亲考入顺天高等学堂时的成绩是全班第一,按照当时惯例,老师安排他做了班长。不过父亲当时只有十六岁,在班上是最小的学生,老师怕他管不了别人,就特地找了一个年纪稍长得学生协助父亲。

到了辛亥革命之后的1913年秋天,父亲跳班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父亲在那篇《回想北大当年》中描写当时的生活,对于北大的藏书楼(北大图书馆的前身)情有独钟,他回忆说当年藏书楼的书除了工程书之外,几乎没有他不看的。而他发现罗素并介绍罗素,“也可以说是与北大藏书楼的帮助分不开的”。

北大毕业之后,父亲留校做助教,由于平时课程并不多,就在图书馆帮助李大钊做一些图书馆的工作。父亲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投身于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可以说这段经历关系很大。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打印卡片等工作,父亲则负责检查和校对。毛泽东在北大听课时,就曾经在图书馆担任过登录图书的工作,有时候登记错了,父亲就会让他去重新登录。
五四运动前后,父亲和李大钊和陈独秀已经是非常熟悉而又志趣相投的朋友。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父亲和李大钊经常投稿,是热心的作者和读者。1918年底他们又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经常在一起谈论工作。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
定了思想基础。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魏金斯基到了北京之后,见到了父亲和李大钊,就中国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后来李大钊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
那一年8月,父亲收到陈独秀的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就是讲建党的事情。信中说:建党的事情在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以谈。当时陈独秀还在信中就党的名称跟父亲和李大钊商量,到底是叫共产党还是社会党。父亲说他们当时还是比较幼稚,虽然认为叫共产党比较好,但是自己却不敢决定,最后还是魏金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
名称定下来之后,大家就开始分头去筹组。上海方面由陈独秀负责。陈独秀为人热情,说干就干,很快就发展了周佛海、田汉、李达、施存统、沈雁冰、沈玄庐等人。等到父亲9月份到上海迎接罗素来中国讲学的时候,陈独秀在上海已经把共产主义小组发展起来了。
在陈独秀在上海活动的同时,北京也开始进行筹组活动,不过李大钊性情温和、为人稳健,工作起来又比较细致谨慎,所以虽然他和陈独秀一样具有热情和信心,但是相对来说北京的发展还是稍微缓慢了一些。
父亲从上海回到北京之后,跟李大钊讲到上海的情况,,并进一步商量发展党员的事情。后来李大钊找到了张国焘。张是北大的学生,当时表现积极,热情很高。除了李大钊和父亲,他是北京的第三个党员。
后来北京方面又发展了高语罕、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等人,不过这都是父亲到法国之后的事情了。
1920年,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里昂大学筹办了一所中国学院,邀请父亲去教授逻辑。父亲离国赴法之前,李大钊和陈独秀分别跟父亲谈过党组织的发展问题,他们希望父亲到法国之后能够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父亲在法国的生活安顿下来之后,并开始着手进行这项工作。
在法国,父亲见到了早他一个月来到法国的周恩来。周恩来告诉父亲:他曾经想到英国去学习,但是英国生活水平太高,所以才到法国来。当时周恩来住在巴黎南郊的哥伦布,从那里坐火车到巴黎大约用一个小时。在那之前,父亲曾经和周恩来有过交往,也曾经听李大钊谈起过他,觉得他思维慎密,对中国的现状和前景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于是父亲就发展了周恩来入党。
后来赵世炎、陈公培陆续到了法国,他们一起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父亲收到国内寄去的通知,并在党小组内进行了讨论,但是因为时间紧、路途又远,没能回国出席。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
父亲最早对罗素发生兴趣就是在前面说过的北大藏书楼。有一天,父亲在北大藏书楼发现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这就是罗素所著的《我们的外界知识》,1914年在美国出版。父亲翻看了一遍,觉得很有新意,又接连看了两编,从此就对罗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开始广泛搜集罗素的文章和著作,并推荐给他的同学。
1919年至1920年间,父亲先后翻译了罗素的《我们所能做的》、《哲学之价值》、《梦与事实》《民主与革命》等文章,并且还撰写了若干介绍罗素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1920年10月,罗素应梁启超所办的“学术讲演会”与北京大学邀请来中国讲学。父亲得知后9月中旬就从北京赶到上海迎接罗素。
罗素在中国的第一次讲演在上海大东旅社举行,由赵元任先生担任翻译。他的演说平易畅达,语皆中的。父亲说罗素的讲话“很像玉泉山水的爽人宜人,清冽干脆”。结束了在上海的讲演,罗素由傅铜、赵元任等人陪同转往长沙,父亲便回到了北京。后来罗素又从长沙到了北京,父亲曾经多次到罗素的住处看望。
父亲向罗素讲北京大学,讲蔡元培校长以及蔡校长实行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讲五四运动之后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深入人心。罗素都很感兴趣,他认为当时遗传的旧教育日渐衰败,新教育必起而代之,他希望中国能够创造一种新文化,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
在与罗素交谈的过程中,父亲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学生,向罗素请教哲学问题,这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当时,父亲已经办好了去法国的手续,所以当梁启超先生见到父亲的时候,梁先生叹息道:“罗素来了,你却要走了。”
父亲前半生参加的活动太多,始终没有办法埋首书斋,五四运动也好,抗日救亡也好,他都是积极投身其中。后来在父亲的晚年,美国的历史学家舒衡哲多次访问父亲并撰写了一本口述史《张申府访谈录》,舒衡哲当时就问父亲:作为一个学者,为什么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之中呢?父亲当时就说:知识分子就应该以天下为己任,承担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种良知使他自己的学术生涯出现了缺憾,父亲在晚年检讨自己的学术生涯,说自己“用心过分,浅尝则止”。有一次我和周谷城先生的孙女聊天,她说,如果父亲能够研究学问,那么在学术上的建树恐怕会超过我的叔叔张岱年。叔叔在学术上确实受了父亲很大的影响。我在给父亲整理文集时也看了叔叔早年的一些文章。叔叔早年对罗素以及马克思哲学产生兴趣,引路人应该说就是父亲。所有后来有学者说父亲没有完成的著作由我叔叔完成了。
现在叔叔九十五岁了,居住在北京大学。身子很硬朗,只是耳朵有点聋了,东西也很少写,只是还是时常看书看报。经常有学生去看望他或者请教,他还是保留着他们那个时代的学者的忠厚,总是来者不拒。人家走的时候还总是送出家门。
他总是对我说:“不行啦,一年不如一年啦。”我时常过去看他,前一段时间我的婶子(冯友兰先生的表妹)摔了一跤,把身体摔坏了。我就劝叔叔说尽量减少一些学生的来访,最近还没有去,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经常留来访的人在家吃饭。
1979年11月中旬的一个下午,那天天很冷,父亲在20年里第一次被允许接受一位西方历史学家的采访,这位西方历史学家的中国名字叫舒衡哲。后来舒衡哲在她的文章中写道:“越听张申府讲故事,越核对他与同时代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是所有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最为世界影响的)的文献和以及回忆”,“就越觉得这位杰出的哲学家竟然在现代史上被忽略了这一点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在第一次采访之后,舒哲衡表达了希望以后能够到家里继续跟父亲进行谈话的愿望。当时外国人还不准自由到中国人的家里访问。可是父亲立刻回答:“我希望可以,非常希望,我们必须坦诚地谈,因为对我来说,讲真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在先后近60个小时的访谈中,父亲与其说是在接受舒衡哲的采访,倒不如说他在给自己寻找一面镜子,他要在这面镜子里寻找自己被忽略了的过去的真正面目。父亲仿佛在他和舒衡哲的谈话中找到了这面镜子。虽然在父亲的晚年,曾经有不少中国学者采访他,但是父亲在跟他们对谈的时候,仍然有一些不能探索的、有关他的经历和内心世界的死角。
在1980年4月28日的谈话中,他们谈到了父亲当年的退出和被民盟开除。那是在1925年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的时候,陈独秀认为当时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薄弱,所以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但是父亲不同意陈独秀的观点,他把自己的看法说出,结果却遭到了众人的冷笑,认为父亲看法幼稚。
当时他们那种轻蔑的态度让父亲感到极端难堪。愤而退出。父亲走出激烈的辩论会场,从旅欧时就跟父亲成为好朋友的周恩来跟他走出会场,表示支持父亲的观点,并劝说父亲不要退出。
“但是,我还是退了出来。我就是那种宁折不弯的人。”说着,父亲大笑起来。他越说兴致就越高,因为他觉得宁折不弯这四个字可以对他的性格做一个概括。他把这四个字给舒衡哲这个外国力史学家写在纸上,接着又笑,又说:“是的,我总是那个样子,在1925年,1948年和1957年都是这样。……”
1948年9月,父亲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呼吁和平》,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杂志《观察》上面。因为这篇文章,父亲受到了党的严厉批判,政治地位从那以后完全扫地。新中国建立之后,父亲曾经一度没有工作。
后来章士钊对主席说,申府也算我们党的老人了,他的工作应该安排一下。主席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怎么敢安排他呢。后来父亲的工作还是由周总理给安排到北京图书馆。在图书馆,父亲只是埋首自己的研究工作,政治上的活动没有了,文章也很少发表。
我小时候,父亲每天除了伏案读书,有时也教我识字,和我一起游戏。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专门向我讲授过大道理,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教导我怎么做人。我七岁生日的时候,父亲送给我一个日记本,他在扉页上写道:有为而有所不为。父亲讲给我听,我也似懂非懂。
在他的晚年我跟他一起生活,父亲在我的眼中,似乎除了书之外没有别的爱好。74年的时候,母亲得了半身不遂,父亲只是埋首书斋,家里的事情基本都是我来料理,每个月我都要算计这个月的开支,把水电费,买煤、买粮食的钱都算出来,但是就是搁不住父亲买书。
有时候日子过得真的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是父亲都能淡然处之。当时家里订了有五六份报纸,有时候实在不能维持,就拿一些旧书报来卖钱。每到这个时候,他总是阴沉着脸。那几天我总是不敢跟他说话,因为只要跟他讲话就翻脸。而每次买废纸的师傅拿走报纸之后,他也总能想起一些舍不得卖的,就追过去再把报纸买回来。一个师傅曾经对我说:“你们家老头儿,有意思!”
1976年,我参加工作,第一年的工资是16块钱,第二年是每月18块钱,第三年是21块钱。出徒之后是33块,随后才是38块6毛。三十多块还能勉强维持生活,没出徒的时候日子的艰苦可想而知。当时跟我一起参加工作的同事都有表带,就我没有。我就跟父亲说我也想要表。父亲拿不出钱,又不愿意让我失望,就把自己的表给了我。
父亲常说,“尽其在我,听其自然”。冬天的时候家里五个屋子都用炭火取暖。当时家里的保姆是南方人,不懂生火,我每天上班也不能随便请假。家里的火经常是这个正着着那个就要灭了,父亲就自己把这个炉子中的碳倒到那个炉子里,又从那个炉子倒到这个炉子。
他把这种琐碎的家务作为一种调剂,一种锻炼,善于在生活中寻找乐趣。人生真是意味深长,父亲早年可以说轰轰烈烈,晚年却默默无闻,现在跟人们说到张申府,大概没有几个人会记得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