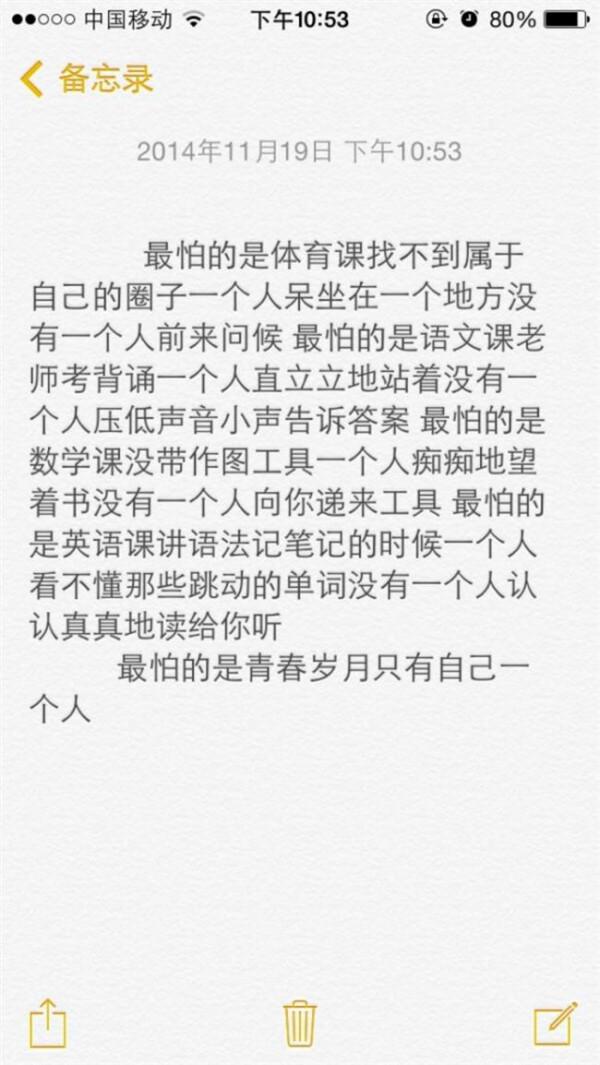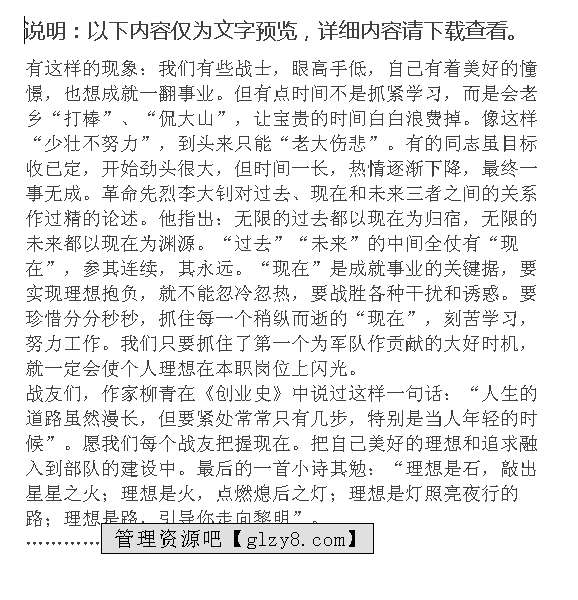亲爱的同学 《亲爱的》影评:我曾失去你 想到就心酸
《亲爱的》是2014年出品的一部由陈可辛执导的“打拐题材”电影。电影主要讲述以田文军(黄渤饰)为首的一群失去孩子的父母去寻孩子,以及养育被拐孩子的农村妇女李红琴(赵薇饰)如何为夺取孩子做抗争的故事。田文军与鲁晓娟(郝蕾饰)是在深圳生活的一对离婚夫妇,而他们之间的唯一纽带--儿子田鹏却意外被人贩子拐走。至此,夫妇俩踏上了寻子的艰难旅途,并在途中认识了一大批与他们同样无助的父母。

终于,田文军夫妇在一个偏僻的村落中寻到了田鹏,但男孩口中的“妈妈”却并非鲁晓娟,而是一位名叫李红琴的村妇。原来,李红琴在自己已过世丈夫的欺瞒下养育了两个被拐来的孩子,另一个悲剧就此展开。李红琴被剥夺了两个孩子的抚养权。为了继续养育自己的女儿,李红琴只身前往深圳,在落魄律师高夏(佟大为饰)帮助下与收养女儿的福利院打官司,但最终无果而终。

【影评】
《亲爱的》以打拐这一社会敏感话题作为舆论点,但是其承载的内容是远比打拐更为丰富的当代转型中国的社会切面、人物境遇。影片用有限的时长勾勒众生相,用深圳这个极具代表性的移民城市,集中展现各种阶层、各类背景的人物的苦难与挣扎。

而在这一个个故事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悖谬频出的人事经历和无因无果的人生苦难,但我们同样也能看到这黑暗背后来自人性和人情的一丝光亮。本文尝试通过对电影情节、人物设计和镜头语言的精析,来看一看《亲爱的》是如何深刻地呈现和回答人生真相这个无解命题的。
本片中的众生相描绘非常成功。影片中的主线人物有从陕西移民深圳的失意者田文军、处在中年困顿期的城市中产鲁晓娟、无法生育的农村低贱妇女李红琴、游走于法律灰色地带的城市上班族高夏,也有负疚负痛的暴发户韩德忠。
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人物各有各的伤痛和面对苦难时的不同选择。除了这些主人公以外,影片还通过大量的情节,甚至情节外镜头展现诸如执法者、农民工、小摊贩等一众人的形象,众多的方言也是影片的一大特色。尽管有这么多的人物,我们却可以发现没有一个人物曾真正占据过视点镜头。
田文军、李红琴这两个影片无疑的主人公实际也一直处在被看的位置,他们都不是看的意义上的主角。这样的设计暗示了在电影中,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权威者或说占据主动地位的人。
这部影片之中也没有真正的施恶者。对于这一点,影片有非常明显而精到的暗示。《亲爱的》的结构设计有一大亮点:影片的前一个小时讲田文军失去儿子又找到儿子的故事,后一半却引入一个全新的主角,讲李红琴失去儿女又争取儿女的故事。
这样一个前后有着明显断裂的情节,又因田文军和李红琴的对立立场而显得愈发荒诞。一个是失去孩子的父亲,一个是人贩子的妻子,两人的正恶立场似乎非常容易界定。然而,李红琴并未被展现成一个恶人,相反,她不仅是一个对自己丈夫的罪行毫不知情的无法生育、地位低贱的农村妇女,更是一个深爱子女,孤独无依的母亲。
对于李红琴苦难的大笔副呈现,迫使观众不得不放弃自己非黑即白的立 场,并对李红琴报以最大的同情和敬意。
影片之中有一个设计很巧妙:田文军和鲁晓娟在发现鹏鹏之后并未按照警方的意思等待,而是抱着孩子一路狂奔。在李红琴和乡民的眼里,他们反而成了拐孩子的人。这就让影片的悖谬有了一定的合理性。善恶、正误的判断很多时候都是相对的,换一个立场也许判断就会完全相反,实际上影片中真正的恶人--人贩子从未被真正地展现。
片中可以指认的恶,诸如韩德忠吃猴子、李红琴养拐来的孩子,甚至是唐青山不愿意帮助李红琴,换一个角度看都是可以被理解的,这些恶都不是纯粹的罪恶。
但是,人物身上的悲却是绝对的。电影刻画几个主人公时的镜头语言有着鲜明的特色:中近景镜头中,人物的部分肢体、面颊经常被物体遮挡或不正常切割,非常规构图很常见(最典型的是鲁晓娟咨询心理医生时她的头始终被框在画面左侧,右侧则是白墙)。
另外,影片很少使用大全景,全景,而大量的中近景镜头又多是通过玻璃、电线、铁栏等拍摄,或是使用镜像、画框中的画框。这就使得人物自始至终都仿佛处在被囚禁、被压抑的状态。正如他们从头到尾都未曾摆脱自己所处的狭小空间和画面牢笼,人物的悲剧也未曾停息。
另外,影片中还多次运用了有声空镜或声画不匹配(例如,李红琴和高夏在深圳街头的影子和他们的对话;田文军与骗子打电话的声音和孩子们玩气球的画面),人物面对苦难时的无力感由此变得鲜明。这让人不禁要问:如果没有真正意义上占据主动地位的人,没有绝对的施恶者,那么这些主人公的悲剧到底从何而来?
是法律吗?的确,影片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展现执法者、政策代言者面对主人公苦难时的冷漠、没有人情味。田文军丢失孩子的焦灼与公安局24小时才能立案的一口回绝;李红琴的多次来访与福利院长的多次无情拒绝;甚至是社会地位很高的富商韩德忠在面对办证人员的,令人难以接受的要求时也无能为力。制度和法律仿佛一团悬在人头上的阴云,他们无法驱赶,更无力反抗。
然而,法律真的就是囚住这群人的围栏吗?从镜头语言和情节设计上看,影片创作者显然不这么认为。正如前文所说,这些法律、政策、国家的代言者也从来没有占据过视点镜头。更为明显的是,影片设计了城管放过摆摊的田文军、判案法官满脸疲惫等细节,以此否定了执法者的没有“人味”。
借高夏的一句 “现在的人就是缺乏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的意识”,影片不经意间就传达出了它对法治的态度:或许对于主人公来说这些法律制度是不合理,但是换个立场这些法律对社会上大多数人来说又有其合理性。因此,影片中的法律并非主人公苦难的源头。
那么是阶层吗?作为一部展现转型社会切面的电影,对于阶层的呈现显然是必不可少的。片中的主人公在深圳的经济、社会地位大相径庭。例如韩德忠这个富商在最初出现时常常处于仰拍镜头中。他在“万里寻子会”这个群体中的权威性不言自明,而这种权威不仅仅来自于他作为创办者的身份,更来自于他的阶层位置。
另外,影片还有很多精到的小细节:幼儿园孩子们脚上旱冰鞋的特写、田文军一家关于说陕西话还是普通话的两次讨论、还有田文军对鲁晓娟的那句“咱俩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我认命,你不认命。”这些极为微小隐晦的情节都展现着社会分层的深刻性。而李红琴走在深圳街头的格格不入的打扮,居住的肮脏破旧的招待所则是这一现象更为外露的表现。
然而,影片却给予了这样一个明显的阶层分层一个想象性的和解。我们看到的是韩德忠联合起了各类失独者一起寻子;高夏选择了无偿帮助身无依托的贫妇李红琴;鲁晓娟也放弃了与自己地位更为相近的丈夫的婚姻。就算在片子的最后,韩德忠放弃了继续寻找,放弃了“万里寻子会”,但他至少是得到了田文军真心的理解和体谅的。
而且当他躲在狭小的专卖柜后失声痛哭时,社会地位优势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他同样是被困在生活中无法逃脱的苦难者。
我们姑且不去判断这样的和解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可能,但这至少说明电影并未将阶层分化设置为主人公苦难的源头,又或者,影片根本不在乎谁是苦难的施予者,其真正关注的是人物在面对人生共同苦难时的共性和差异。
没有恶者,没有苦因,这就是这部影片的荒诞和压抑所在。人物在其中寻不到苦难的解脱,因为他们连苦难从何而来也未曾知道。其实人生就是如此荒诞的存在。抛开戏剧化的展现,这部影片实际就是对每个人真实境遇的展现。正如张冀在采访中所说:“从命运而言,人的抗争最后都是无意义的,只能带来荒谬感。”这也是为什么影片要在最后设置李红琴怀孕这样一个荒诞至极的情节。
但是,人生的苦难和荒谬绝不是影片的全部内容。因为我们还能看到主人公从头至尾未曾停止的挣扎与抗争,或是坚忍的接受与承担,我们更能看到人物之间的和解和愈发紧密的连结。影片最让人动容的和解发生在田文军和李红琴之间。
片中有一个前后呼应的情节:田文军在寻子录像中说自己的孩子吃桃过敏,而故事最后则是李红琴反将这个事实告诉他。虽然在拐孩子这件事上两人的立场是绝对对立的,但在对孩子的感情上,两人都同样是爱之深切的父母。与此相似,影片中几乎所有人物的和解与互助都是建立在人性、人情、体谅、感同身受的基础之上的。而正是这喷涌的人情让这群受难者得以突围,获得短暂却弥足珍贵的快乐。
人情的突围在影片的镜头语言上也有明晰的展现。片中存在有大量的人物脸部特写镜头。尤其是在人物陷入苦难或是他的脆弱和痛楚开始显露之时:韩德忠的特写第一次出现在他带泪讲自己吃猴子的故事时,而这一情节正是在暗示他因自己的罪恶而产生的负疚之情。
而高夏的第一次特写则出现在他给保姆打电话时,那时他脸上无法掩盖的焦虑正为之后一个老年痴呆的母亲和入狱的姐姐埋下了伏笔。在这一个个特写镜头中人物被画框紧紧框住,没有丝毫挣脱的出口。但是也只有在如此逼近人物面孔的镜头中,他们表情的细微变化和丰富的情感表达才能够强烈到冲出画面,直抵人们的心灵。
影片的最后,田文军、鲁晓娟、吉芳和李红琴依然被牢牢地囚固在画框中的画框之中,但是他们的情感已经无法被框住,已经刺入每个观影者的心灵。我们看到了喷涌的情感和张力,看到了小人物对人生各种禁锢最势单力薄却又最直击人心的抗争。我想,这便是电影给予这些苦难者最大的敬意与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