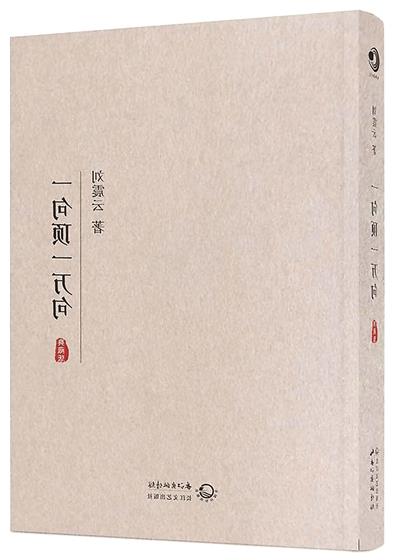刘雨霖年龄 刘雨霖:诠释中国式孤独
刘雨霖:作家刘震云之女,电影导演、编剧,攻读于纽约大学导演系。2014年,凭借微电影《门神》入围50多个国际电影节,并获得了包括第41届美国奥斯卡(学生单元)最佳叙事片在内的8个国际奖项。2016年11月,执导的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上映。

11月4日,由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作品《一句顶一万句》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大陆上映,导演系作者刘震云的女儿刘雨霖。
这是刘雨霖的电影长片“处女作”,影片推出后,迅速入围韩国釜山电影节和埃及开罗电影节,并获得台湾金马奖提名。这并非她第一次受到国际关注。

早在2014年,年仅27岁的刘雨霖,就凭借微电影《门神》入围法国戛纳、日本东京等50多个国际电影节,并获得了包括第41届美国奥斯卡(学生单元)最佳叙事片在内的8个国际奖项,成为继李安之后第二位问鼎奥斯卡奖的中国导演。

名门之后,又头顶“奥斯卡奖得主”的光环,刘雨霖的导演之路似乎比一般人顺畅得多。出入各种电影节、接受媒体采访,她都落落大方、从容不迫,有超出实际年龄的成熟稳重。
自信缘于视野的开阔,她从小就跟着父亲刘震云到各地采风,也跟着做公益律师的母亲出入老少边穷地区,既见识到底层生活的艰难,也结识了名人大腕。母亲郭建梅获得“国际妇女勇气奖”,她也陪着去美国白宫领奖。
在刘雨霖的世界里,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她觉得幸福的瞬间,可能是和父亲蹲在纽约路边,一人啃一个土耳其烤肉卷儿,看来来往往的人。这也是她做电影的价值观,她不想为王侯将相立传,而要去发掘普通人内心被忽略的情感,这些情感纠葛在她的眼中不亚于一次世界战争。
走出父辈的荫翳
网络上的“刘雨霖”词条,对她的第一句定位是“作家刘震云之女”,在外界看来,这几乎是她身上最大的标签。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生活在父辈的荫翳之下,到了特定年纪,会有所谓的“影响的焦点”。对这个笼罩头顶的“光环”,刘雨霖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向《凤凰周刊》谈道,“这是我一辈子感恩和荣耀的地方,我不想摆脱它。作为他们的女儿,我从小能有一个自由的生长环境,明白很多人世间的道理,找准了方向做自己喜欢的事。”
她从小就是“孩子王”,在农民日报社的家属院里,组织健康小队、文艺小队,像个假小子。一群孩子呼啦啦地跟着她,一溜烟儿地到处疯跑。这和家庭的“放养”政策有关,在刘震云看来,家庭就不应该有教育,“车轮转不转,要看它自己。”
一到晚上,别人家总在阳台上喊:“xxx,回家吃饭了!”“xxx,回家写作业!” 而刘雨霖是那个快乐的“漏网之鱼”,玩到多晚都没人管。
回忆起“上蹿下跳”的小时候,即便是不那么美好的经历,刘雨霖也充满愉悦:“从小被狗咬过三四次,被猫抓过,还被兔子咬过。后来去卫生防疫站,医生都认识我了,打最后一针的时候,医生说‘你别打了,你已经打了太多针终身免疫了,你现在可以随便被猫抓、被狗咬了’。”
由于没人强制约束,她长这么大似乎没有过“叛逆期”。但是,自由并不代表放任,父母对她更多的是做人、做事“大道理”的引导,做人“要向身边的人请教、学习,多观察,要‘不要脸’,一日三省吾身,要大气”;做事“要用心,不马虎;把事情一次性做对,不反复;要注重细节。”
这种对事执拗的完美主义精神,体现在刘雨霖身上,就是一件事只要决定了,就算赴汤蹈火也要尽善尽美。
《一句顶一万句》剧照。
大二那年,原本在中国传媒大学学习播音主持的刘雨霖兴趣转向了电影,她没有和家人沟通,学校的课业疏漏了,不好好上课也不练声,成天抱着电影的书看。学校老师打电话给刘震云,刘震云怒不可遏,极少地动手打了刘雨霖。
以刘雨霖的形象气质和能力,再加上父母的声望,从播音主持系毕业后,去央视做一名主持人,是非常保险的路子,但她兴趣转变之快之坚定,让父母措手不及。几番商讨后,一直保持着民主、自由作风的家庭,选择了尊重孩子的意见。“你喜欢做什么就去做,不论想做厨子还是导演,但是既然做了就要用心。”
为了走上职业化导演的道路,她想去美国继续深造,最终得以进入梦寐以求的纽约大学电影学院。
研二那年,她作为场记参加了冯小刚导演的历史巨制《一九四二》,她对记者说起冯导:“他一直在坚持自己,走别人不走的路,努力开拓新的方向。成千上万人的大场面,他都能特别冷静地既顾全到大局,又照看到细节。”
作为唯一获得奥斯卡奖的大陆导演,她也认识了同样毕业于纽约大学电影学院的“师兄”李安,说起这位前辈导演,她学来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做事情不能揠苗助长,他出作品的速度其实不快,三四年磨一部,他是在潜心做自己的事。即使在很劳累的状态下,也能带着团队坚持往前走。”
《门神》获奖后,刘雨霖有机会出席活动,发表演讲。面对两三千人的场合,刘雨霖无需讲稿,气场十足。
“这是我根本没想到的。”郭建梅说,她发现之前对女儿的很多担心是多余的。那一刻,“妞子长大了。”
“六亲不认”的导演
由于刘震云既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原著作者,又是电影编剧,电影的剧情和拍摄手法,都是父女俩商量着定的。
但一旦有了分歧,两个“牛脾气”犟到一块儿,刘雨霖也会叫板刘震云:“你是导演,还是我是导演?编剧的时候听你的,拍摄的时候就应该听我的!”但是平常情况下,郭建梅透露,“妞妞”对父亲还是多少有些畏惧的。
刘雨霖专注做起事来,有一副“六亲不认”的架势,不能不说是受到刘震云的影响。刘震云经常对做官的弟弟声色俱厉地教导,“无论你官做得多大,你必须……否则我就不认你!”对于有亲人想托他的关系晋升,他也是“凶巴巴”地撇下一句话,“没能力就别干!”
刘雨霖与《一句顶一万句》的意大利文译者帕特里西亚·里贝拉蒂(Patrizia Liberati)在拍摄现场。
《一句顶一万句》在河南老家拍摄,有不少亲人,奶奶、姑姑、舅舅等好几次都想去片场看看,还找郭建梅来说软话,都被刘雨霖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你们谁都不能来”。气得奶奶放狠话,“和她爸一样,这个龟孙!”
为了不受干扰,就连郭建梅想去探班也屡屡被阻止。终于有一天,刘雨霖打电话:“妈,你来吧。”那是牛爱香和宋解放结婚,要拍婚宴大场面,缺群众演员。
饰演庞丽娜的女主演李倩这样评价刘雨霖:“她的头脑令人惊讶的清晰,你问她什么问题她都能解答。她能hold住全场的原因是之前做足了功课,什么问题都深思熟虑过。”
其中有一场戏,庞丽娜骗丈夫要去苏州旅游,其实是和出轨对象蒋九最后一次约会,完了就分手回归家庭。欺骗的过程中,李倩总觉得需要表现出一点愧疚。刘雨霖的意见是,不要太刻意,感情要往回收,因为庞丽娜出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样撒谎的时候肯定也多,而且她这次出去是要和蒋九断掉的,她认为她可以回得来,你知道她的结局回不来,但是她自己是不知道的。“她的分析说服了我,所以我遵从了导演的意见。”李倩说。
男主演毛孩对《凤凰周刊》说,“跟着刘雨霖拍戏太幸福了。因为几乎没有出现一个废弃的镜头,有的导演可能没有想好,一个场面会多拍几个镜头备选,回去可以剪辑,但是,刘雨霖脑海里很清醒,她要什么样的镜头已经考虑得很周全了,工作效率极高。”
有一场戏,演员刘蓓和毛孩“姐弟俩”说一些心里话,那场戏一共拍了8条,刘蓓因为入戏太深,哭得太厉害,在演的时候完全没法坚持把台词说下去,毛孩也跟着哭。刘雨霖在监视器后面也“噼里啪啦”地掉眼泪,但是她清晰地知道,这是积压在心里十几年的疤痕,当一个人面对这种痛苦的时候,并不会泪如泉涌,而是一种藏在心底的伤痛和挣扎。
毛孩不无赞叹地说起刘雨霖对细节的苛求,细致到一根筷子怎么摆放她都要斟酌,墙上的画没有挂正,她都要赶紧去摆正。“细节控”、“完美控”,是因为她谨记着一个家训:用心做事。所有人都觉得这像她父亲,但是刘雨霖知道这是她自己。
尊重生活的逻辑
凤凰周刊:刘震云先生的小说作品众多,你为何会选择改编《一句顶一万句》?
刘雨霖:《一句顶一万句》是刘老师(刘震云)的小说中我最喜欢的一部,也是读的遍数最多的一部。2007年前后,在他的创作阶段,我跟着他去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采风,当一个小助手做记录,观察当地人的生活。所以,书中的人物故事和细节我都很熟悉,在情感上也很亲切。
2014年初,我开始想把它拍成电影,这个想法酝酿了半年,才给刘老师打了越洋电话,跟他争取小说的改编权。他不是一个主动要发展电影的人,都是电影人准备好了来告诉他,向他邀约。我知道他肯定会问三个问题:为什么要改编《一句顶一万句》?它那么大的文学体量,你准备怎么改?作为导演,你不同的地方是什么?这三个问题我都思考得很细致,所以他爽快地同意了,正式拍摄是去年10到12月。
凤凰周刊:小说和电影是两个不同的艺术门类,他是专业的作家,你是科班的电影人,两人在编剧和拍摄的过程中遇到分歧,谁听谁的?
刘雨霖:分歧肯定会有,刘老师作为书的作者,最了解里面的人物和故事架构。他改编剧本,一个月就出来了,非常成熟。但一些细节和台词,我们会有讨论,两人观点不一致的时候,不是说以他或者我的意志来决定,而是以人物生活的逻辑来决定。
直到开拍前十天,我们还在讨论细节。比如,里面有一场戏,姑父安慰百惠说:“百惠,你是不是想去动物园看长颈鹿?”而原剧本里说的是带她去看大老虎,这个细节的改变是因为有一次我去买早餐,听到卖早餐的人说,下了班要带女儿去动物园看长颈鹿。这些细节来自于生活,又融入到影片中。
我希望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看不到导演的痕迹,那我怎样才能隐藏自己呢?首先得有一颗敏感而柔软的心,来吸纳生活中被我们忽略的细节和情感。其实,这种商量并不只是发生在我和刘老师之间,和摄影指导或者灯光指导、造型师、道具师、演员的合作,都会有。
无以言说的孤独
凤凰周刊:《一句顶一万句》要表现的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孤独,为了逃离孤独,需要去寻找精神伴侣,寻找能说得上“一句顶一万句”的话的人,你怎么看待这个寻找的过程?
刘雨霖:孤独是艺术永恒的主题,无论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如何,都会有诉说的欲望,孤独感并不是找人吃顿饭就能解决的,它可能伴随人的一生。每个人都不会放弃这种寻找,它不局限于时空或者婚姻。能说得上“一句顶一万句”的话的人,不一定非要是结婚对象。生活中可能有不同的人能听懂你说的话,也有的人原本能说得上话,但后来又说不上了或者离开了。这是一个变动的状态,人的渴望也是变动的,这是这部电影的底色。
凤凰周刊:你之前说喜欢《小鞋子》《一次别离》这样的电影,也想要用影像来表达全世界人的共通的情感,但也有人说这部电影表达的是“中国式孤独”,你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刘雨霖:孤独感是世人都会有的,所不同的是,在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人们的孤独可以对神说,对真主安拉、基督耶稣、圣母玛利亚说,而神不会跟第二个人说,你说什么他都能完全接纳,说多长时间他都愿意听,他会说:“没事,孩子,我原谅你了。”中国人却少有这样的诉说出口,可能跟朋友说完以后,发现朋友是靠不住的;跟家人说,发现家人是聊不来的;跟伴侣说,发现时间长了都是各玩各的,这就是所谓“中国式孤独”。
凤凰周刊:说到信仰,在韩国釜山电影节上,《一句顶一万句》的海报是一个渺小的人跪在巨大的佛像面前,这有什么象征意义?
刘雨霖:电影中有一场戏,是男主角牛爱国和佛的对话,牛爱国发现妻子出轨,心情很复杂,就去找佛诉说。我估计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跟佛祖说“我要杀人”的人,因为他实在没人可以说话了,佛是一尊石像,石像不会给他反馈。
他第二次又跪在佛的面前,泪流满面,是因为他发现这个世界对他的欺压,他要反抗却没有办法。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叫《Someone to talk to 》,这场戏里的“someone”就是佛。当孤独到只能找佛祖的时候,生活是很悲凉的。
凤凰周刊:对你而言,要找到能说得上“一句顶一万句”的话的人难吗?
刘雨霖:很难,但是心态要摆正,身边能有这么几个人就够了。可能一些人在这方面和你能说得着,另一些人在另外的方面能说得着,不可能一辈子就只找那么一个人。而且,比这更重要的是,在特别焦躁、孤独和痛苦的状态下,要学会和自己对话。
人间的情感是共通的
凤凰周刊:我看电影时在想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很多人也感到电影的年代模糊,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这是有意为之吗?
刘雨霖:我在釜山电影节上接受记者的采访,他们也有同样的疑问。这部片子会有一种力量,让人忘记故事的年代和发生地,把时间、地点模糊化。这样的效果让我觉得很神奇,我本无意为之,却变得像是有意地创造了一种电影方式。
我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效果,主要是因为我不关注这些,其实一部片子光是让人记住了它在何时何地拍的,无任何意义。我并没有特别强化时间和地点,因为电影里面的情感和故事,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一样的。刘老师的原著是从民国写到当下,时间上并没有一定的标榜,如果说这事必须发生在什么时间,就把自己局限住了,也把人物故事局限住了。
凤凰周刊:《一句顶一万句》原著被译成20多种语言,受到广泛的国际关注。这部电影也被寄予厚望,参加了多个国际电影节,你会担心外界批评你用一种特别中国化的故事去讨好电影节吗?
刘雨霖:这恰是我最不担忧的,我不喜欢为了得奖而去用作品讨好人,贩卖人物的情感。这部片子并没有卖血卖肉,讲老少边穷。虽然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修鞋匠,但他的院子里有银杏树,秋天叶落满地很美,他在能满足的情况下,还是尽力给女儿买她想要的毛毛虫面包,家里布置得很温暖,一尘不染,这是我对里面人物的尊重,并不是中国人就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这讨好不了外国人。
一个真正成熟的电影人,之所以把电影拿到国际电影节上给外国人看,并不是为了拿奖,而是让更多人看到真实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情感状态。如果为了拿奖而讨好别人,这样的电影人和作品走不长久,因为他是在为别人活着,没有自己的路。
凤凰周刊:《门神》获得奥斯卡奖,对你后来的创作之路有何影响?
刘雨霖:《门神》我只花了8天时间在河南黄河边的小村庄拍的,拍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最后能走进50多个电影节,给我的母校纽约大学带来荣誉。
但它给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奖项,而是让我明白人间的情感是共通的,我带着这部片子到每一个电影节,发现大家的哭点和笑点都是一样的,他们忘掉了这是在黄河边一个小姑娘的事,可能会想起自己的童年、自己的女儿或者父辈。它让我更加肯定自己要走的路,就是通过电影去表现一些日常生活中惊心动魄和被我们忽略掉的情感。
凤凰周刊:你怎么看待目前中国的电影市场,它在经历转型吗?你认为当下观众的期待是怎样的?
刘雨霖:我觉得中国电影市场迎来了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并不是指票房上的火爆,实际上,2016年的整个电影票房相比去年是冷清的,没有动辄票房上10亿元的片子,这是因为观众冷静下来了。
前几年,公众有了消费能力后,对电影处于饥渴状态,饥不择食,有闲钱,又要消磨时光,什么电影都愿意买票去看,但后来他们发现,很多片子是不值得花两小时的时间去看的,即便有明星大咖也拉动不了票房。但也有一些电影厚积薄发,靠口耳相传,最终收获了不错的票房,这说明观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重视影片的质量,这对严肃做电影的人来说,是莫大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