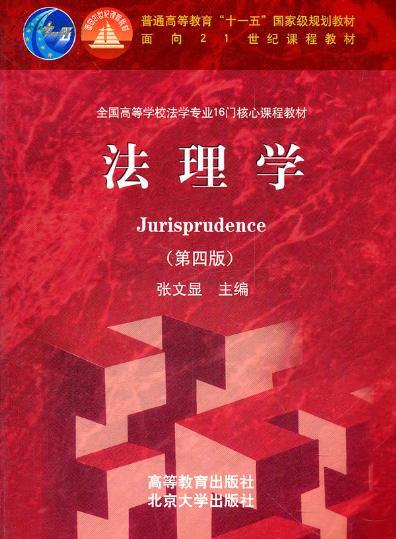白马非马的解释 帮我解释一下“白马非马”的意思?
《白马论》是《公孙龙子》最为知名的一篇,然其“白马非马”论题并不易确切解读。在《白马论》中,公孙龙把他的“是”即“等”,“非(不是)”即“异”、“不等”作为论证“白马非马”的方法,通过“白马”与“马”有“异”、“不等”便得出“白马非马”结论,体现了他那种“甲是甲”的思维模式及各物为“独”的思想。

通过详细分析,我们认为公孙龙“白马非马”论题不能笼统地解读为“白马不是马”,而应是“白马”为“定所马”,不是“马”那种“不定所马”,与公孙龙的“白马”有“定所白”,没有“白”那种“不定所白”为同一思想,表达出“定所马”与“不定所马”、“定所白”与“不定所白”相离、没有联系,即殊、共相分离思想。

另外,很多学者解读“白马非马”为“白马不等于马”,我们给予了否定。
公孙龙(约前320—250),姓公孙,名龙,字子秉,战国赵人,为先秦名家之集大成者。公孙龙生活时代当与燕昭王、赵惠文王、平原君、孔穿、邹衍同时,孟子、惠施稍前,荀子稍后。公孙龙的思想集中在《公孙龙子》一书中,其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十四篇,今存六篇。

今本《公孙龙子》一书,其《迹府篇》为后人集其事迹而成,非公孙龙亲笔,余之《白马论》、《通变论》、《指物论》、《坚白论》、《名实论》五篇,可信为公孙龙本人作品。《白马论》是《公孙龙子》一书最知名的一篇,然而学界对其文意乃至“白马非马”论题的理解仍多分歧,我们提出自己的解释,以便与学术同仁共商。
若要透解《白马论》,不借助《通变论》将难以对公孙龙“白马非马”论题的论证方法有确切之了解,不借助《公孙龙子》各篇之文互证,亦难以对“白马非马”论题的含义有确切之了解。
在《通变论》中,公孙龙论证“二无一”论题涉及“左右无左(右)”、“羊牛非马”、“牛羊非鸡”、“青白非黄”、“白青非碧”五个命题,分为三个层次:
命题中,“左右”与“左”、“右”的差异小,同于“羊牛”与“羊”、“牛”,“青白”与“青”、“白”的差异,双方关系为“类近”;“羊牛”与“马”的差异大,同于“青白”与“黄”的差异,双方关系为“类远”;“牛羊”与“鸡”的差异最大,同于“白青”与“碧”的差异,双方关系为“不类”。
公孙龙在论述“羊牛非马”命题时说:“非马者,无马也。”知“非”即“无”,故命题可换为:
命题中“羊牛”与“牛羊”、“青白”与“白青”没有区别,和“左右”都是“二”的变称,“羊”、“牛”、“马”、“鸡”、“青”、“白”、“黄”、“碧”和“左”、“右”亦都是“一”的变称而已。
从上述命题中看到:
互为“类近”的两者,其关系为“非(不是)”、“无”,即没有联系;互为“类远”的两者,其关系为“非(不是)”、“无”,没有联系;互为“不类”的两者,其关系为“非(不是)”、“无”,没有联系。
在公孙龙看来,与某物关系为“是”,发生联系,则只能是与该物没有任何差异的自身,即:
互为相等的两者,其关系为“是”,有联系。
公孙龙将“类近”、“类远”、“不类”统称为“类之不同”(不同类),那么相等之自身则为“同类”。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公孙龙“物”的分类思想如下:
公孙龙看来:
两者有“异”、“不等”,为“不同类”,其间关系为“不是”,即为“非”、“无”,之间没有联系;两者没有差异,“相等”,为“同类”,其间关系为“是”,即一物只是其自己,只与自身发生联系。
公孙龙在本篇《白马论》中反驳客之“白马是马”时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马不异马也。”他的“是”即“不异”、“等”;公孙龙又说:“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他的“非(不是)”即“异”、“不等”。
在《名实论》中,公孙龙说:“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在《坚白论》中,他又说:“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都在强调名与实的一一对应,一名专应一实,一实专应一名,各物为“独”,只是其自己,即只与自身发生联系的思想。
他的“二无一”论题,是在说“二”与构成其身的此“一”、彼“一”之间只存差异,不存联系,互不属于对方,没有包含或被包含的关系,“二”只是“二”自己,“左右”只是“左右”,“羊牛”只是“羊牛”,“青白”只是“青白”,“一”亦如此,此“一”只是这个此“一”,彼“一”亦只是那个彼“一”而已,各为“独”,与自身之外任何有差异的他物之间都没有联系,故“无”。
公孙龙的思维模式为“甲是甲”,他的世界为一个各物为“独”,只与自身发生联系,物与物之间只存差异,不存联系的“离”的世界。公孙龙的“是”即“等”,“非(不是)”即“异”、“不等”,两者关系为“是”,存有联系,关系为“非”,不存联系。
庞朴说:“在《白马论》中,公孙龙只是否定‘白马是马’的存在权,他还提不出任何‘改善’这个判断的办法。两千多年之后,十九世纪的欧洲,有所谓宾词确定论者,继续着公孙龙的事业,提出了宾词内涵应该和主词绝对同一的主张。
譬如‘白马是马’,他们认为,应该改成‘白马是白色的马’,否则绝不能容忍。这样一来,系词‘是’字两边的确是相等了,差异和矛盾都没有了。……公孙龙没有像宾词确定论者这样,从内涵上计较宾主词的绝对同一。
”其实,在公孙龙思想中,已经把“是”与“等”,“非(不是)”与“异”、“不等”看同了,只要两者之间有“异”、“不等”,公孙龙便认为其间不再存有联系,公孙龙的联系只存在于同类事物自身之间,所以在整篇《白马论》中,公孙龙就是通过“马”和“白马”的有“异”、“不等”来论证“白马非(不是)马”,从而切断了应有的联系。
公孙龙的《白马论》从四个方面来论证“白马非马”,通过“马”与“白马”有“异”、“不等”来论证“白马非马”,实为前三方面,第四个方面阐释出了“白马非马”的确切含义,是对前三方面内容的深化。我们依次分析此四方面内容。
1.在《白马论》开篇,主、客有这样一段对话:
客:“白马非马”,可乎?主:可。客:何哉?主: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形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这是第一次论证。公孙龙认为“马”、“白”、“白马”是不同的称谓,有不同的构成意义,“白马”兼“命色形”,“马”仅“命形”,两不相等,故“白马非马”。
2.接下来,主、客之间又展开了第二次讨论:
客:有白马不可谓无马也。不可谓无马者,非马也?有白马为有马,白之,非马何也?主:以“有白马为有马”,谓有白马为有黄马,可乎?客:未可。主:以“有白马为异有黄马”,是异黄马于马也;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以黄马为非马,而以白马为有马,此飞者入池,而棺椁异处, 此天下之悖言乱辞也。
在公孙龙看来,若说“有白马为有马”,即承认“白马是马”,因“是”即“等”,那么应该“白马=马”,既然“白马=马”,所以主问“谓有白马为有黄马,可乎?”客应答“可”,而不应答“未可”。客之所以答“未可”,是因为白马不是黄马,而公孙龙的“不是”即“不等”,所以公孙龙又说“有白马为异有黄马”,即白马≠黄马。
公孙龙辩论的前提为白马=马,而今白马≠黄马,故马≠黄马,即“以‘有白马为异有黄马’,是异黄马于马也”。
学者多局限在“以‘有白马为异有黄马’,是异黄马于马也”单句中,认为当作“以‘有马为异有黄马’,是异黄马于马也”,所以“白”字为衍文,径删,主此论者有庞朴、栾星、屈志清等人。其实此句是紧接前“(主)(以‘有白马为有马’)谓有白马为有黄马,可乎?(客)未可”之论而来,且公孙龙的辩论有个“白马=马”前提,本作“以‘有白马为异有黄马’,是异黄马于马也”者不误,不应径删“白”字。
如今“异黄马于马”,即黄马≠马,公孙龙的“不等”即“非(不是)”,所以“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即“黄马不是(非)马”。
若承认黄马不是马,黄马中没有马,而以白马是马,白马中有马,不合逻辑,故说“以黄马为非马,而以白马为有马”为“悖言乱辞”。
公孙龙否定“白马为有马”,在他看来,“非马”与“有马”相矛盾,他的“白马非马”即“白马无马”,这与《通变论》用“左右无左(右)”来论证“二无一”,又由“二无一”推导出“白马无马(白)”一致。
3.公孙龙接着说:
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马不异马也。所求不异,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
可与不可,其相非,明。如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
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马皆可以应;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马独可以应耳。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马非马”。
这是第三次论证。公孙龙继续用他的“白马是马”应“白马=马”来展开辩论,既然“白马=马”,也即“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马不异马也”,所以求马、求白马,“黄、黑马”应“皆可致”,而不应“有可有不可”。
实际情况是“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不可以应有白马”、“马者,无去取于色,黄、黑马皆可以应;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所以色去,唯白马独可以应”,故“白马≠马”,而“不等”即“非(不是)”,所以“白马非马”。
4.客在这个时候已经看出公孙龙是在用“马”与“白马”的有“异”、“不等”来论证“白马非马”,故问道:
以马之有色为非马,天下非有无色之马。天下无马,可乎?
客方意思是,如果依照论主所说,“马”之有色便不再是马,那么天下充满了各色之马,并没有无色马,依主所言,天下就是没有“马”了。论主反驳说:
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已耳,安取白马?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
谭戒甫:“‘有马如已耳’,如、而二字,古通用。”伍非百评论这段话说:“公孙答以‘马固有色,故有白马’,……是白马不得为非马,在公孙意中,已不啻承认之。然而公孙知其辞之自陷也,故急转其论锋曰‘故白者(即白马——引者注)非马也’。
此语殊奇突。白者非马,黄者非马,黑者非马,……试问何者为马耶?……公孙始终避去不答,辞近乎遁。”其解不确,公孙龙这段话已表明他的“白马非马”论题不能笼统的理解为“白马不是马”,因为这个论题中的“白马”是殊相马,这是公孙龙本人所承认的,故“马固有色,故有白马”及前之“白马者,有去取于色”,公孙龙前说“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所以他不否认“白马”亦“可致”,黄森对此评断说:“‘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无意中却肯定了黄、黑马是马,当然逻辑上必然包含白马在内。
这是公孙龙在论辩中的失误,同他自己提出的‘白马非马’的命题是自相矛盾的。”此论亦不确,因为黄森同伍氏,把“白马非马”论题笼统地解读成“白马不是马”了。
公孙龙“白马非马”论题中,“白马”为殊相马,而其“马”一词,取共相义,不取殊相义,为共相马,故“使马无色,有马如已耳,安取白马?”及前之“马者,无去取于色”。为殊相的“白马”是由共相之“马”与共相之“白”相结合而成,但这个为殊相的“白马”与原之共相“马”、共相“白”之间并没有联系、相离,故“白马者,马与白也。
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公孙龙“白马非马”论题的含义为“白马”这种殊相马不是“马”那种共相马,“白马”这种殊相马中没有“马”那种共相马。
客不明论主这层意思,把论主的“白马者,马与白也”简单地理解成“白马”就是“马”和“白”,没有理解此句中“马”、“白”只取共相义,不取殊相义,“与”字,即下文“合马与白,复名白马”中的“合”,同《坚白论》“坚未与石为坚而物兼,未与物为坚而坚必坚”及《指物论》“指与物,非指也”中的“与”,为“相与、相合”义,不是表并列的词,所以客进而把论主“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简单地解读成“白马”因为有了“白”便不再是“马”了,故反驳道:
“有白马不可谓无马”者,离白之谓也;不离者,有白马不可谓有马也。故所以为有马者,独以马为有马耳,非以白马为有马。故其为有马也,不可以谓“马马”也。
谭戒甫:“‘有白马不可谓无马’者,犹云‘有白马为有马’。”客方意思是,依照论主您的看法,若说“有白马为有马”,即承认“白马是马”,那是因为把“白马”的“白”离掉的缘故,即“‘有白马不可谓无马’者,离白之谓也”。
如果不把“白”离掉,那是“白马”,依论主之意,“白马”不是“马”,所以“不离者,有白马不可谓有马也”。这样说来,“白马”之所以为“马”,只是因为“白马”中的“马”为“马”,不是因为“白马”为“马”。
如果“白马”不是“马”,是因为有“白”,即“不是‘马’的词 马”便“非马”、不是“马”,这样一来,人们为了称呼一匹马,便只能用“马马”这种称呼了,但现实中人们不用“马马”来作称呼,所以论主您的“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不合常理。客的这种反驳是无力的,客并不明了“白马非马”论题含义,所以在篇末公孙龙将他“白马非马”论题的确切含义更为明白地解释了出来:
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合马与白,复名白马。是相与以不相与为名,未可,故曰“白马非马”。
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
其“是相与以不相与为名,未可,故曰‘白马非马’”句末,今本多衍“未可”二字,我们据金受申说删,这样的两句话意在深入地解释“白马非马”含义。可以看出:
(1)“马”、“白”代表共相,取其共相义,不取殊相义,故说“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白者,不定所白”及前之“马者,无去取于色”。
(2)“白马”代表殊相,故说“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及前之“马固有色,故有白马”、“白马者,有去取于色”。
(3)殊相之“白马”由共相之“马”、共相之“白”相与、相合而成,故说“合马与白,复名白马”及前之“白马者,马与白也”。
(4)殊相不是共相,殊相中没有共相,其间相离、没有联系,故说“定所白者非白也”、“相与以不相与为名,未可”及前之“使马无色,有马如已耳,安取白马?”和“马与白,马也?”
同时,篇末的这两句话亦在表明:能抽离掉的“白”为共相之“不定所白”,因这个“不定所白”是“忘之而可”的;“白马”之“白”为“定所白”,而“定所白者非白”,即这个殊相之“定所白”不是共相之“不定所白”,因而这个为殊相的“定所白”是不能“忘”的,即不能从“白马”身上抽离掉。
自清·傅山将“离白之谓”那段话起首的“曰”字看作“是与上文一人口气,非又设一难问之人也”而归为论主之语后,得到现代多数学者的认可,如庞朴、栾星、屈志清等人,我们不认可。
我们认为“离白之谓”那段话起首的“曰”字代表的就是客语,不是“与上文一人口气”,“离白之谓”是客方的观点,非论主观点。公孙龙反对把“白马”中的“定所白”抽离掉之后来谈论“白马”与“马”的关系,反对客“‘有白马不可谓无马’者,离白之谓也”的论说。
公孙龙在《指物论》中说“物不可谓指”、“物莫非指”、“物不可谓无指”,谓“物”没有“共相指”,但都有“殊相指”,如果“物”没有了“殊相指”,便不再是其自身了,即“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之意,也就是说“白马”(物)虽然没有“白”这样的“不定所白”(共相指),但有“定所白”(殊相指),不能把“定所白”从“白马”身上离掉,因为离掉之后,“白马”就不再是“白马”了,关于“白马”与“马”之关系的讨论也便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公孙龙反对把“白马”中的“白”(定所白)抽离掉,这种“白”(定所白)不能“忘”,基于此点,《迹府篇》说:“公孙龙……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假物取譬,以‘守白’辩,谓白马为非马也。”所谓“守白”二字,即公孙龙反对客“离白之谓”之义。
这最后一次的论证,可以看出“白马非马”即“白马无马”,论题的确切含义为:
“白马”是“殊相马”,不是“马”那种“共相马”,“白马”这种“殊相马”中没有“马”那种“共相马”,“殊相马”与“共相马”相离、没有联系。
传统解释中把“白马非马”论题简单地解读为“白马不是马”,失之笼统。我们对“白马非马”论题的这种解读亦完全适用于“白马非白”论题,“白马非白”即“白马无白”,亦不能笼统地解读为“白马中没有白”,其确切含义应为:
“白马”仅有“定所白”这种“殊相白”,没有为“不定所白”的“白”那种“共相白”,“白马”所具有的“殊相白”不是“白”那种“共相白”,“殊相白”与“共相白”相离、没有联系。
“白马非白”论题更为确切的提法应为“马白非白”,不能笼统地说“马的白不是白”,而是“白马”的白只是为殊相的“定所白”,不是为共相的“白”这种“不定所白”。我们对“白马非白”论题含义的这种解读是否可以在《公孙龙子》一书中得到证明呢?当然可以。
我们先看公孙龙在本篇《白马论》中的论证:
其一,“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形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据此亦可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形非命色也,故曰‘白马非白’。”
其二,“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亦可曰:“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白也?故曰‘白马非白’。”
其三,“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合马与白,复名白马。是相与以不相与为名,未可,故曰‘白马非马’。”亦可曰:“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合马与白,复名白马。是相与以不相与为名,未可,故曰‘白马非白’。
”所谓“相与”即“白马者,马与白也”、“合马与白,复名白马”中的“白马”,为殊相,由共相相与、相合而成;所谓“不相与”即“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之共相“马”、共相“白”;所谓“相与以不相与为名,未可”即“白马非马”、“白马非白”。
其四,“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冯友兰说:“此白物或彼白物所表现的白,是‘定所白’的白,……‘定所白’的白,是具体的、个别的白,不是一般的、抽象的‘不定所白’的白。白马的白,是‘定所白’的白,‘定所白者非白也’,所以白马非白。”为明言“白马非白”者。
我们再看他篇中可以证明“白马非白”的论述:
其一,《通变论》中“二无一”论题可直接服务于《白马论》,曾祥云说:“‘白马非马’之论,从其思想实质来说就是‘二无一’。”所以“二无一”即“白马非马”、“白马非白”,或者说“白马无马”、“白马无白”。
其二,在《指物论》中,公孙龙说“而指非指”,即“殊相指”(定所白)非“共相指”(不定所白),亦即《白马论》中“(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之意,即“白马非白”;公孙龙又说:“天下无指者,生于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
”即“共相指”看不见,不能被具体感知,因为可见、可感知之“指”只为“名”所代表的“殊相指”,“名”不代表“共相指”。所谓“共相指”即本篇《白马论》中“白”这种“不定所白”;所谓“殊相指”即“定所白”;所谓“名”即“合马与白,复名白马”中为“名”的“白马”,代表的为“殊相白”,即“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所谓“(名)不为指”,即“名”不代表“共相指”,即“(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亦即“白马非白”。
其三,在《坚白论》中,公孙龙说:“坚未与石为坚而物兼,未与物为坚而坚必坚。其不坚石、物而坚,天下未有若坚而坚藏。白固不能自白,恶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则不白石、物而白焉。”共相不依待外物、殊相而能自足其身,也即共相“白”这种“不定所白”能自足其身,不依待“白马”这个“物”中为殊相的“定所白”,所以“白”与“白马”相离,没有联系,亦即“白马非白”、“白马无白”。
以此看来,《白马论》篇末“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句下当有脱简,王琯说:“‘定所白者非白也’句,文义上下不完,似有漏误。”王琯不知所脱为何,我们据文意补脱为“马者,不定所马,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马定所马也,定所马者非马也”,这是确切解读“白马非马”论题的关键。
公孙龙“白马非马”论题就是说“白马”是“定所马”(殊相马),不是“马”那种“不定所马”(共相马),其间相离、没有联系。
中国文字简单,公孙龙表达共相之“不定所马”和殊相之“定所马”均用“马”字,表达共相之“不定所白”和殊相之“定所白”均用“白”字,在字形上不作区分,所以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白马非白”可简单表述为“马非马”、“白非白”,谓“定所马(殊相马)非不定所马(共相马)”、“定所白(殊相白)非不定所白(共相白)”,这里的“非”即“不是”、“无”,表示殊、共相间相离、没有联系,这与公孙龙在《坚白论》中说:“坚未与石为坚而物兼,未与物为坚而坚必坚。
其不坚石、物而坚,天下未有若坚而坚藏。白固不能自白,恶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则不白石、物而白焉。黄、黑与之然。石其无有,恶取坚、白石乎?”表达出共相不依待殊相而能自足其身,所以与殊相相离、没有联系的观点相契合。公孙龙这种论题显然是为论证他那“离”的世界观而服务的。
依此,“白马非白”论题与“白马非马”论题具有同等论证旨趣。公孙龙在《指物论》中所说的“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即此篇“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意,即“白马”之为“物”,均有“定所白”属性(殊相指),而“定所白”不是“白”这种“不定所白”(共相指),亦即“白马非白”,所以“指非指”即“白非白”(白马非白)。
另外,公孙龙在《白马论》中之所以采用“白马非马”这种论题,实际上是为了使自己的正名学说在那个名、实相乱的时代更易受到人们,尤其是官方的注意,以便达到《迹府篇》所载“(公孙龙)欲推是辩(即‘白马非马’——引者注),以正名实,而化天下”之政治目的。
学界颇流行一种新观点,将“白马非马”解读为“白马不等于马”,并进而认为公孙龙没有切断殊、共相之间的联系,只是在表达殊相与共相之间有差异、不相等而已,如屈志清说:“公孙龙对‘白马非马’的整个论证过程,都在于强调‘白马’与‘马’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
通读《白马论》,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公孙龙主张‘白马不是马’的结论,……他讲的‘非’,相当于‘异于’、‘不等于’或‘区别于’的意思。”陈癸淼说:“他(公孙龙——引者注)的‘白马非马’实际上就是‘异白马于马’,则‘白马非马’之‘非’字可以肯定即‘异于’之意。
‘白马’与‘马’当然有异,所以可说‘白马非马’。”胡曲园、陈进坤两人进一步说:“公孙龙在这个命题(即‘白马非马’——引者注)上所使用的‘非’字是作为‘别于’或‘异于’之义而言的,……‘白马非马’这一命题并不割裂个别(殊相)与一般(共相)的联系,……公孙龙强调个别(殊相)与一般(共相)的区别,并非就是割裂了个别(殊相)与一般(共相)的联系。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均以本篇“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作为解读“非”为“不等于”、“异于”,即“白马非马”谓“白马不等于马”的关键。公孙龙在本篇亦确实是通过论述“马”与“白马”的有“异”、“不等”便直接得出“白马非马”结论,使人觉得“非”字的直接意思应为“异”、“不等”。
其实“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一句中的两个关键词“异”、“非”如果意思全同的话,那么这句话本身就是在无谓的重复,整句话就没有意义了,只有“非”字的意思为“不是”,全句的意思才能顺应,公孙龙在《白马论》全篇通过论述“马”与“白马”有“异”、“不等”便直接得出“白马非马”结论亦应作如是解。
许抗生释“以‘有白马为异有黄马’,是异黄马于马也;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时说:“公孙龙用黄马与马有差异性来证明黄马不是马,乃至白马不是马。”甚确。如果解读“白马非马”为“白马不等于马”,认为公孙龙没有切断殊、共相之间的联系,试问,这种解读岂不与公孙龙那种没有联系的“离”的世界相矛盾?
据他篇之文,公孙龙确实割断了殊、共相之间的联系:《通变论》中“二无一”论题服务于《白马论》,“二”由此“一”和彼“一”构成,如同“白马者,马与白也”、“合马与白,复名白马”中的“白马”,因为“二无一”,所以公孙龙说:“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
”他的“白马非马”即“白马无马”,即殊相马中没有共相马,切断了应有的联系。公孙龙在本篇《白马论》中又说:“以黄马为非马,而以白马为有马,此飞者入池,而棺椁异处,此天下之悖言乱辞也。
”若承认“黄马非马”,而又认为“白马为有马”,是“悖言乱辞”,可见,公孙龙否定“白马为有马”,在他看来“非马”与“有马”是矛盾的,若“非马”成立,那就应“无马”,亦可证“白马非马”即“白马无马”。
另外,在《通变论》篇,公孙龙用“二无一”这个分论来论证“变非不变”这个主论,所以“变非不变”即“变无不变”,而“右有与,谓右,非右”这个分论亦用来论证“变非不变”这个主论,所以“右有与,谓右,非右”亦即“右有与,谓右,无右”,其“右有与”之“右”为共相右,“谓右”之“右”为殊相右,“非右”、“无右”之“右”又为共相右,意思是,共相右与物之后变而为殊相右,这个殊相右不再是原之共相右,殊相右中没有共相右,仍是将殊、共相之间应有的联系切断了。
前引《指物论》:“天下无指者,生于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物之“名”仅代表“殊相指”,不代表“共相指”,因“殊相指”不是“共相指”,亦即《指物论》所说的“而指非指”之意,仍是将殊、共相分离开,切断了其间的联系。
公孙龙在《白马论》中说:“合马与白,复名白马。”又说:“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重复了这种思想,即“白马”这个“名”代表的只是“定所白”这种“殊相指”,不是“不定所白”这种“共相指”。
在《指物论》中,公孙龙又说:“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也。”又说:“天下无指者,物不可谓无指也。”意思是,“物”没有“共相指”,如“白马”中没有“白”这种“不定所白”;“物”又都有“殊相指”,如“白马”有“定所白”,公孙龙切断了殊、共相之间的联系。
前引《坚白论》:“坚未与石为坚而物兼,未与物为坚而坚必坚。
其不坚石、物而坚,天下未有若坚而坚藏。白固不能自白,恶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则不白石、物而白焉。黄、黑与之然。”共相不依待外物、殊相而能自足其身,故共、殊相之间相离、没有联系。公孙龙在《指物论》中说:“且夫指固自为非指,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重复了这一思想,谓“共相指”固自为“非殊相指”(共相指),即“共相指”能自足其身,不依待外物,同《坚白论》中“坚必坚”、“白者必白”意。
在《通变论》中,公孙龙用“羊牛非马”、“牛羊非鸡”、“青白非黄”、“白青非碧”与“左右无左(右)”来共同论证“二无一”,他说:“(羊牛)非马者,无马也。”其“非”即“无”。若直解“非”为“异”、“不等”,将无法解释“非”有“无”意,更使得命题变得毫无意义。我们认为《公孙龙子》全书的“非”字应专守一义,应解为“不是”,有“无”意,即没有联系。
我们看到《墨经·小取篇》作者对公孙龙“白马非马”做出了批评,他说:“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获,人也;爱获,爱人也;臧,人也;爱臧,爱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又说:“马或白者,二马而或白也,非一马而或白。
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可见,其作者是把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解读为“白马不是马”来做批评的,他认为“白马”是“马”,而且“马”应包括各色之马,不仅仅有“白马”。《小取篇》作者当与公孙龙生活年代相差不远,两家思想甚至有同源的可能,所以《小取篇》作者对“白马非马”含义的解读应符合公孙龙原意。
曾祥云说:“《公孙龙子·迹府》载:公孙龙曾与孔穿会于赵平原君家,孔穿以公孙龙‘去白马非马之学’而愿‘请为弟子’。公孙龙说:‘龙之学,以白马为非马者也。使龙去之,则龙无以教。’试想,如果‘非’即‘不等于’,那么,对于‘白马不等于马’这样一个简单命题,公孙龙何以要如此般重视?又有何必要专门作《白马论》反复论证、申明?难道孔穿不愿接受的就是‘白马不等于马’这样一种常识?……解‘非’为‘不等于’,不符合公孙龙本意。
在这一点上,我们维护传统的解释:‘非’即‘不是’或‘不属于’。”此论很有道理。
公孙龙论证“离”的方法就是通过两者的有“异”、“不等”便把他们的关系说成“非(不是)”、“无”,否定掉了其间应有的联系,公孙龙的“联系”只存在于同类事物自身之间。公孙龙正是通过切断应有的联系之后,使各物为“独”,与自身之外的任何他物之间仅存差异,不存联系,才造就了他那个没有联系的“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