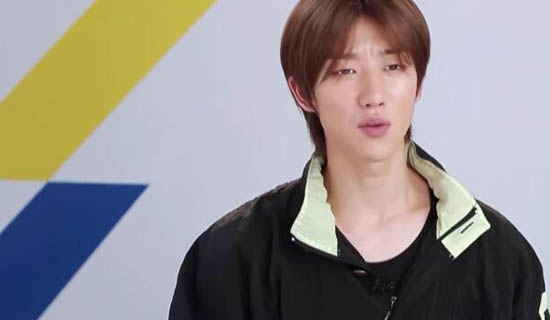杜维明的老师 杜维明:梦想的中国 是精神文明的大国
2009年12月30日晚,新儒家代表人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就“2020,中国新十年”主题接受凤凰网与正义网联合访谈。
西方价值有普世意义,东方价值同样有普世意义
凤凰网资讯:未来十年后,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之间会以什么样的格局来存在?
杜维明: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将来大概不会只是东西文化的核心价值对话,是更广的东西南北。所以我说我们的关注点,除了北美和欧洲以外,对印度、拉美、伊斯兰世界、澳洲等各个地方的核心价值都要关注,我们的参照要扩大,我们要走出一条不同于非东即西这种道路。
甚至我还认为现代化过程中间,可以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也就是现代性之中传统的塑造力,以前总认为传统是现代之外;现在发现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现代性也有一种塑造作用。
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影响力不完全在经济,应该是在文化。文化的影响力,是在多元的背景下发挥积极作用。所以儒家可以跟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之间进行对话,不是和其他大的思潮之间抗衡的关系,而是兼容并包的关系。如果不能够走到那条路上,它只是变成一种区域的、地方的价值,不可能成为普世价值。要成为普世价值,应该跟现在在世界各地的一些普世价值进行对话。
我认为现在文明之间的对话,最低要求也是最必要的条件,就是儒家的金科玉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人和人之间,地方和地方之间,国与国之间,这个可以成为一个重要机制。如果我们的视野比较宽阔,所考虑的问题比较长远,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利益问题,而是国际秩序的问题,同时还要是人类的存活问题,也就是生态环保,这些问题都来考虑,都成为我们关照的对象,那我觉得东亚所代表的儒家传统,它的说服力就不只是限制在东亚,这个说服力也不应该来自有意造作的软实力,而是应该把发扬它的核心价值作为最重要的工作。
凤凰网资讯:在您看来,下个十年以及未来更长时间,儒学如何与自由主义结合?
杜维明:在政治方面,我认同自由主义,因为我强调市场经济、言论自由、法治、民主、个人尊严。
在经济方面,我比较倾向社会主义,因为我认为公平、平等、正义、向弱势群体倾斜、注重社会的融合和社会的和谐等,而自由主义比较强调竞争。
在文化上面,我是比较倾向不用保守就守成,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这是我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化资源,所以我在文化认同上面,以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作为主要的资源。
希望社会越多元化,越能够走向民主,重视人权,重视自由,在整个社会的正义、公平上照顾弱势群体。这方面也是我所关怀的。从这方面来说,儒家的传统和自由主义所代表的一些基本价值可以配合。
可以这样说,从五四以来,儒家传统先经过向西化国家学习,也就是学习自由、人权、民主,使得儒家传统里一些已经过时的东西甚至糟粕能够彻底转化;然后再进一步考虑儒家和现代社会互相配合的可能性;再就是能不能通过儒家的人文资源对现代发展过程中所出现弊端做批判性的认识,批判的认识还是一种了解,就是对西方的基本价值要能够再多了解、认识、引进,算是自己的核心价值,能够让它充分体现。
以前的问题是把中国糟粕中的糟粕、儒家糟粕中的糟粕和西方精华中的精华来比较。比如自由、民主、人权,在西方世界还在发展过程当中就认为是代表西方的;而中国譬如说权威主义、专制主义、男性中心主义乃至鸦片,就说是国民性的阴暗面。
这洋对比是不行的,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新时代,是核心价值和核心价值之间深层的文化对话。一方面是西方所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个人的尊严;另一方面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包括正义价值、责任的价值、同情的价值、社会和谐的价值、还有法的意义、人与人之间如何融合协调这些价值。
这个层面的对话我想现在可以开始了,以前并没有在一个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对话,把儒家所代表的价值叫做亚洲价值或地方价值,而西方的就是普世价值。现在新的理解,是西方价值扎根在欧美文化中间,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儒家的这些基本价值,扎根在东亚特别是中国,也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这中间可以互相对话。
儒家思想面临两大挑战
凤凰网资讯:您觉得下个十年当中,儒学、儒家思想的发展,会不会遇到什么挑战?
杜维明:我认为会遇到很大的挑战。
凤凰网资讯:主要是什么方面?
杜维明:任何一个传统的发展,我想用乐观和悲观恐怕不能够描述现在的构想。我提到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第一期当然就是儒学从曲阜变成中原文化的主流;第二期从中原变成东亚文明的体现;第三期就是能不能走出东亚,面向全球?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它发展的趋势是向这方面走。这十年,已经很明显了,下一个十年这个趋势可能更明显。
这并不是乐观和悲观的问题,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传统,如果要进一步的发展,它自己的核心价值、它的开放、多元、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能力一定要保持。但儒家很可能被政治化,可能被与儒家核心价值相违背的力量所腐蚀,譬如儒家是非常重视社会和谐的,但是和谐变成协同一致,这是“和”还是“同”?儒家的“和”,差异化非常重要,“和而不同”。
完全把“和”的价值机械地消解成“同”,对儒家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儒家一直有非常强烈的自我反思能力,乃至对政治、社会批判的能力,甚至抗议的精神。假如说这成为支持现实利益的一种借口,或者作为一种工具,这是很危险的。
另外,现在很明显大家开始重视儒家的价值,但可能助长狭隘的民族主义,不仅可能会使中国人觉得很自信,而且变成很傲慢,甚至完全把儒家当成软实力,我认为这也是不健康的。我对软实力的提法有很多疑虑,软实力是美国提出的,是对美国在世界的霸权的一种体现,除了军事、政治、经济,还要有文化的力量。
我觉得下十年,应该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价值观,我们强调自己的核心价值,同时可以和其他各种不同的、比我们先进的、或是比我们后进的世界共同分享这些核心价值,而不是塑造一种向西方,或者像其他地方纯粹挑战式的软实力。
我们的视野要更加宽,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协调的机制。中国有天下的观念,所以不是完全停留在国家利益,有超越国家利益,甚至可以说超越人类中心的一些基本理想。这些都应该能让它发挥积极作用。
凤凰网资讯: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下一个十年,中国现代化的步子可能会加快,很难慢下来。在儒学与中国的现代化之间,会不会存在一些本质上的冲突?
杜维明:这是很好的问题。我现在在讲全球化,但这个全球化和现代化、西化,也有不同的地方,特别是这个文化全球化,它和文化的多样性是有密切关系的。而且文化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地方化,也是可以连接的。因为文化的全球化可以和各个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一种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从这方面看,儒家能够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因为它自己经过了好多代的自我更新、批判、发展,能够独立提供它的文化能力,所以不仅对于现代化、伦理智慧、精神价值,对全面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也都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现在,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也碰到了一些困境:随着市场经济的突破,使得社会各个不同的领域,都被市场经济所渗透了,成为了一个市场的社会,这实际是很不好的情况。这个市场的力量渗透使得社会滑坡了,特别是导致了诚信丧失这个问题。
儒家作为一个覆盖面宽广,整合也比较深层次的人文思想,对市场经济所导致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负面因素,可以一方面进行反思,另一方面进行全面地批判。当前社会比较浮躁,它就能对现在中华民族的心灵起净化作用,这和佛教、道教作用是一样的。又因为它提倡入世,所以它可以有一种转化,不会因为外在市场、政治的干扰以后,丧失掉进一步发展的力度。
凤凰网资讯:刚刚您讲到心灵精神的净化作用,现在也有很多人感慨中国可能缺乏一个清晰的公共价值,您觉得今后十年,这方面有可能会取得一点进展吗?
杜维明: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民主化的过程就是公共领域的扩大,公共领域的扩大,就是说各个领域包括政治、学术、企业、媒体、各种社会组织,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每一个地方都可能出现一批具有良知、理性的公共知识分子,从多元发展的角度来看,大家讨论辩论的机制越来越完备,而且是有责任地讨论政策、国家世界的重大问题,政策的形成和大家的讨论有很大关系。
公共领域的出现,公共价值的探讨,当然一定要负责任,要和媒体的炒作、互联网上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有很大的不同。很明显,这种力量正在形成。
但同时我们也在担忧权和钱紧密的联系,使得社会出现了极端的不平等、极端的贫富分化。虽然在经济发展上整体来看气势如虹,但从人均所得来看,我们还是相当穷困的。这样一个情况,公共理性,可以通过各种负责任的渠道使得公共价值能够开阀。
凤凰网资讯:现在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我们的物质生活提高了,但是精神价值好象有沦落。就是物质与精神之间,怎么样能够找到平衡?
杜维明:现在我们在经济发展和心态平衡中间的选择,非常值得重视。从比较长远来看,为了中国人的福祉、所有人的福祉来设想,有四个侧面必须同时注意:一是每一个个人的身心健康问题;二是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健康互动问题,一个核心的课题就是家庭,还有人的素质培养,也就是基本的教育;三是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四,从精神价值说,还有人心和天道的关系,就是人的终极关怀。四方面必须同时进行,同时考虑。
真正的对话并不局限于政治经济领域
凤凰网资讯:您看来下一个十年以后,中国有没有向外输出价值观的可能和条件?
杜维明: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条件,而且可能也很明确。现在当然是一个初级阶段,孔子学院只是一个初愿,假如孔子学院能从汉语教学提升至文化乃至哲学和价值的讨论,而不是一个狭隘的发展软实力的方式,更不是具有特殊政治色彩的扩大影响的方式,可能会更有影响力并被分享。
另外在对现代西方所碰到的重大问题进行批判时,如果中国的知识界、媒体、政府等各行业,能够和西方的知识界进行对话,这些对话不应该局限于贸易、金融等技术层次,还应该把不同的核心价值、人类面临的存活问题列入议程。
我们的知识界能否积极参加这些讨论?现阶段看来有点担心,因为在这种讨论中,中国的声音、亚洲人的声音还是非常薄弱的,因为我们也没有主动自觉地向这方面发展,总是限制在一种政治、经济层面。这不是真正的对话,也不是真正的核心价值的共同探讨。
凤凰网资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还是有可能通过对话来解决,是吗?尤其对中国来说?
杜维明:是这样,通过对话来解决冲突,有的时候过分理想化了,过分浪漫;但是没有对话,冲突的出现是非常可怕的,为了避免矛盾冲突所带来的灾害,对话是非常必要的。对话本身是不是一定能够达到和谐?很难说。但是对话是必要的。
儒学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核心价值而不仅仅是软实力
凤凰网资讯:中国和平崛起,但一些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这样一个不确定性力量的崛起仍有忧虑。在未来十年,儒学能不能帮助中国找到一条比较和平的,同时让其他国家放心的崛起之路?
杜维明:如果你看属于文化中国的几个文明,可以发现几个特色。首先它们都是学习型的文明,日本、韩国、越南,包括中国在内,都是乐于与外界对话的文明,同时也比较宽容,各种不同的宗教,各种不同的价值,能够和平共存,能够有一种包容的气象。
而亚细安国家(东盟各国)的运作机制,也受到印尼爪哇文化的影响,所以亚细安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地域化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中国,特别是文化中国所代表的这一地区,也有很丰富的精神资源。从人的观念来出发,它具有包容的气象,包括公益、同情、责任、互信这些基本价值,特别是由于东南亚发展的非常快,总能感觉到一种再自信的倾向。
但是你不能够把儒家的文化工具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来应对冲突,你要把这些核心价值当做自己的内在价值。
我们确实相信,将来国际社会的重组要依靠这些我们在传统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将来也可能起到重要作用的资源。一方面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核心价值有信心,另外我们要把它付诸实施,不仅仅是把它当做一个简单的工具,我想这是一个前提。
凤凰网资讯:回到一个历史方面的问题,从历史发展的一个坐标来看,您觉得当前的中国与今后的十年,在历史坐标上居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杜维明:我觉得这段时间非常关键。因为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中华民族一直在屈辱、悲愤地忍受着很多外在压力,却感觉到无能为力。目前,经济上面出现了新的动力,尽管也碰到很多内在的困难,但毕竟是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中国文化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多积极的作用。下一步就是逐步地建立这个文化平台。如果这个平台能够建立,我想可能从鸦片战争以来,是第一次又能够和传统中国,特别是天朝礼仪大国的精神命脉重新接起来。前一段时间唐君毅先生说是“花果飘零”,现在就有了“灵根自植”的可能。我想,如果我们往前看,这个可能性是绝对有的。
文化认同的形成需要公共领域的探讨
凤凰网资讯:您现在对中国的哪些问题比较关注?
杜维明:基本上是文化认同问题,因为中国的经济在发展,政治夜开始有影响力,但我们想传播到世界的信息是什么?我们自己文化的凝聚力是什么?这仍是个问题。我就很希望它是开放的、多元的,而不是狭隘的、国内的。比如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儒家的人文精神这几方面,如何能够通过一个公共的领域来探讨,来对话,来发展出一种共识。这个共识,不仅仅是在知识精英中,而且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间都能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凤凰网资讯:您对于当前的中国最大的担心还是在文化认同这个方面吗?
杜维明:文化认同固然是我的关切,但我更大的担心还是市场经济所导致市场化的出现上。诚信问题、法律制度、以及太多的潜规则,这些都会使中国在经济面受到很大冲击。比如说,法律制度不能建构,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会有很大的困难,在文化上面当然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创伤。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专业和专注点,我所关注的问题是文化认同,以及中国文化能够向世界传播什么样的信息,怎样进行文明对话,怎样使得文化中国间的互动能越来越健康,越来越频繁。
凤凰网资讯:您是不是也担心市场经济会在下一个十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特别大的冲击或者是挑战?
杜维明:假如市场经济的本身是创造财富,可以开发很多的资源、很多的动力,那么这对文化的发展,绝对有很大的好处,也能提供很多发展空间。但是当市场经济改变了整个社会,让我们的社会成为了市场社会时,那就是大灾难,文化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干扰。
凤凰网资讯:您对这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杜维明:你刚才前面也提到公共领域的扩大,公共价值的涌现,或者通过负责任的言论讨论与辩论对话,使政治在形成的过程中,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有长远规划,而不是着眼于短期效应,这是最好的一条路,这也是在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化进程,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是有的。
凤凰网资讯:最后一个问题,想知道你理想中的,或者梦想中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杜维明:我梦想中的中国,是一个精神文明的大国。精神文明的大国,是建在人民的富强、康乐的基础上,第一我们要成功,我们要站起来,第二我们要追求意义,追求核心价值。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要推已及人,利已利人,我们自己能够发展,我们也希望比我们更糟的地区能够发展。
在世界层面上,我们不仅要对中国,对东亚要有责任感,应该对世界有责任感,乃至于对人类有责任感。人类要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才能够对我们现在所生存的地球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要作所谓精神文明的大国,那么走出的这条路就不是只有中国人能走,而是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分享。人类现在最危险的大问题,就是存活问题,这条宽广的人文精神之路,能为人类找到一种新的归宿。儒家全面、深刻、能够整合的人文精神,会成为各个不同民族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