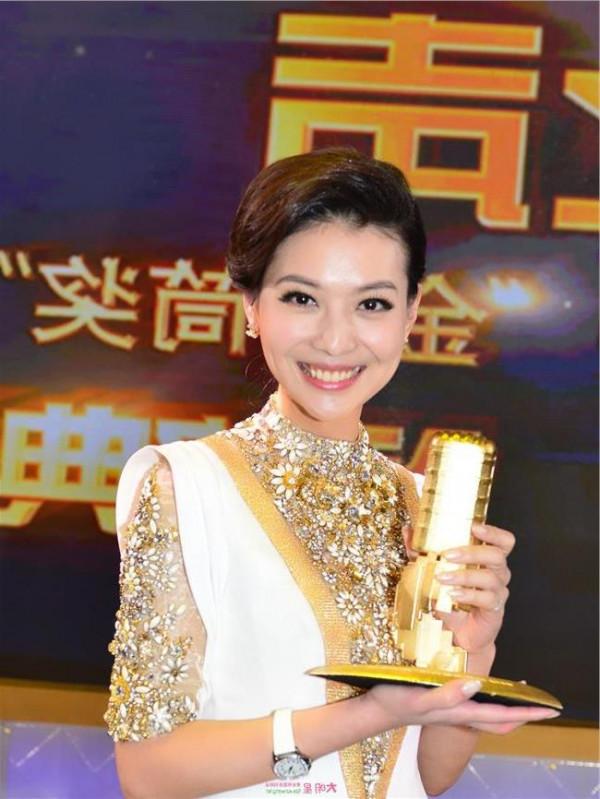巫宁坤英语 余英时序巫宁坤《孤琴》:燕京末日的前期
1949年秋季开学,燕京的"末日"便开始了。中共对于"帝国主义"创办的大学怎样处理虽早已成竹在胸,但在夺权之初,为了收揽和稳定学术和教育界的人心,暂时不动声色…… 一 巫宁坤先生继《一滴泪》之后,将他多年来所写的散篇文章集结成《孤琴》一书。
这两部书恰好经纬相错,交织成文。《一滴泪》是"经",提供了一个连续不断的完整叙事;《孤琴》是"纬",将叙事中某些极重要但只能一扫而过的快速镜头加以放大,使我们可以观赏其中的一切曲折。
作者在《孤琴》中建造了许多通幽的曲径,每一条都把读者带向《一滴泪》世界的深处。 我曾为《一滴泪》写了一篇长序──〈国家不幸诗家幸〉,这篇序当然也完全适用于《孤琴》。
不过现在特别为《孤琴》写序,我却不愿重弹旧调。《孤琴》勾起了我的一些记忆和感想,我想借此机会写出来,与作者的经验互相印证。但首先我要作一点为此书"解题"的工作。
此书为什么以"孤琴"命名?作者在〈前言〉中已作了明确的解说。但作为〈前言〉的〈孤琴〉原是作者1991年的一篇英文散文,现在收入本书的则是别人的译文。1990-91学年作者在母校曼彻斯特学院(Manchester college)从事写作。
这是美国印第安那州的一个"沉闷的小城",作者在这里过了一年十分孤独的生活,基本上完成了《一滴泪》的初稿。但孤独并没有让作者"发疯",如朋友们夸张的预测所云。
相反的,他的精神获得一次最高的升华,所以他说: 我的孤独再也不是一座初露端倪的疯人院,而是一个别具一格的美丽新世界,一个烛照的透明新天地。 他又借用济慈的诗句描述这个新发现的孤独世界。
于是我感到自己像一个天象观察者, 突然一个新星游入他的视野, 寂然无声,在达里恩一个山顶上。 这里我们看到作者精神升华所达到的高度。
在常人眼中,这也许便是一种"疯狂"。但这是苏格拉底所说的"神的疯狂"(divine madness),而且在四类"神的疯狂"中居于最高的位置。因为"爱神"(Aphrodite)恰好是这一"疯狂"的主宰。
(见Plato’s" Phaedrus")试看作者自己对于"孤琴"两字的解题: 孤琴!原来这就叫孤琴。我立即发现这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一个人在冬眠中找到的孤独只是在逃避世界和作为社会动物的自身。真正重要的是达到这样的心态:身在"众生要承受的万千劫难"之中,仍能弹奏孤琴。 精神升华使作者的孤独化为一个"神奇的宇宙",一切文字和艺术作品都顿时在他的心中活了起来。
如果仅仅为了自我解脱,他大可长驻其中,从此远离尘嚣。然而不然,他向往的却是回到承受着万千劫难的"众生"之中去"弹奏孤琴"。恰好说明为什么他对"孤琴"之喻,情有独钟。
我必须提醒读者,这是作者全心全力投入《一滴泪》的撰述期间。他以弹奏中的"孤琴"自喻,因为他正在发出动人心弦的琴音。但是他的"孤琴"之奏不是为了自己赏音,而是出于爱"众生"之一念,让他们在艰难之余,共享他所能发现的"神奇的宇宙"。
上面提到最高一层的"神的疯狂"在这里得到了印证。 这里让我为"孤琴"的意象下一转语,作者的专业虽是西方文学,但毕竟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孤琴"所表达的在骨子里即是中国人的一种共同向往:个人不应仅仅满足于自己"得道",而必须同时帮助一切人"得道",至少也要把一己所得之"道"原原本本地传布给世人。
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便是这一精神的最早呈露。后来大乘佛教的"菩萨行"传入,因为和中国原有的精神取向相同,很快便融合无间。所谓"菩萨行"即指未度己,先度人,愿为众生承受一切苦难。王安石便因为读到禅宗大师一句话,才毅然接受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