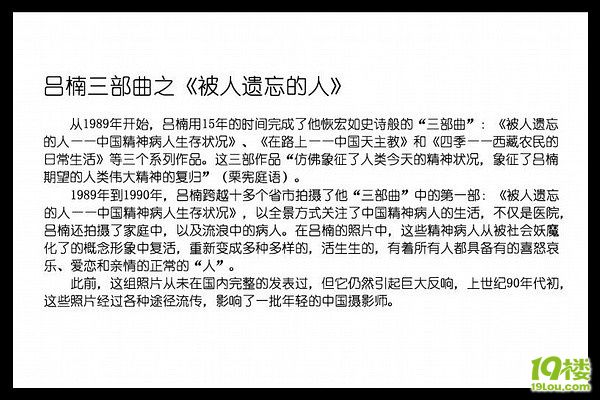当代摄影家王庆松 王庆松:摄影和当代艺术那些事
(以下为王庆松、杨小彦、郑梓煜三人对谈)
最早定义我是摄影师的其实是我自己
杨小彦(以下简称杨):我有点诧异你今年会参加国内的摄影节。在很多人印象中王庆松是个当代艺术家,而摄影展和当代艺术展的区别是它很有群众性。你认同自己是个摄影家吗?
王庆松(以下简称王):1996年到2000年之间,中国当代艺术界开始有很多人介入摄影,但那时候我是拒绝的,我不认为自己是摄影师。2000年以前如果别人这么说我,我可能会急。但事实上最早定义我为摄影师的其实是我自己,2000年我在北京做个展,原定的题目是"王庆松作品展",临开幕前我特意加上"摄影"二字,变成"王庆松摄影作品展"。
杨:一开始拒绝是出于什么原因?
王:那时候我只是借助摄影这个媒介形成了一种临时的"风格",我并没有认为作品本身是个独立的影像。
郑梓煜(以下简称郑):好像1996年你开始做影像之后,绘画你就没有再怎么花时间去做了。你接受摄影家这个身份是因为摄影这个手段更能表达你的想法吗?
王:对,这个可能跟我的题材有关,我的题材跟影像容易契合。不是所有的题材都合适,你想象一下如果张晓刚的题材用摄影的手法,那不是拍遗像吗?还有王广义的题材如果弄成照片,跟样板戏有什么区别?慢慢我就觉得离不开摄影了,摄影太好用了。另一方面当代艺术的圈子也有点无聊。
郑:这些年下来,你对自己的题材有没有一个总结?
王:我一直强调一点: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它像口号,但它真的很准,尤其在中国这种现实当中。
郑:你现在做作品是用数码还是胶片?后期修片多吗?在作品的制作和展览上是不是有很严格的标准?
王:用胶片。过去是8×10,现在是12×20,特制相机,尽量一张搞定,基本上不修片,尽可能在现场把所谓元素控制好。
制作标准当然会严格,但考虑太多你会生气。除了国外的展览好一点,中国的展览基本不可能达到要求。但你要有底线,底线是绝对不允许打破的。如果完成不了,就不要拍;如果展览的效果突破底线,就不要展了。这个是不能凑合的。
摄影节被想象成江湖排座次,摄影和当代艺术站在各自的立场自说自话
杨:2000年,也就是你刚承认自己是个摄影家的时候,中国的纪实摄影已经蓬蓬勃勃,你当时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吗,跟纪实摄影家有什么交往吗?
王:真正的交往是2002年在平遥。此前很多纪实摄影家的作品我是看过的,挺有意思。但那届平遥有个争论(关于摄影与当代艺术的争论,编者注),我开始不知道,他们让我第一个发言,好像有点想让我去搅这个局。我就很客气地说我第一次参加摄影展,是抱着学习态度来。我第一次感觉到摄影和当代艺术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它不是简单的作品的矛盾,而是很难对话,每个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自说自话。
杨:你刚才讲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分裂状态,你觉得虽然交了些摄影家朋友,但有时候很难对话。可是到国际上,你又发现摄影是个影响很大的媒介。我想了解的是,你为什么觉得不能对话,是你自己的原因,还是他们的原因,还是这个事本身的原因?
王:不能对话的原因主要在于有太多利益瓜葛。那时候中国刚有摄影节,曝光才刚刚开始,大家把它想象成江湖排座次,感觉拿个大奖就跟武林盟主似的,所以像庙会,会相互拆台。这跟中国刚开始出现有钱人一样,谁发财了都会引人嫉妒。
那次有个笑话,展览的事情弄完后我都买了火车票走了,突然接到组委会的电话说你可能获奖,赶紧回来。七点半要开始颁奖,六点半才让我回来,这事情中间肯定有矛盾。我不太愿意掺和这个矛盾,有人会认为你一个摄影圈的"外来者"哪怕获一个铜奖也要占掉一个名额。
现在看来,2002年平遥摄影节我可能算是最大的一个赢家,因为基本上只要去了平遥的西方策展人、画廊后来都找我。就摄影而言,我在国外的影响大于国内。
现在中国搞摄影节已经十年了,大家也看明白了,一个金奖不能代表什么,这几年心态要平和得多了。在西方也存在类似情况。一开始我去参与西方的摄影节,所有人对你都很客气,他们不认为你是来抢饭碗的。2006年我在阿尔勒摄影节获了奖,很多采访我的人说你是第一个在阿尔勒获奖的中国人,我说也不代表什么啊,但西方也有人开始紧张了。郑:西方有人紧张什么呢?
王:觉得你抢他们饭碗了。打个比方,假如你是个懂中国书法的外国人,你刚开始到中国来很多人夸你,但如果你正儿八经地在美术馆做一个书法个展,肯定很多人会说:你一外国人怎么可能写得好中国书法?不可能。
郑:他们觉得摄影是个西方产物?
王:没错,他们也开始产生排斥心理。英国的评委觉得英国摄影师应该获奖,法国的评委觉得法国摄影师应该获奖,英法都觉得摄影是他们发明的嘛。尤其这几年,明显感觉西方有这个困扰。
摄影和当代艺术对话的可能性
杨:但是你跟摄影家慢慢建立私人关系以后,发现其实还是可以谈论些严肃的问题的,那谈些什么呢?
王:比如我跟安哥、颜长江他们可以聊具体作品的问题。事实上我做的摄影和纪实摄影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在反映社会现实问题,只不过用各自的方式去做。纪实和观念两边的人其实都挺在意对方怎么看自己的。这个对话,在水平比较一致的两个人之间或者朋友之间,是可以很随意地。
这就像两个农民一个种白菜,一个种土豆,只要双方都做得足够好,一定能沟通。白菜用什么肥,土豆用什么肥,都有基本的标准,而且你卖的是白菜,我卖的是土豆,没有利益冲突。
另一方面,摄影的历史太短,门槛太低。早几年你拿个尼康相机都觉得不得了,现在相机太多了,传统的专业摄影跟大众摄影的距离越来越近了,这种夹层带来了危机感,也才造就了摄影跟当代艺术对话的可能性。我对安哥2002年在平遥说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他说其实我们也是搞当代的,我们在摄影界是很当代的、很前卫的、很先锋的。
杨:你刚才说,只要双方都做得足够好,还是可以沟通。也就是说不管是所谓纪实还是观念,都要有一个专业门槛。但就你来讲,你肯定不会采用纪实摄影这种方式去工作,你会有自己的专业标准。
王:今天很多人热衷讨论风景摄影和景观摄影的关系,其实你做的不够好的话,两者是一样的。我也在开始慢慢地转向,化解所谓纪实和观念的矛盾,把对立模糊化,这就意味着要尽量平实。我尽量不用电脑修图,这可能也是纪实摄影对我的影响,纪实摄影本身有它感动我的一面———它的真实性。
我的工作方式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我也尝试过做一种"无镜头摄影":电脑直接做出来的影像,像无性生殖。但这也就是做一两张玩玩,它不是我习惯的工作方式,我还是喜欢大画幅、喜欢在一种可控的范围内工作。
当代艺术圈假话太多,摄影圈太着急
杨:你觉得跟摄影家玩和当代艺术家玩,有什么区别?
王:当代艺术这个圈子,可能关系太好了,就不敢说真话。估计20年后,很多人老了、死了以后,真话会出来,现在很多评论都很虚假。跟摄影人可以不谈想法,起码可以谈技术:你这个焦点对得很实嘛,哈哈。可以说这支镜头不好,整另一支镜头更好,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沟通,相对平衡些。但当代艺术不行,说你画得不好,这是骂人,而且牵涉的利益很大,一说就得翻脸,这样谎话就多了。
郑:这十年里摄影在中国变成一个显学,在你的角度看,当下国内的摄影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王:总体来说比较浮躁。现在的浮躁是因为这个市场还没建起来,人们总觉得油画都这么火了,摄影可能很快也会火。不管是摄影家还是评论家,有人开始焦虑了,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着急。另一方面就是相似的作品太多了,有时候甚至十个人的作品看起来都像一个人的。
郑:你认为这种相似是因为不自觉的模仿,或者是市场引导?
王:是因为这两年,学术界、媒体、各种中国因素都在起作用,包括几个摄影家开始出名了,让人产生要抓住这个机会的紧迫感,因为摄影很少有这种潮流的机会,过去很难有。
郑:是不是像农民一样今年什么好卖就种什么?
王:不一定好卖,但至少可以抢到位置。因为严格来说中国摄影其实还没有历史,更多的是一种现象。西方摄影历史上的各个潮流演变中国都没有经历过,中国摄影真正的潮流是突然出现的,就像中国的工业化好像也是突然达成的。
面对这么复杂混乱的现实,用黑白是一种逃避
郑:我听你跟一个拍湿版的年轻摄影师聊天,你说你不明白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主张重新回到黑白,好像拍黑白就是一种更纯粹、更本质的摄影方式。
王:现在很多人用黑白的理由其实挺微妙。例如同样拍个建筑,用彩色觉得太直白,转成黑白就感觉不同了,其实这是在利用假象。他很紧张,觉得好像只有黑白才能找得到他的想法,或者保持摄影的纯粹性。事实上,他们没明白很多时候彩色和黑白没多大区别。你做得再旧、再像老照片,我也能一眼看出来是个"赝品"。
面对中国这么复杂混乱的现实,很多时候用黑白是一种逃避,或者臆想自己表达的是一个常人不能看到的空间,其实不过是自己强加的一个套路。用不用黑白必须针对更具体的对象去考虑,不是什么题材一用黑白就纯粹了。
杨:"黑白是一种逃避",这说法很有意思。但纪实摄影主流领域里,绝大多数摄影家认为,黑白才是正宗,黑白才真实。
王:什么类型的东西多了,就尽量不要去做,这是个很重要却也很简单的策略。但很多人不明白,他看到了别人的理想,看到了别人的方法。
说我像杰夫·沃尔,或者说我比杰夫·沃尔还牛,都是胡扯
郑:今年你在法国阿尔勒摄影节做评委,据说原本组委会还打算邀请加拿大的杰夫·沃尔(Jeff Wall)和安德烈亚斯·古斯基(A ndreas G ursky),你跟他们有私交吗?
王:从来没有交往。我去温哥华,就在杰夫·沃尔所在的那个大学里,有人要安排我跟杰夫·沃尔见面,我说我见他干吗?他们经常安排这种所谓的对话,好像中西大比拼,我从来不见。
郑:他们是不是觉得王庆松有点像杰夫·沃尔?有可能受了杰夫·沃尔的影响?
王:十年前经常有这种说法,说我左眉毛像谁,右眉毛像谁,鼻子像谁,你说我像谁啊。最关键的问题是,你能不能认出是我,如果能认出来那还有什么像不像的问题吗?
这几年再没有人说我像杰夫·沃尔了,但又有人很虚伪地说我比杰夫·沃尔牛多了,这也是胡扯,比说我像杰夫·沃尔还胡扯。缺乏共同语境的所谓对话和评判是没有意义的。解海龙的《大眼睛》,中国人都知道它背后是希望工程,你让外国人去评论,他以为是哪个农村女孩在要饭呢。
我们看很多西方摄影作品也觉得特别无聊,但你不能就此说西方摄影比中国摄影差远了,这是个错误判断,你不了解全部的背景。它不像有些人宣称的那么好,但也肯定没你认为的那么差。
不退出生活看生活,你就是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婆
郑:你说你尽量不牵扯到圈子里的是非利益,但你的名声地位却是很多摄影师羡慕的。可能有人私底下会不忿,为什么西方策展人就看上你?
王:最早有些西方人也认为,我有假的一面。但他们一到中国来,就会突然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做。很多人没办法把握生活的这种距离感,很多摄影家只是表现生活,我不是为了表现生活,而是退出生活再去看生活。不退出来的话,你就是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婆,老是去讲一些很虚的问题,好像很专业,其实很无聊。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更远的角度上去看。
郑:我觉得你对距离感的把握特别敏锐。
王:这可能跟我生活经历有关,因为我父亲在我十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是一个大学后勤单位的员工,我母亲没有文化。我那时候认为随便一个家庭的孩子都比我好,别人可能是教授的孩子、很聪明的孩子。所以我会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我,跟别人接触会特别小心。
我有时候跟一个完全不搭界的人能聊了半个小时,旁边很多人不理解。你一个那么牛的艺术家,怎么会跟一个业余爱好者聊那么久?我觉得我们在谈生活,摄影他不一定能跟我聊上,但生活是一样的。如果是一个谦逊的人,我愿意跟他聊,但如果是一个很高傲的人,就根本不可能。大事上要有平和心态,也要保持一种距离。做作品也是,这种距离感才是真实。
保持距离才能超越简单的个人悲悯,发现更大的问题
郑:关于纪实摄影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如果你要拍好一个题材,一定要很深入接触,最好在里面生活个一年半载,才有可能拍得好照片。
王:深入接触可以,但你不能让自己变成拍摄对象的家人,如果你仅仅是因为同情心而去拍,没戏。你要拍一个穷苦家庭,但最后你成了这个家庭的儿子的话,你是站在道德角度看问题。仅仅道德是不够的,而且道德这条路已经有太多人去走了。别人向右,你为什么不向左呢?我的工作方法就是这样,你可以说这投机取巧,但是你要准确。个性和排他性是不一样,不是别人说好,我就非得说坏,而是保持一定距离的,它会公正。
郑:你强调的公正具体是指什么呢?
王:超越简单的个人情绪,站在"人类"的立场而不是单个"人"的立场。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看电视剧可能也流泪,但那是个人情感,事实上这电视剧确实拍得很垃圾。我觉得艺术要想走得长远,就需要距离感。
郑:你说的就是超脱简单的个人悲悯?
王庆松:对,从大角度可能可以反映出背后具体的现实问题,或者一个更大的黑洞,一个更大的不为人知的问题。反正我是喜欢经常抽离出来。拍摄之前深入去了解是我要做的前期功课,但仅仅是了解真实的状况,真正做作品的时候我会抽离出来。
郑:当代艺术圈有一些人故意不把人情世故当回事,觉得一个牛逼的当代艺术家就应该如此,崩了就崩了。你怎么看?
王:那是在过去,过去信息不通的年代,骑马传递信息的年代,需要传说,塑造传说就需要个性,名士就是要皇帝来了都不理。现在是个信息时代,人不能太自作多情了。有一次有个摄影家到一间学校做讲座,回来说没想到我有那么多粉丝,其实就仅仅因为那里是学校,学生就当上课一样,你不能把自己想象得特牛逼。
要走得更长、更远才有意思,不要轻易把话说满,早着呢。你才40岁就把话说满,你能明白50岁的道理吗,就装得像老人一样看透一起了?怎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