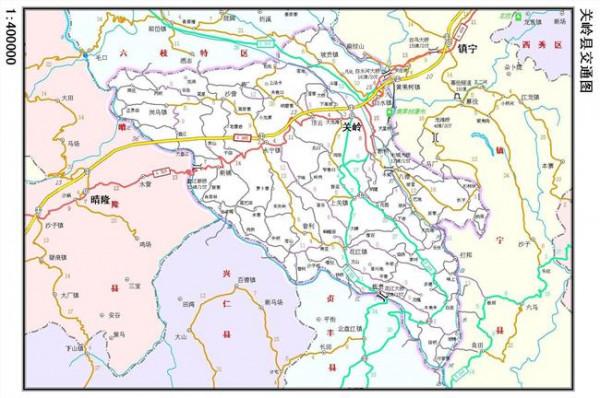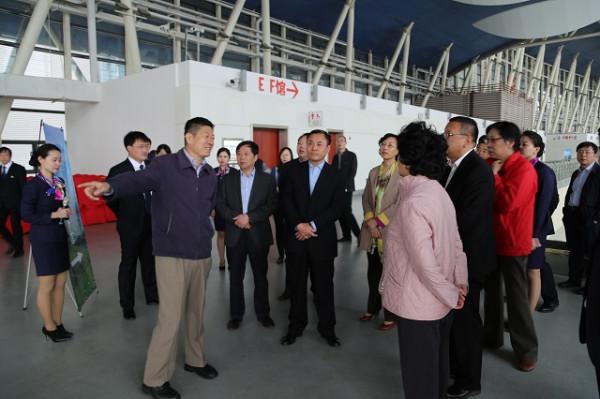潘复生委员:官员问责亟待走向制度化
新华网北京3月10日电(记者任沁沁) “强化行政问责,对失职渎职、不作为和乱作为的,要严肃追究责任。”——温家宝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让来自重庆的全国政协委员潘复生感到欣喜。
他的提案之一,就和“官员问责制”有关。
在西方国家,问责制是一种追究公职官员责任的最基本、最常用的制度,也是公共行政的一种有效治理方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向前推进,中国的行政问责建设也在不断发展。”潘复生说。
早在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有“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提法。2008行政问责制首次写入《国务院工作规则》和国务院工作要点。2009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更是把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实施和推行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具体到落实层面,潘复生认为,还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问责制的有效、合法、合理推行。
他认为,目前对官员问责的界定不够明确,在具体实施上表现为问责的力度不够与问责的混乱。“这种界定不够明确首先体现在问责主体和问责客体的界定上。”
目前看来,中国官员问责大多还是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之间的内部问责(即同体问责),在具体问责方式上也大多是“行政问责”。潘复生说,问责主体理论上说应该是人民群众。
“在已有的问责案例中,问责客体大多还局限在重大事故或灾难中失职的官员,对于一些官员盲目决策造成巨大损失,以及有关部门在选人用人方面的失误失察,问责尚少。”潘复生说,特别是目前,一些各部门“齐抓共管”“集体决策”的事情,个人责任的判定就更加困难,甚至出现“集体负责”就是无责的情况。
问责的内容和范围界定不够清晰。潘复生说,“单就某一个官员而言,在问责中,具体承担什么责任,是直接责任还是间接责任,是政治责任、行政责任还是法律责任,现在还是粗线条的?如果仅仅以‘以平民愤、暂避风头’而去问责,难以令官令民心服口服。表面上可能问出了一个大快民心的‘责任’,最终仍然‘问’得一头雾水。”
问责监督不到位。“不公开、缺乏透明度的问责往往会留下制度外操作的空间,出现所谓的‘伪问责’。”潘复生说,由于尚未形成程序性的官员问责,在问责中谁来监督,监督什么,如何监督就成问题了;问责后,效果如何,公众有何反应,受问责的官员的处理和具体安排等还呈现一种“真空”状态。
缺乏问责官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官员问责涉及不少“高官”,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也还是对国家的事业做出了不少贡献的,很难保证每次问责都是公正的。“这就出现了对这些官员的合法权益如何维护,在不公正问责中遭受的损失如何弥补等问题,需要相关的救济机制作保障,以维护官员问责实施的相对公正性。”潘复生说。
上述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了问责工作推进难、问责工作操作难和问责工作监督难“三大难题”。“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问责制度上的不健全,目前还没有真正实现由‘权力问责’为主向以‘制度问责’为主的转变,问责的法律体系亟待完善。”
目前问责制适用的法规、条例散见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政策文件中。
“已有法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责任政府理念,但没有相应的统一法律制度做支撑,可能会导致该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潘复生说,正因为如此,当一些官员被问责后,有些社会成员提出了种种疑问,包括这些官员是依据何规何矩被追究责任的,被追究责任的官员会不会重新异地做官,允许一些“问题官员”辞职是否可能导致其逃避法律责任等等。
“必须以立法形式,对有关规定加以整合,形成一部全国统一的问责法律或法规,并在操作层面出台和规范细则。”潘复生建议,要创造条件,尽快制定“国家行政问责法”,科学规定问责的范围、对象、事项、处理程序、惩罚措施。
“广义的政治问责制应该偏重于异体问责,离开异体问责的问责制是缺乏公正和缺乏持续性的问责制。”潘复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