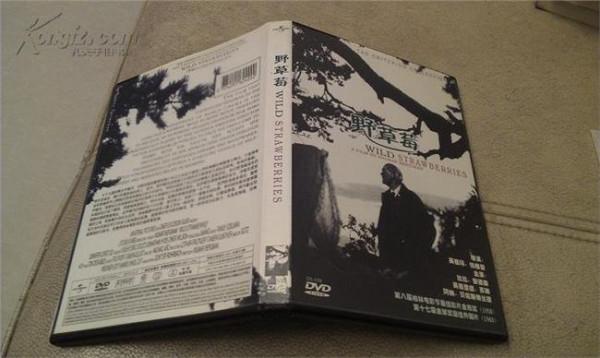【野草莓伯格曼】《野草莓》:时间、回忆与救赎
英格玛·伯格曼1918年出生在瑞典。父亲是一名路德派教徒,长期担任牧师,教子严厉,家庭氛围压抑。伯格曼小时候寄养在乡下的奶妈家,几乎未曾感受到母爱。
1957年,伯格曼在卡洛琳医院写下电影《野草莓》的剧本,同年7月上旬开拍,8月底杀青。
创作《野草莓》时,伯格曼的人际关系一片混乱:我已和第三任妻子分手,仍觉得锥心痛苦。去爱一个绝对无法与之相处的人,真是奇异的经验。……我和双亲痛苦争执,我既不愿意也无法和父亲交谈,母亲和我多次设法暂时修好,但是宿怨已久,误会已深;我们一直在努力,因为我们希望和平共处,但结果却不断失败(《伯格曼论电影》)
《野草莓》讲述了主人公伊萨克·伯格驱车前往隆德接受荣誉学位的一天。在这一天里,他睡出噩梦,重温记忆,检视自己的一生,请求原谅,最后在回忆里得到救赎。
伊萨克·伯格(Isak Borg),这个名字的缩写与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一样。伯格曼晚年回忆说:伊萨克·伯格等同于IB,等同于Ice(冰)和Brog(在瑞典文里,这个词指堡垒),很简单也很廉价。
我创造的这个角色,外观上像我父亲,但其实彻彻底底是我。我在三十七岁时,断绝人际关系,阻隔于人际关系之外,自以为是,自我封闭,彻底的失败。虽然我在社会上成功了,人聪明,井然有序,又有纪律。
显然,《野草莓》鲜明地打上了伯格曼的个人印记,表现的是他的生命以及他对人生的思索。
主人公伊萨克的自我陈述始终冷静而客观,他在开头表示,自己几乎斩断一切关系,坦然沉浸在孤寂之中。
片头序幕结束,迎来伊萨克的第一个梦。这是一个古怪得骇人的梦。梦里,他在街上散步迷路,他看到的钟表只有表盘,没有指针。周遭寂静无人。他回头看到一个路人,他拍拍路人的肩膀,对方转过头来,那是一张古怪得没有形状的脸。
路人顷刻倒下,化为汩汩流出的血水。此时,钟声自远处传来。有马车驶来,被路灯绊住,车上的棺材滑落在地,露出一只手,抓住了前去扶正棺材的伊萨克的手。棺材里的人探出头来,那是伊萨克自己的面容。他惊醒,看了看时间。从整个梦境到现实,没有一句台词,梦里有他的脚步声、心跳声、远方的钟声,醒后现实中有钟表的滴答声。
这一梦,最重要的元素是时间。伊萨克自我表露的淡静,在梦境里被自己摧毁。他焦虑,他感到了死亡的迫近。他的钟表没有指针,他失去了时间,空漠的表盘刻度无法标记他的生命。路人倒地后,远处响起的钟声持续不停,直至梦境结束,敲了将近三十下。时间永不消逝,不为任何一个死者停留。一个人死去了,他只是一个人陷入空虚、孤独与彷徨。死亡,就是不再拥有与外界联结的时间,他被时间抛弃,被时间摧毁。
在这个关于时间的梦魇之后,伊萨克决定开车去隆德。一路虚实交互,他重新审视自己的一生。
路上,儿媳玛丽安和伊萨克一起去探望他的母亲,见证了母子之间的寒暄所透露的冷漠。母亲有20个孙子,只有伊萨克的儿子伊沃德来看望过她;有15个曾孙,却从未见过面。回想起伊沃德只需要死的生活,玛丽安说:他们家的一代代,都是冷酷、死亡和寂寞。
伊萨克冷酷、自私、无情无义的形象,通过侍女的抱怨,儿媳的吐露,去世三十年的妻子在梦境中的控诉,一展无遗。他像冰块一样冷酷,不愿意陷入关系之中。他被判处终身孤独。他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活着的只是尸体。
伊萨克所忧心的未来、难以释怀的过去,都充斥在他的梦魇里,梦境比现实更现实。(关于他的梦魇的影评有很多,不再赘述。)而他留恋的美好,只存在于记忆之中。每当感到担忧和焦虑,他就需要唤醒童年的回忆来抚平自己的内心。
这一天,伊萨克有两段回忆。第一段关于初恋萨拉,他看到堂弟如何追求她,她的纠结与哭泣。第二段回忆在影片结尾,他在寻找父母,找不到。萨拉挽起他的手,领他走向林间一处阳光灿烂的空地,父母在彼岸向他招手。
这两段回忆的奇特之处在于,伊萨克以现在的老年的面貌重新进入了回忆的画面。在第一段回忆里他不被知觉,在第二段回忆里他可以直接参与进去,因而第二段回忆更确切来说是充满渴望的念想。他以老年身份重新融进了回忆的画面里,而且他回忆的内容大多是他当时未曾亲眼见到的。因而,很多影评将这两段回忆也指称为梦境。
我还是把他们理解为回忆,一种模糊了现实与想象的边界的回忆。这种处理方式,好像是表明现在的伊萨克介入了往昔,但事实是,他存活于往昔。伯格曼在《伯格曼论电影》中说:“我一直留驻在童年……”同样,带有伯格曼自传性质的伊萨克,也是漫游在零散的时光里,时而是美好的回忆,时而是真实的梦魇,现实世界只供偶尔探访。时间的界限被抹除,他畅游无阻,才能在回忆里得到救赎。
伊萨克是医生,他在梦境里被考核,医生的第一责任是——请求原谅。最后,他态度软化,意在请求亲近之人的原谅,但在现实里他难以获得宽恕。儿子侧身与他谈话,不想正面交流,只想快点结束寒暄。他在童年的记忆之中,才得到萨拉的牵手与指引,父母的招手与微笑——他在回忆与幻想里得到原谅与拯救。
但是,回忆里的萨拉很快就跑开了,父母也是在隔水的彼岸。伯格曼说:“驱使我拍《野草莓》的动力,来自尝试对离弃我的双亲表白我强烈的渴望。在当时我父母是超越空间、具有神话意味的,而这项尝试注定失败。”所以,在《野草莓》里,他们并未尽弃前嫌,和睦相处,只是一种想象中的和解,人生的、人际的矛盾并未解决。
《野草莓》,让人看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硬,交流的困难,人性的冷漠,生命的孤独与人生的痛苦。时间摧毁肉体,忆想救赎灵魂,但是是停留在经由愿想加工过的回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