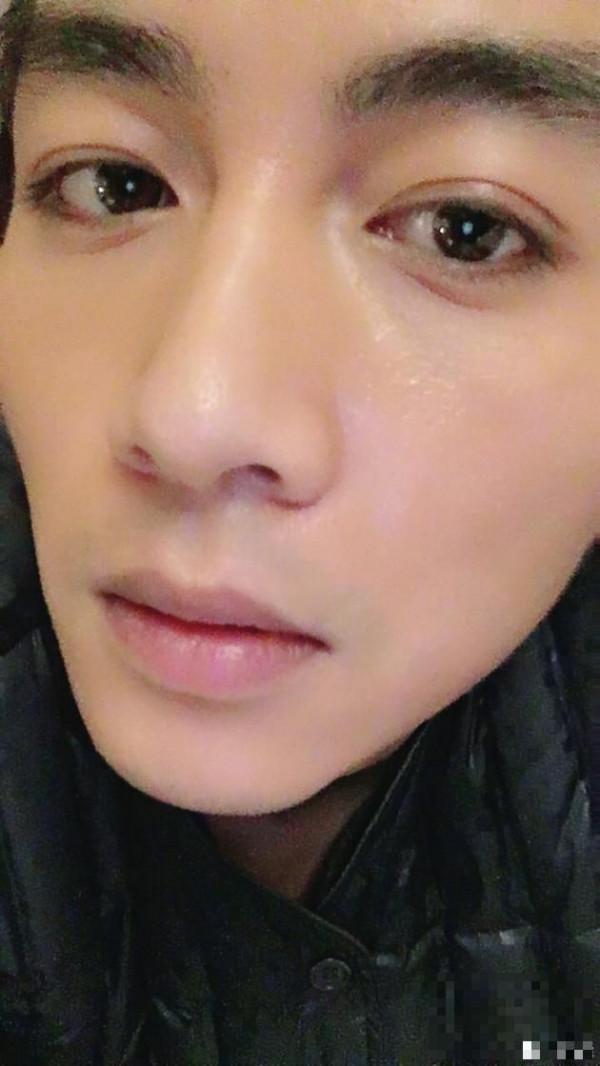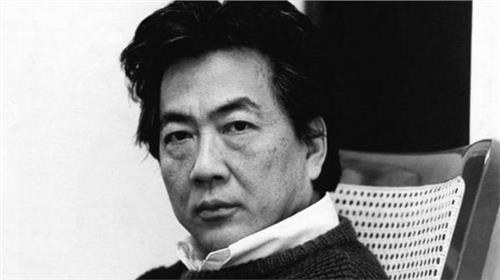陈素真徒弟 我的良师益友陈素真
洛阳有位魏太太是个戏迷。30年代末陈素真随狮吼剧团在洛阳演出时她俩相识,并结拜为干姐妹。魏太太排行老四,陈素真排行老五。我到洛阳搭班后,魏大太又迷上了我的戏,并托人叫我认她做干妈。她知道我有心向陈素真学艺,便从中牵线,请陈素真收我为徒。

陈素真很喜欢我,称赞我为“后起之秀”。她没有想到在那个同行是冤家的年代,我这个已经挂“头牌”的红角,竟然会如此虚心地向比自己仅仅年长六、七岁的同行拜师学艺。她不好意思收我为徒,但碍于朋友的面子,相信我是真诚的,又不忍心拒绝我的要求,干是欣然答应,井将我视为知音,愿以姐妹相称,甘愿将自已的技艺向我倾囊相授。

在洛阳世界舞合,陈大姐教我一套“趟马”和其他表演程式,虽然以前在科班我也学过这些东西,但不如陈大姐的规范、严谨、漂亮。她那颇具京味的程式表演动作,使我受益匪浅。
一套“趟马”,对今天的青年演员来说,人人都会,不是什么高难绝技。但在当时的河南梆子舞台上,谁能走一套规矩漂亮的“趟马”,确实令人刮目相看。三、四十年代的豫剧,以唱为主,很多优秀演员都是以唱闻名,身段表演大都比较粗糙简单。相比之下,陈素真那既不失河南乡土气息又带点京剧味道的台步、身段表演就显得高人一筹,出类拔萃。我从心里佩服这位老大姐,承认人家从各方面比我的水平高。

我到西安搭班后,陈素真也在西安,这时她已与尹晶天结婚,怀孕在家闲居。她怕孩子难成人,便托我给孩子做了个百家长命锁,取个吉利。为的是戴上百家锁,小孩能成人。我就拿出一部分钱,又求人施舍了一部分,给孩子做了个百家锁。

陈大姐怀着身孕,身子越来越笨,心绪也很乱,有心给我说戏实在是力不从心,不教给我一出戏吧,又觉得对不住我。于是,在酷热的暑伏夏天,她不顾炎热和疲劳,趴在床上给我抄写了《女贞花》和《义烈风》两出大戏的唱和念白。这件事若是放在别人身上,也许不算回事,但是放在身怀六甲的孕妇身上,可真是件又苦又累的事啊!师傅对徒弟,大姐对小妹的一腔情怀,尽都蕴藏在这两出“樊戏”的唱词和念白的字里行间。
这时候,魏太太跟随她丈夫也来到西安,她这个戏迷对我格外关心。她经常说我的戏装配不上我的戏,说我的行头不如陈素真的讲究。我倒不是不舍得置买戏箱,也不是买不起,哪个演员不愿意在舞台上穿戴得漂亮,可是当时在西安有钱也买不上好货。
到北京、苏杭去买吧,抗战时期,时局不稳,交通不便,几次想方设法托人代买,都是空手而归。这时,魏太太想到了陈素真。这位“豫剧皇后”的戏箱在当时是一般演员比不上的。那色彩、图案的搭配,针线做工的精细,面料质地的讲究,同京剧、秦腔名家们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高档货”。
魏太太亲自找到陈素真说:“把你的那些行头给兰田吧,她现在在西安唱得红的发紫,可就是缺一堂像样的行头。她是你的徒弟,你又喜欢她。
再说,你现在也用不着,在箱子里锁着干啥?你不唱戏也没进项了,尹晶天又没影子了,你马上生孩子还得用钱,你在困难中,我也不能让你白送给她,您俩这叫互相帮衬,她也有好戏箱了,你也不发愁生孩子没钱了。不要不好意思,你说个数,我去给兰田说。”
这可把陈素真难住了。她没卖过东西,哪会谈价钱。再者,我们这种关系,别说她心里没数,即使心里有数,她也说不出口呀。“要兰田拿两千五吧。”魏太太看陈素真为难,便替她报价。
陈素真为难地说:“按哪方面说,我都不能收兰田的钱。这件事若是放在半年前我结婚那会儿的话,我会分文不要送她一堂好箱。可现在我真充不起英雄侠义了。虽然还没有到秦琼卖马的地步,可也差不多了。再者说,除了兰田,换个人我还不舍得卖给她哩。我不在乎钱多少,可眼下我也真缺钱,就算半卖半送吧。”
俗话说得好,好马需配好鞍,宝刀应配好汉。好角儿有一堂好行头,如同锦上添花,给戏增添了不少光采。有了陈大姐这堂好戏装,我演戏更不敢有半点马虎。在我的艺术生涯中,这是令我永生难忘的一件事。
《三上轿》原本是豫剧中一出老掉牙的戏。剧情简单,唱腔单调,一向被许多戏班当作“送客戏”来演。当年陈大姐从一位老艺人那里学会这出戏后,在唱腔上下了很大功夫,设计出很多新唱腔,在开封一唱便打响了。一出“送客戏”叫她唱成了很受欢迎的“留客戏”,啥时演啥时客满。
我很喜欢这出戏,陈大姐又亲手抄写了她演出的《三上轿》私房本送给我,我捧着那一沓子写满密密麻麻字迹的草纸本,激动万分。虽然当时我识字不多,看着剧本还有很多“拦路虎”,可是,从字里行间我体会到了陈大姐对我的殷切期望。
拿到剧本后,我便起早搭黑地读剧本,背唱词。在唱腔安排上基本是按照陈大姐的唱腔,学习吸收了不少祥符调,但在行腔运腔上又不失豫西调的特色。我演的《三上轿》和陈大姐的《三上轿》就像一对孪生姐妹,虽然血脉相通,但是又各具特色。
1956年参加河南省首届戏曲汇演,我演出了这出戏。57年首次晋京演出,我又在首都舞台上演出了这出戏。同时我还把这出戏传授给了我的学生。
1980年夏天,我的学生郭惠兰在郑州的河南人民剧院演出《三上轿》。当时,我正在郑州参加省文代会。陈大姐在郑州她的孩子家住。我约马金凤一块陪我去请陈大姐看戏。她正在火炉上煎着中药,听说我把《三上轿》教给了徒弟,二话没说,当即抱病去剧场看戏。
散戏后,她高兴地走上舞台接见演员。我请她到接待室坐一会儿休息一下再乘车回家。没想到这一坐就是1个多小时。全团演员来到接待室围坐在陈大姐身边,陈大姐不顾一晚上看戏的疲劳,也忘了自己身患疾病回家还要服药,非常兴奋地一边说一边唱,一边讲一边做,现身说法,绘声绘色地给青年们讲她当年创演这出戏的经过。
1961年我带团到河北邯郸演出。这时陈大姐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身处逆境,在邯郸东风戏校任教。
我的大徒弟张宝英此时已经有了比较扎实的功底。常言说:纳百川才能成大海。我想请陈大姐给她说说《宇宙锋》,点化点化她。趁剧团在邯郸演出之便,我把宝英送到了陈大姐的门下。
大姐一向关心青年演员的成长,很乐意给我的学生说戏,但又为我担心:“我现在是右派,在这里没有人敢主动找我学东西,你现在是党员,宝英是团员,不怕受连累?”
我忿忿不平地说:“我不管啥右派不右派,你是黑是白我心里清楚,我只求你把艺术传授给宝英,在表演上我不如你,我希望宝英将来能超过我。至于别人说什么我一概不在乎。”
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上街买了两条高价鲜鱼让宝英给陈大姐送去。她看到这两条鱼,那削瘦的脸庞上淌下两行热泪。她什么也没有说,宝英也不会说什么,她们一老一少,在大姐那间潮湿、阴暗的小屋里一个认真地教,一个用心地学,不到3天功夫,一出陈派名剧传授给了这个年仅20岁的崔门弟子。
宝英回到团里,我安排团里的主要演员给她配戏。我亲自坐阵指挥排练。在河北峰峰矿区戏院首场演出十分成功。宝英这闺女还真行,不仅水袖舞得像样,唱的也蛮有陈派的味道,我高兴地夸她是“化学脑子”学谁像谁。
剧团回到安阳向领导和观众汇报演出这出戏时,我特意交代剧场在海报上写上“陈素真亲授”5个大字。自57年陈大姐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在她演出的海报上从来不许写她的名子。这5个字若是放在今天写,十分平常,但要在当年的海报上写上这5个宇,确实需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这是我对陈大姐敬重同情的自然流露,我们之间的深情厚谊促使我必须这样做。
十年浩劫后,在北京举行的田汉追悼会上,我与陈大姐劫后重逢。这时我俩都已是容颜改、两鬓白,历经磨难、年愈半百的人了。在八宝山悼念大厅前,大姐紧紧抓住我的手,关切地问我:“兰田,你身体咋样?”姐妹亲情溢于言表。她又关切地寻问:“宝英现在还演戏吗?她对你咋样?”
“宝英和我的师徒关系一直如母女一般,文革中为保我也受了不少罪,现在已经是团里的主要演员了。”大姐听我说罢,又高兴,又激动,眼含热泪,握着我的手,什么也说不出来。
1988年省文化厅和安阳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为我举行舞台生活50周年庆祝活动。陈大姐当时正在山东一个县剧团力青年演员传艺未能亲临安阳。她特意给我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她的得意高足吴碧波专程来安阳并在纪念演出中高歌吟唱。
这几年,我一直想抽空到天津去看望年迈的大姐,但因我一直有病,出不了远门。去年4月初,我从《河南日报》上看到大姐不幸病逝的噩耗,心里万分悲痛,一连几天都沉浸在痛苦的思念之中。大姐是我们豫剧界的一代宗师,是我的良师益友。
因我事前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大姐逝世后也没人通知我,所以很遗憾我没能参加大姐的追悼会,在她临走的时候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为此我内疚了很长时间。后来听说省剧协的同志代我给大姐敬献了花圈,我心里才稍微有了一点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