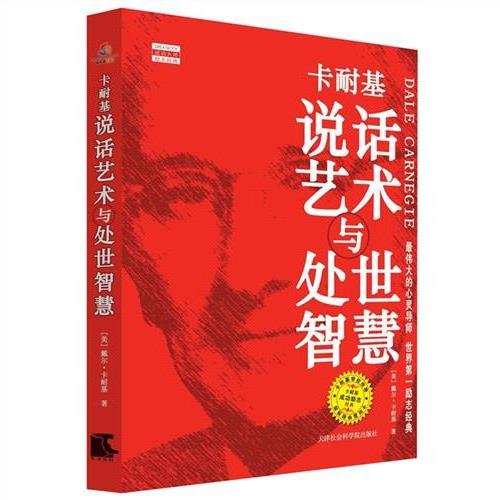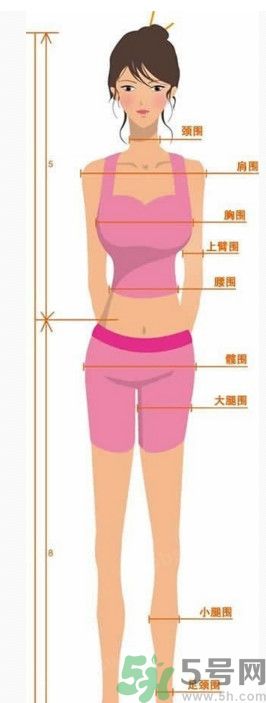爱因斯坦3岁才会说话 爱迪生12岁还不会阅读
舒华和国外很多研究阅读障碍的团队保持着学术联系。她告诉记者,芬兰语的阅读障碍和英语就不一样。芬兰语是一种浅层正字法(正字法是拼字或拼词的规则)语言,其拼词规则没有变化,也就是一种字母组合只对应一种发音,无一例外;而英语是深层正字法,一种字母组合可以对应多种发音,有很多例外。所以,芬兰语阅读障碍的主要问题是速度,即他们的阅读速度明显慢于正常儿童;而英国阅读障碍则主要是语音方面的问题。
相对于英语和芬兰语比较单一的阅读障碍问题,汉语的阅读障碍更为复杂。舒华告诉记者,汉语阅读障碍往往是若干缺陷的组合。“这跟我们的文字有关系。我们的语音比较简单,每个字都是单音节的;但是汉语在读一个字的时候不光要读出音来,还要知道这个字的意思,汉语有好多同音字,所以这就有词素的问题,这是所有语言里比较特殊的。
”舒华说。对母语是英语的人来说,知道读音规则就能读出很多英语单词;但对中国人来说,不认识的汉字基本上读不出来。
进一步,中国人在学习阅读时,要快速把形音义结合起来,所以速度要求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几种因素里面,只要一种有问题就可能导致障碍。目前我们和香港学者认为,汉语阅读障碍是多方面组合的缺陷。”舒华说。
“汉语阅读障碍在脑机制方面也有一些特殊性。”刘丽说,“比如左脑额中回、右脑舌回的异常激活等。”有时,阅读障碍的个体会存在多种语言的阅读障碍。小柯就是这样,他学习英语也有类似问题。
得知自己可能是阅读障碍后,小柯询问能否弥补这方面的缺陷。“通过各种训练是可以弥补的。”刘丽说,由于他现在已经成年,识字精确性的问题已经不明显,现在主要的是阅读速度的问题。“推荐你每天坚持反复大声朗读一段文字,在读对的基础上提高熟练程度,最后能够快速流畅地读出来。”
“从孩子出生到6岁开始阅读的6年中,有很多因素影响其阅读。而这6年的时间也给科学家带来一线曙光,我们可以做很多工作来帮助他们。”舒华说,对于如何帮助阅读障碍者,国际上也经历了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起初是将有阅读障碍的孩子单独编班或者单独安排到特殊的学校,但这还是会对孩子自尊心有影响。
目前的国际趋势有3层:一是改进正常教学,让所有的老师了解阅读障碍,让有阅读障碍的孩子受益;第二层措施是在正常的学校中组织小组教学;最后才是对有严重阅读障碍的孩子进行个别训练。
给舒华留下深刻印象的是,2007年,她到日本参加一个国际阅读障碍学术会议,遇到一位日本母亲非常执著地宣传社会应当重视阅读障碍问题。“日本阅读障碍的研究起步较晚,很多人不接受这个概念。”舒华说,这位母亲的小男孩不能被日本的学校接受,但是这位母亲不放弃任何希望,把孩子送到英国去读书,终于得到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他后来上了大学,学的是化学。”男孩的姐姐写了一本书《我家小弟》,用图片和极其简单的话语向大家讲述弟弟的故事。他们希望,每一个有阅读障碍的人都应该相信自己能够成功。
由于阅读障碍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所以要界定一个人是否有阅读障碍,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随着外界环境变化和个人努力增强,阅读障碍可能在一个人身上消失。“国际上有很多种语言有标准化的测验,能将有阅读障碍的孩子筛选出来,但是中国没有这个测验,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舒华现在所做的大量问卷工作,已经为制定汉语阅读障碍的测查量表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7年,舒华在北京测查了2000多个孩子,2009年,他们又测查了1600个孩子。“测查量表还没有形成正式的文本。”舒华坦言,他们是怀着左右为难的心情在做这件事。由于国内心理咨询从业人员的专业化程度较低,他们担心量表制定好之后被滥用。
而在发达国家,只有临床心理学家或教育心理学家获得相应的证书之后,才有资格使用相关的量表,并且他们不会将量表向社会上随意扩散。“这个测验使用效果已经非常好了。但是目前怎样拿出来、让什么样的人去使用它,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舒华希望,等到社会环境允许的时候再妥善推出。
然而,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进入政府的议事日程。我国的特殊教育多集中在聋儿和盲儿身上。“国际上的特殊教育已经扩展到心理问题了,包括阅读障碍、计算障碍。”舒华说,阅读障碍首先需要基础研究;然后要跟应用研究结合,要让学校、老师、家长、医生、政府官员都知晓阅读障碍。
“我们国家的相关基础研究起步晚,国外已经进行了上百年,因为基础研究做得好,很多概念能让社会公众了解,再加上措施有力,民众就容易接受。现在基础研究虽然在做,但还是不够,到应用就差得更远,概念还需普及。”
阅读障碍在西方是一个很热门的研究领域,因为”知识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是一个国际学术界长期探索的理论问题,阅读障碍正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十分关心和重视这个问题。“因为现在阅读是人最重要的行为之一,人所有的知识、交往都是通过阅读和书写获得的。”舒华说。
发达国家的民众也普遍接受阅读障碍的概念。刘丽告诉记者,在美国的***政策里,有阅读障碍的孩子可以比正常的孩子延长***时间;可以要求老师把题目念给他们听。而且一旦发现一个有阅读障碍的孩子,学校就能从联邦政府获得一笔专门的拨款,以帮助这个孩子。
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的态度,香港的情况都让舒华觉得很羡慕。1999年,舒华作为专家应邀参加香港第一次阅读障碍的学术会议。大概有两三百人参会,包括香港、内地和国外的学者。香港参会人员包括了小儿神经科的医生、教育署官员、大学的研究者,还有家长。
可以说,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香港的研究者进行了全方位的努力。如今,香港很多大学都有阅读障碍的研究小组,已经做出了香港地区儿童阅读障碍的标准化常模,并在基础研究、临床干预和教育教学中使用。“因为有政府支持,所以进展非常顺利。”现在,阅读障碍的研究成果已经在社会上产生影响,使很多孩子受益。
虽然与香港的进展还有很多差距,舒华的团队已经坚持追踪290多个北京孩子长达10年了。“我们每年给他们测一次,测查完后针对每个孩子写一个报告,告诉家长孩子的阅读能力发展得怎么样,哪些方面可能有问题,怎样帮助他们。”张玉平现在负责这项工作,比较明显的有阅读障碍的孩子大概有十几个。家长们的态度基本上比较配合,这让张玉平感到欣慰。
在研究中他们发现,父母的教育水平对阅读障碍的孩子有影响,而且很早就开始起作用。对于语音能力低的孩子,只要他们的父母受教育水平较高,其阅读也没有问题。这是因为受教育水平高的父母可能有更好的策略帮助孩子。“所以,早期鉴别、早期干预是非常重要的。”舒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