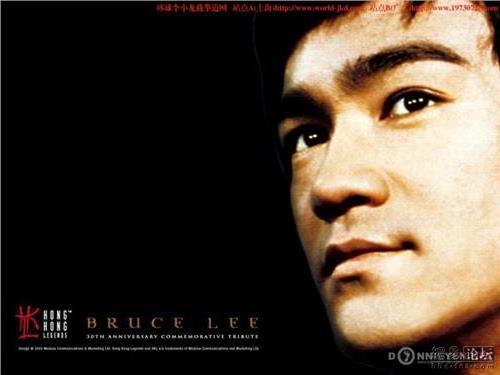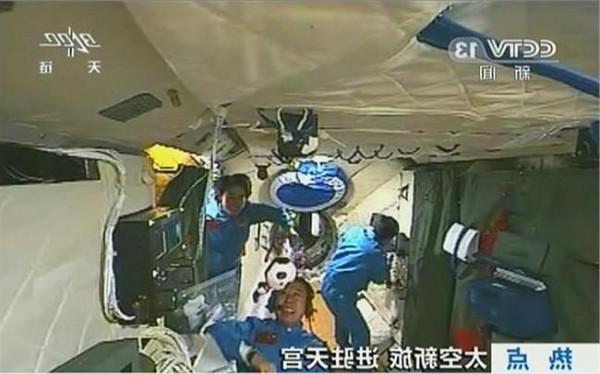刘海龙砍人 刘海龙: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与传播研究的未来
传播学一直以来对身体比较忽视,我也是抛砖引玉,目的是怎样把身体重新放回到传播中,丰富我们的思考。当然,今天我们面临的是另一个相反的问题:身体可能变得不重要了之后,传播又该往哪里走的问题。

之所以在传播研究里面,身体不是核心的问题,大家讨论的比较少,我猜测有这样两个原因:第一个,大家有一个假设,传播是精神的交往互动,基本和身体无关。第二个,我们对于身体问题有一种理所当然的看法,有点像意识形态或者德里达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在场。

我们假设传播的前提是身体在场,所以面对面传播被当成是传播的理想类型。一旦身体缺席,比如大众传播、网络新媒体的传播,就会产生一种焦虑,总是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克服,比如我们要追求更加仿真的交流方式,好象身体在场,我们不满足于文字交流,要看到图像,听到声音,甚至要看到影像,进行虚拟的、全息的交流等等,这些技术都在追求一个东西,就是怎么样能够像是面对面交流。

所以传播学者约翰·彼得斯提出一个问题:在人类交流中人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持缺席?他认为这是传播观念里面一直存在的焦虑。他给我们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的起点。

因为今天吴飞老师给大家的题目是《反思传播学》,上午各位前辈做了很多反思。但反思里有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你站在什么样的视点上反思?上午很多前辈是站在当下反思历史。在讨论传播中的身体问题时,反思的视角会发生一些变化。
一是站在过去看当下甚至未来,如媒介考古学;还有一个是站在未来反思今天,像是看一个未来的后视镜一样。如果未来可能是这样,那么今天的传播应该怎么样往前推进?这是件比较吊诡的事情,许多对未来的想象是科幻。
科幻的东西我们怎么能相信它?这存在一个如何建构我们想象力的问题。我可能会借助文学或是科幻小说、电影来讨论。但是没有办法,我们除了使用这样一些叙事以外,作为人文社科学者很难用其他方式来想象。理工科的叙事不直观,也过于技术化和局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它们是基础,但不是全部。
我今天的讨论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历史,思想史,另一部分是科幻,原因就是上述这些。
约翰·彼得斯在提出上面的那个问题后总结了传播中的身体问题史,给我们讨论传播中的身体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历史语境。他首先讲到了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他强调对话中身体一定要在场,身体不在场没有办法确定交流是否发生。
他以爱欲作类比,通过文字等中介的交流,甚至演讲(当时的类似大众传播的存在),被他认为是滥交,种子的浪费。基督教福音书里的撒播观刚好相反,不区别身体与幽灵。阅读文字时,我们还是用面对面对话的方式来想象交流,通过阅读我们复活作者的幽灵,跟幽灵对话。所以不论是和面对面的身体,还是和幽灵交流,都是一样的,没有太大的区别。
他还提到了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认为身体是障碍,最理想的交流是没有身体的天使之间的交流。天使般的交流没有误解。
洛克对于我们所讨论的传播身体观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人,他确立我们今天所谓自由个体主义的身体观。他认为肉体是私有财产的源泉,身体的劳动形成私人财产,同时身体也是存放个体内部性的容器。所以这就形成了我们拥有自己身体,以及无法脱离这处身体的概念,也就是身体和意识、自我和意识之间的关系。
彼得斯还讲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十九世纪开始电报、电话等现代科技激发了人们与幽灵对话的热情,也就是招魂术。招魂术不仅仅希望跟精神和幽灵交流,还希望看到一个实体,所以产生了招魂术。技术终于使人摆脱身体在场的面对面交流的局限,实现了人类远距离精神交流的梦想,但是反而激发了人们对于身体的渴望。
招魂术往往是利用女性的身体作为中介,就是我们讲的灵媒(medium)。女性的身体是最早我们想象媒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实体,一个具身性的媒介。
进入大众传播的时代,交流中的幽灵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为大众传播其实没有办法面对面交流。
另外他谈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当我们与机器、动物、外星人交流的时候会出现困境时,身体在场的焦虑又会出现。比如与机器的交流,我们无法确定这个机器是在跟我们交流还是它只是对交流的模仿,图灵说的“模仿的游戏”?或者说我们能不能确定跟机器能建立起情感上的联系,换句话讲,和机器能够不能有爱情产生?这个事情之所以很难确定的,很大的障碍是在于机器没有像人类一样的肉身。
这也是一个大家特别纠结的问题,就是你的爱情如何确定能够发生,网恋、异地恋等身体的不在场也会遇到同样的困境,就像《她》(Her)那部电影揭示的困境一样。
跟动物交流的困境也是一样,维特根斯坦说即使一头狮子学会了人类的语言,其实我们还是听不懂它在说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体跟它身体构造不一样,你没有办法体会它的世界。
外星人也一样,当我们看不到外星人的身体,看不到飞碟实体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接收到的信号是来自外星人的消息,还是宇宙中偶然的一个波,即噪音。彼得斯认为这些困境就顺成章地得出一个结论:肉体的在场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讲了一句话:“过去的交流成功标志是触摸灵魂,现在是触摸肉体。”只有肉体在场才能说交流发生。他讲身体(触觉)和时间是不可复制的,它们都具有排他性和歧视性(和你对话的同时就不能和其他人对话),所以身体是我们感受爱欲或者对话的唯一方式。
彼得斯接收了很多后人类主义的东西,比如机器和生物之间的界限在消解,动物与人的界限在消解。但是他在这一点跟后人类主义划清了界限。在这里他采取了一个特别人文(类)主义的,以人为中心的立场,他讲到:“如果我们认为交流是真实思想的结合,那就低估了身体的神圣。
虽然这个时代技术已经可以充分地模拟人体,但身体是否真正在场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在一个访谈中他还谈到这样一个观点,他说:“面对面身体在那里存在(being there)本身就显示了某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本真性(authenticity)和善意”(Kane & Peters, 2010)也就是说只要保证身体的在场,他至少是一种善意,就是我愿意和你在一起,把我这段时间完全排他性的让渡给你,这是传播最基本的条件,我们能够确认的东西。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有这么丰富的传播方式了,还要通过饭局谈事,因为你来了这是最大的善意和尊重。
他认为只有文字、收音机、照片这种模拟的媒介才能产生幽灵,数字化技术不能产生幽灵,因为0和1是确定的,它们之间没有幽灵存在的空间。当然这个观念我并不同意,幽灵的产生是接受者具有的“对话”期待产生的,而不只是媒介的属性。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今天的数字游戏、虚拟技术怎么会让人沉浸其中。
我们要谈传播中的身体就要回到麦克卢汉。麦克卢汉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大部分严肃的学者是不太喜欢他的。每次我们觉得麦克卢汉快要被我们清理出去的时候,过一段时间他又悄悄溜回来了。谈到身体问题的时候,传播研究里面居然最早谈这个问题的居然是麦克卢汉。
他讲“媒介是人体延伸”,还有一句话是“延伸意味着截除”,就是你开始用机器,机器就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替代了你原来的器官。这个视角非常像后人类主义所说的赛伯格(cyborg),所以这个家伙还是很厉害的。
Kittler对他有个批评,他认为麦克卢汉是从身体的角度去考察技术,而不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考察身体。这是他们两个的区别,Kittler可能更强调机器、芯片,硬件本身对传播过程的改变,而麦克卢汉是以身体的尺度去想象、隐喻媒体。
所以我们看到赛伯格讲到从人体的延伸再到人机结合,我们现有的身体是我们使用的第一个身体,第一个假肢,我们完全可以像适应这个身体一样去操纵其他身体。这种看法可以在麦克卢汉的理论中找到起源。
传播学里另外一个涉及传播与身体问题的是媒介考古学,里面也讲到身体跟机器的关系,我们在使用机器的时候成为了机器系统的一部分。Kittler的信息唯物主义是一个代表。当然他跟麦克卢汉讲的有区别,其实我们今天发现麦克卢汉要比基特勒在这个问题上走的更远。
Kittler举过一个例子,他讲到尼采的朋友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晚年作品长篇大论的深度思辨大量减少,而短小精悍的警句箴言在不断增多。尼采回答说,你说得对,我们的写作工具似乎也参与了我们思想性的东西。
尼采晚年视力不好,有一段时间用了汉森的打字球(机),这个打字机是专门给盲人设计的,它像一个球。它把书写的连续过程变成了一个空间的想象。因为它由一个一个的按键构成,是一个一个离散的字母,跟西方人书写时连笔的那种字母写作方式完全不一样。
所以而且尼采的晚期经常用击打、敲打的意象,有人讲跟他打那个打字机有关系,打字砸下去用力很猛,它还经常坏,搞得人很烦。海德格尔也讲,打字机这种东西剥夺了我们身体的本真性,因为你把手的书写功能变成了按键的机械动作;而且打字机是标准化的,每个人书写文字是有他个人的个性,我在里面存在,但是一旦用打字机打出来就完全一样了。
我想到中国的书法,海德格尔的这个观点对我们中国人其实特别好理解。我认为中国的书法其实记录的不是书写内容,而是对人身体运动过程的记录。观看的过程就是回放运笔的起承转合、轻重缓急,学习的过程就是复制这种身体的动作,从而由外而内改造我们的精神世界。因为我们会把书写的特征与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像对王右军、颜鲁公的字的评价往往会讲到他们的人格。
传播研究里讨论身体的另一个理论资源是控制论,它其实也是在讲身体,作为信息系统的身体。身体本身通过新陈代谢,一百多天以后(或者更长时间)我们身体全换过一遍了,但是我们怎么确定这个身体还是原来那个呢?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身体存在的模式,而这个模式是一种信息的组成部分,即DNA。
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讲,荷尔蒙也好、基因也好,包括机器人的软件也好,最终其实都是编码的问题。格里高利·贝特森也谈到这个问题,他提出一个问题,说拐杖是身体的一部分。
在控制论全盛时期,学术界曾经认为它可以打通所有学科。所以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把社会和人也当成机器系统具有相同运行逻辑的对象加以讨论。在他那里文化和自然完全是统一的。当然,在这本书里维纳本人是相当纠结的,从理性上他推出是统一的,但是作为人文主义者,在感情上他接受不了,所以应该“像人那样去使用人”,而不是像自动机器那样使用人。
在传播中的身体问题讨论中,女性主义者可能最为积极,是最早对一系列二元对立发难的。她们乐于打破性别边界,就会顺带带出来对于身体的重新的思考。所以后人类主义是从女性主义者那里最早提出来的。比如哈娜维的《赛伯格宣言》,讲到动物和人类、有机体和机器、身体和非身体的界限在于新媒体条件下正在消失。
海勒斯的信息后人类主义也在强调这个东西,说到了信息形式优于物质实例,身体就是我们用来操控的最初的假肢,我们可以用其他东西来替代我们的身体,人类是可配置的,从而能够与智能机器无缝链接。大家都看过《阿凡达》,这是一个典型的信息后人类主义的叙事。
这里列举了一些科幻的叙事,因为我刚才讲了通过叙事来想象未来的传播中的身体问题,比如《神经漫游者》《黑客帝国》《银翼杀手》《阿凡达》等等,《黑镜》第四季的第四集San Juniper里面,变成了狂想,整个人变成了一段程序,就实现了不朽,可以永远活在那个叫San Juniper的地方(一个软件系统),你可以任意选择一个身体。
所以在后人类主义者看来,身体变得不那么重要,可以完全超越身体。一切都是信息,我们的意识和软件之间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不同。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比。电影《her》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人能不能和机器恋爱?这部电影里面是否定的,因为你没有身体。但是在《银翼杀手2049》里面,那里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向《Her》致敬的场面,但答案却完全相反,它认为是可以的,没有身体的智能软件也可以通过与其他人的身体同步完成触觉的复制,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想象。
我们把未来作为一个后视镜,通过技术去蔽,可以更好地认识我们的身体和人体。这里面当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跟机器交流?过去这不是我们传播学的问题,在今天当我们人的身体和机器之间开始融合,赛伯格时代到来的时候,人机之间界面的交流可能会成为讨论传播的重要的话题。
刚才有老师提到了AlphaGo,围棋在古代还被叫作“手谈”。谈话就是交流,人和AlphaGo,人和人工智能怎么样去交流?人可以体会下围棋的乐趣,也可以表达其思考的逻辑,传授给其他人,但是机器下围棋是怎么思考的,人能否理解它的逻辑?机器的招法非常新奇,现在围棋界已经出现了所谓AlphaGo流,就像过去的宇宙流、中国流、秀策流等等,成为围棋界的时尚。
例如传统的围棋理论认为开局点空角的三三是一个错误的着法,被大家否定,而现在这么走的大有人在。
还有什么尖冲无忧角,新的角部定式,成为了棋手中最流行的一套着法。当然我们可以认为AlphaGo把人类的围棋技术推进了一百年,但是人类棋手能否理解它的思考方式(而不仅是算法)?最近新版的AlphaGo Zero可以不用人类的知识掌握围棋。(PPT图示)
左边的图就跟小孩下棋一样,先从中间下,就想吃子。中间是稍微提高一点,开始有边角意识。右边这个会看到大量基于全局的着法。大家看AlphaGo自我对弈,非常惊讶,看不懂,专业棋手也看不懂。人类下棋时还是有一个“对话”的思维模式,谈话是我说你也跟着我说,所以在一个局部大家会你来我往。
但是AlphaGo下法有大量基于全局计算的脱先下法,你下在这里我不跟着你下,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下,但对方还不理你,又在另外一个地方下。
这就完全摆脱了人类交谈的意识形态,我们还在用谈话的隐喻来想象对弈,但AlphaGo已经超越了这个模式。所以怎么样去想象对手的逻辑,如何手谈?我们人类对于围棋的理解,跟AlphaGo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当然我们可以把它神话,说它的围棋多高,境界多高,但我们真的能理解它吗?真的能学习它吗?现在职业棋手也承认我们没法儿学习,因为你不能理解。
所以这已经不是图灵讲的模仿游戏了,完全超越了人类的知识与想象。我们当然知道机器肯定有弱点,至少后面的版本比前面强,说明前面的着法不是无懈可击。但是人类已经不能判断它哪步是妙着哪步是臭棋,因为你接着下也赢不了它。我们只能接受机器的概率判断,但这个判断是否是完美的呢?我们不知道。
回过头来,总结一下。这些问题对我们传播来讲是挑战还是机会?虽然感觉信息好像成为了未来的中心,在虚拟世界里面,我们可以接入到一个系统,完全可以不受身体束缚,一切都变成了传播。传播、信息变成了社会最核心的东西,好像我们传播学就一下变得很重要了。
但是也许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错觉。如果我们不去思考这些问题,传播学也可能会被取消。所以我们应该怎样讨论这个问题?比如如何跟机器的交流,如何和分布式的认知打交道。还有,自然与文化的界线消失了以后,我们怎么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信息/传播、物质/身体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浮动之后,大家讨论的具身化的问题。
人还需不需要身体?具身化是不是我们传播或者人类存在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你可以跟仿生人结婚生子吗?你可以爱上一个机器,爱上一个程序吗?这个在刚上映的《银翼杀手2049》里面有非常多的反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当然海勒斯提出来我们不用再纠结传统的身体在场/缺席的逻辑,回到一个控制论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模式/随机的问题。我们过去认为噪音是不好的,噪音本身就变成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很重要的因素,那怎么样处理和噪音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处理随机性的关系,这可能是我们未来要讨论的问题,而不是我们今天很纠结的在场还是缺席的问题。
另外对于我们来说,当传播信息成为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底层基础设施的时候,我们传播学里研究的传播系统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超社会或元社会系统,当然传播学的地位一下就提高了。但那个时候这还是不是传播学能解决的问题,或者作为传播学者我们还能不能跟上时代?
我想这就是未来我们要面临的挑战和机会,当然以上还是一个很初步的想法。除了技术的可能性外,我们还会面临传统的权力分配的问题、身体的等级问题。就像我经常在地铁里会看到有人拿着手机让你扫码。这么一个虚拟世界的推广问题最后却要通过最原始的身体在场来解决,这也许就是我们在放飞想象力之后仍然要清醒认识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