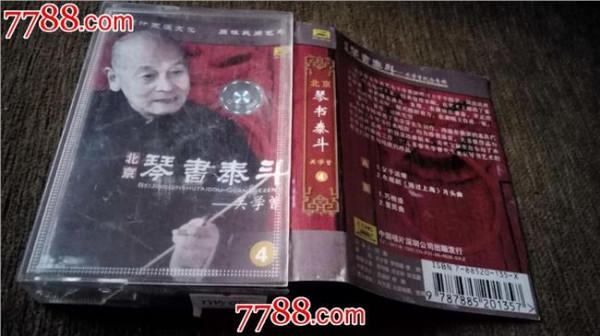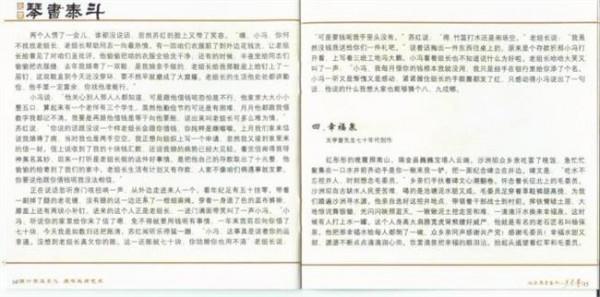关学曾采访 琴书泰斗关学曾(名人专访)
这就是唱了一辈子“北京琴书”的关学曾。
亲手创“北京琴书”
提起北京琴书,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电影《有话好好说》中的那一段——“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总想要点强……”这段铿锵嘹亮、京味浓郁的琴书,从作词到演唱都是关老一手操办的。那一年关老76岁。
从上世纪30年代初,关老就在天桥演出。日子一长他有了自己的一拨儿书迷。“当时爱听琴书的人很多。还有人专门给我送了匾——用玻璃框做的,上面写着‘琴书泰斗’。我老说,这唱鼓曲就好比是‘平地抠饼’。凭您的本事、您的演唱、您的两片子嘴挣出‘嚼裹儿’来。说实话,那个年代,能抠出什么,您就吃什么。有本事您就有酒有肉,没本事只能喝西北风。”
“我虽没抠出什么酒肉来,总算没饿肚子。可别叫什么泰斗,人家多听我几回书比什么都强。”
新中国成立后,关老又赴朝慰问志愿军,又到各地宣传抗美援朝。这段经历让他大开眼界,见识了不少地方的曲艺形式,尤其是琴书,如山东琴书、徐州琴书、四川琴书、冀州琴书等,数不胜数。所有的琴书都冠有地方色彩,唯独他只有“琴书”两字。
于是,关学曾琢磨上了:“我唱的琴书是北京的土特产。我是北京人,又是用北京话唱的,怎么就不能把我唱的叫北京琴书呢?”回到北京后,关老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琴书更名“北京琴书”。“我和老伙伴吴长宝把唱腔、板式、表演都做了大胆的改革。那年秋天,在前门箭楼上第一次以‘北京琴书’挂牌演出,那心里头乐得哟……”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曲艺界的同行只要一提到“北京琴书”,就会想到“琴书泰斗”关学曾的名字。
字正腔圆话人生
“我这一生,唱过上千个段子,演出近2万场,自己创作并经常演唱的段子就有200多段……”听关老说话就像听精彩的“长书”,虽无唱腔,句句都有点唱大鼓书的韵味,字正腔圆,不高不低,调门掌握得恰到好处。
“话说我年轻时候,地痞、流氓都管我们叫臭唱大鼓的、臭要饭的,刚‘解放’那会儿,政府成立了戏曲界讲习班,在讲习班里第一次听说我们是文艺工作者,我心里这高兴啊,打那以后,谁再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再不说自己是唱大鼓的了。”关老笑得脑门上现了纹路。
“想当年,我为赴朝志愿军唱过,为广西前线的战士唱过……这辈子演出,您说什么地方我没有去过,什么人物我没有见过?我就这么跟您说,为老百姓演出我最卖力气,为战士演出我最感动。只有为老百姓、为战士演出时,我才觉乎着我的价值,我演出的意义。
”有一次,演出刚结束,好几位部队首长建议把《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间》再演一遍。关学曾马上答应下来,第二天就演出了这个段子。“等我唱完,全场鸦雀无声,只见战士们个个脸上都是泪水……”关老的小地桌上压着许多发黄的老照片,有些甚至已经分不清时代,但仍可以辨认出战士、孩子、老人……还有关老灿烂的笑。
“说实在的,我在党旗面前举手宣誓的那场面,一辈子也忘不掉。像我这样一个穷小子,一个唱了一辈子大鼓书的老艺人,意义太不平常了。我就觉着非把自个儿的一切交给党才行。所以,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甭管别人怎样,我是关学曾,我就按自己个儿认准的道走。我一直认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关学曾的今天。”关老背过身,哽咽着咳了两声,压了口白开水,清了清嗓子,言语一字一顿,铿锵有力。
老鼓琴曲唱不断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退休后的关老担任起北京市曲艺协会主席,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养接班人上,连续组织“曲艺进校园”,还在家里开办了“北京琴书讲习班”。“每礼拜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我在家里教北京琴书。谁愿意学都可以来,不但不收费,中午还管一顿炸酱面。”
这话一出,本来就不宽敞的家,每周六挤满了前来拜师学艺的人。全国各地不断有人给关老写信,求学求艺。河北有个叫王树才的年轻人,打遍了电话才找到关老。“这小子先天条件很好,我对他抱很高期望。”现在,王树才已经被北京戏曲学校破格录取。看着老鼓琴曲有了传人,关老高兴得了不得。
如今年事虽高,关老仍在为弘扬北京的传统文化鼓与呼。上世纪60年代始天桥茶社销声匿迹,时隔40年后,天桥茶社重张。其间,关老倾心尽力,亲笔书写“天桥曲艺茶社”牌匾并为之揭幕,还担起茶社的名誉主席。“只要有人喜欢,曲艺就不会灭绝。
如今,人们的文化需求呈多元化,喜欢歌啊、舞啊,都很正常。但我始终认为,身为中国人,首先要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历史,了解传统的艺术。你说什么能代表咱北京的市民文化,不就是曲艺嘛。”关老说。
这不,他的学生王树才又为他铺上纸墨,为宣南文化博物馆题字。关老一气呵成:“中华文化几千年,民族遗产代代传,华夏儿女共携手,走向世界永流传。”笔墨稍停,两滴硕大的泪珠润湿了未干的字迹,“还真是不争气,字没写几个,我倒是先流起墨来了。”关老赶紧抹着眼角,他望着手中撇到一边的笔头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