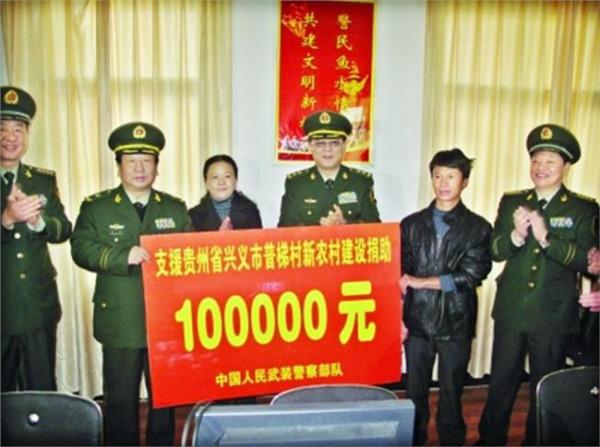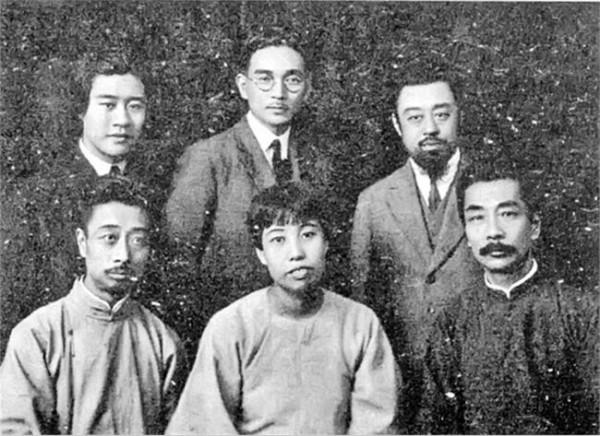查建英弄潮儿 查建英《弄潮儿》出中文版 暗示政改复杂
查建英《弄潮儿》出中文版 暗示政改复杂
作家访谈
扎西多是査建英的笔名,“我不是姓査嘛,这笔名就是我和我妈开玩笑时随口起的”,査建英对南都记者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她为颇有影响的香港杂志《九十年代》写专栏,就开始用了这个笔名,一直延续到后来在《读书》、《万象》上发表杂文。这个笔名还引起了一个误会,当时沈昌文是《读书》的主编,形容她的作品像“麻婆豆腐”,作家舒芜还曾问沈昌文,“扎西多这藏族小伙子是谁啊,文笔还不错!”
同时,査建英在国外用“JianyingZha”的名字发表英文作品,在国内用“扎西多”发,老有人问她,怎么中文作品和英文作品差别那么大?“李欧梵也曾说,你在英文里和中文里像两个人!我自己也觉得挺人格分裂的,后来就干脆不用了。”
查建英的写作起步于大学时代,但让她为更多人熟知的却是出版于2006年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她选取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崔健、林旭东、田壮壮,对话并记录。
新作《弄潮儿》在2014年1月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前的英文版已经在2011年面世。追溯起来,早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之前,査建英就向美国古根汉姆的非虚构写作基金报了《弄潮儿》的选题,而后回国,完成了《八十年代访谈录》之后,査建英又继续了《弄潮儿》的写作。
与2006年红极一时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相似的是,査建英都选择了她认识和熟悉的对象进行写作,此前不认识的对象,甚至也因为写作《弄潮儿》而成为好朋友。不同的是,《八十年代访谈录》是一对一的采访,而《弄潮儿》则借助个人的故事,展现了更加复杂的中国。
书中的部分章节比如《国家的敌人》、《国家的仆人》、《龟的故事》因为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也被热心的读者翻译后贴在网上,甚至有朋友告诉査建英,他曾读到过十个以上不同版本的《国家的敌人》。
“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是唐诗,“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是宋词,但对于《弄潮儿》这一书名的释义,生活在纽约的査建英选择了《尤利乌斯·凯撒》:“人生总有涨潮时”。
“没人可以改变涨起的潮水,但是这又取决于你如何弄潮,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定数并影响其他人。我所有的朋友以及书中提及的每一个人物都在全神贯注直面应对着‘崛起的中国’,这据对是他们人生戏剧中最为重要的一幕。”査建英说。
《弄潮儿》全书上篇是“知识人”,写张维迎、刘东等人的《北大!北大!》,写王蒙的《国家的公仆》,写査建国的《国家的敌人》;下篇是“企业家”,包括写潘石屹、张欣的《龟的故事》,写张大中的《一位好大亨》,写孙立哲的《赤脚资本家》。査建英试图用这些人物的故事和命运来反映中国政治、商业、文化的生态及其变迁。
査建英说,这首先是一部写给英文读者的书,她是“以聚焦中国人去诠释中国”。查建英的写作,也由这本书呈现出较完整的风貌。
北大中文系文学新星
从小说起步的写作之旅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作家出版社“文学新星丛书”推出,入选这套书的首要条件就是,这是作家的第一本书,而且只能是小说。阿城的《棋王》、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就是丛书第一辑推出的,残雪、格非、余华也都是通过这套书而逐渐被大众熟知。编辑杨葵曾写过,当时作家社编辑石湾找到莫言,说要出书,“莫言万分惊讶,说我都能出书了么?”
査建英的《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在1991年3月入选这套丛书,不过她告诉记者,她和作家社的编辑没有太多的交流,这个时候“跟八十年代的气氛差别非常大”,她记住的更多的是之前自己作品单篇发表的杂志和编辑,比如《人民文学》和朱伟,《北京文学》和李陀,《文汇月刊》和肖关鸿,《小说界》和郏宗培,既是作者和编辑的关系,又像朋友。
“新星文学丛书”在2009年由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改名为《回眸—从文学新星丛书看一个文学时代(上下)》,但时隔境迁,这套书在豆瓣网上“少于10人评价”,査建英也压根不知道重出这回事。
南都:刚上北大那会,早期北大校园刊物《未名湖》和《早晨》的编辑团队你都参与其中?
査建英:1978年我们入学,就张罗着办刊物。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最初的流星》就是发表在第四期《早晨》上的,陈建功是当时的主编,还说这是这一期《早晨》的重头稿,结果那是《早晨》最后一期,之后停刊了。那时候所有人都是文学发烧友,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班陈建功,一天到晚谈小说构思。现在没有这样的氛围了,聚会都是吃吃喝喝,有很多作家可能也就是酒肉朋友了吧。
后来,黄子平、王小平和我几个人就去办北大的五四文学社的刊物,叫《未名湖》。我们当时封面是请徐冰设计的,徐冰设计了几个有套色的,但按照我们当时那个趣味,就选了一个全部是黑色的,除了“未名湖”几个字是红色的,当时大家就开玩笑说是“黑皮未名湖”,用的稿子有史铁生、北岛等人写的,还请北岛来大学交流。
这些都跟校方没关系。后来忘了是谁打小报告,校方说有倾向问题,资产阶级自由化,办了一期我们就撤了。紧接着就是《这一代》,十几所大学联合办的学生刊物,印了一期也被封杀了。那时候所谓的“解冻”是非常脆弱的。
南都:办刊经费从哪里来?
査建英:其实没有多少经费。像陈建功,还捐了他一个月的工资,他是从煤矿干了八年才来上学的。当然刊物也出售,价钱不高但是成本也很低啊,最后还能把成本给收回来。刊物也很简陋啊,一看都像那种废报纸钉在一起的感觉。
后来2009年我们班长岑献青还组织我们出了一本书,就叫《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我写了一篇回忆梁左的文章,没写校刊的事儿。
南都:校园刊物这也算是你文学上的起点了吧?
査建英:是。写作是孤独者的事业,但在那样的年代你一点不会孤独,集体发烧,热闹极了。热爱文学的年轻人实在太多了,而我们又在北大中文系。那时文学青年也很单纯,没人想到赚钱,也根本没有发行渠道,我们就在三角地那儿吆喝,学校和学校之间互相邮寄、串通,非常纯粹的。当然回头看那些作品,其中最好的东西是比“伤痕文学”好一些,但还是有时代烙印。
南都:对《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丛林下的冰河》,你之前评价“不说一无可取,不忍卒读的感觉肯定会有”,好像没有仔细梳理过?
査建英:这都二十年了嘛,老谈过去意思不大。我当然不悔少作,那是青年时期的作品,应该说有几篇小说写得也还不错啦,但我很少去看。去年华中师范大学的江少川教授联系到我,说他在做一本“新移民文学访谈录”,已经采访了哈金、严歌苓等20多位海外作家,于是借此机会去年我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回顾了一下当年写小说的一些感受、情况。
直到现在,有时候还会遇到陌生读者跟我说,当年他们如何如何喜欢《丛林下的冰河》。但其实,我被转载最多的中篇小说是《到美国去,到美国去》。讲述一个外省女知青到了美国,如何为了物质上的成功而艰苦奋斗的故事。那女主角伍珍与我的生活轨迹、追求、情感方式都很不同,所以我可以安全地隐藏在一个虚构的男性叙述者背后,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去讲那个故事。
1988年我住在南京,我放弃了写英文的博士论文,用来写小说,《丛林下的冰河》的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总体上是与我个人生活经历最接近的一篇创作,当时我去美国生活了五年多,回国一年多,有很强的冲动想回顾、整理一下自己整个出国的心路历程,于是,那些有关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之间互相迷恋又互相误会,有关不同种族间的疑虑、隔阂与相通,有关人在成长、走向成熟当中如何安放青春理想,有关他乡与故乡……很自然就全都涌出来、以不同方式进到小说里了。
南都:对当时像阿城、莫言他们这些文学新星们,你还有哪些印象?
査建英: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的时候,阿城来纽约访问,就认识了。当时觉得他是个神人,杂学特厉害,博闻强记,脑筋、口才都是超一流,和他谈话,那真是特殊的享受。我至今没遇见过比他更会讲故事的人。莫言只是饭局上见过,余华早就认识,但来往不多。最熟的是刘索拉。有一些当年不熟但后来认识的,像迟子建。我不是那种喜欢老跟其他作家一块儿切磋文学的。除非你上创作班,我想作家最不愿意坐一块儿谈的就是怎么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