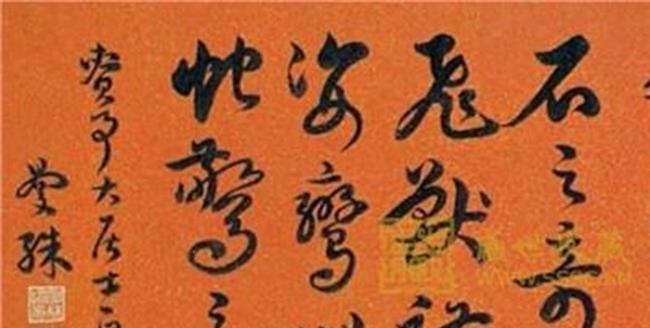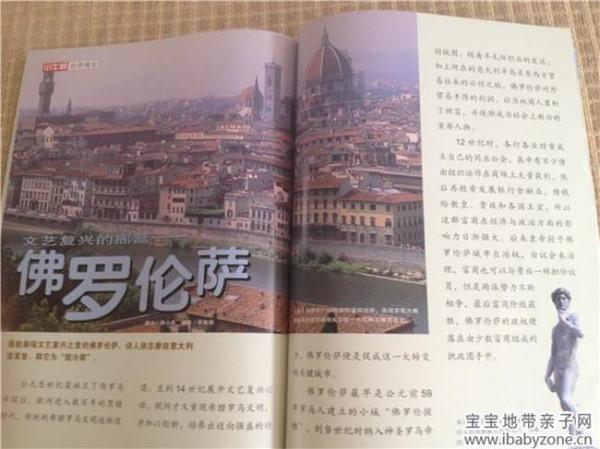【苏曼殊经典语录】一切有情 都无挂碍的民国情僧 — 苏曼殊
陈独秀、章士钊、苏曼殊三人留学日本时,合租一屋居住,有一次竟断了炊,他们便让苏曼殊拿几件衣服去当铺典当,买点吃的东西回来。苏曼殊半夜才回去,带回来却不是可吃的东西而是书。他振振有词地说:“这本书我遍寻不得,今天在夜市翻着了。

”陈独秀和章士钊骂了几声“死和尚”“疯和尚”,只好空着肚子上床睡觉去。又有一次,孙中山让宋教仁接济苏曼殊200大洋。生活困苦的苏曼殊接钱后狂喜,遂广发请柬,大宴宾朋,孙、宋二人亦在被请之列。接到帖后,孙、宋两人对视,哭笑不得。

在长沙任教职时,苏曼殊攒了不少钱,回到上海后,便常常出入“江南春”、“海国春”、“一家春”等名餐馆,叫局吃花酒。每次吃饭都会叫来很多人,陈独秀、包天笑等人都被他请过。客人到齐了即开宴,宴毕即散,不通姓名,亦不言谢。

民国初年,他跟沪军都督陈其美交情匪浅,陈其美常去看望他。去时通常见到高朋满座,美女如云,苏曼殊与歌伎诗词唱和,好是快乐写意,陈其美也艳羡不已。苏曼殊不交权贵,对陈也不怎么亲昵,但陈其美走时,总是赠金若干。苏曼殊花钱如流水,海滩高等堂子都知道有个和尚出手阔绰。他对歌伎彬彬有礼。后来他35岁病死,设灵堂的时候,许多歌伎头戴百花前来吊唁,个个颜色悲戚。
苏曼殊的画和他的诗一样,山明水秀,格调不凡,意境深邃,超然有遗世独立之慨,很有胸怀和意境。有人曾经说,苏曼殊画画时,总是身着禅绸,有妙龄女子侍立在旁,研墨铺纸;若画三月桃花,则蘸取女子唇上的胭脂,其画绮艳逼人。苏曼殊曾经画了十几位英国国王的小像,出神入化。一个美国朋友见了,爱不释手,苏曼殊就全部赠与他。美国人在一个展览会上展出,极为轰动,竞相争买,最后一个英国人以五万美元成交。
苏曼殊不轻易作画,因此身后作品不多。他在南京陆军学堂任教时,结识了革命家赵声,两人志趣相投,常在一起饮酒赋诗,纵马高歌,钟山附近的人常被他们豪迈的气概所吸引。赵声曾经向苏曼殊求画,那时苏曼殊正准备要去日本,没有马上为其作画。
后来他为赵声画了一幅《饮马荒城图》,并题诗一首:“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但赵声为革命四处奔走,居无定所,苏曼殊一直无法交给赵声。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赵声悲愤而死,葬于香港。苏曼殊获悉后,极为悲痛,托友人将此画带到赵声墓前焚化,以示悼念。从此以后,他不再作画,以谢死友。
苏曼殊,就像一个俗世中的贾宝玉。一生为情所困。
20岁时,苏曼殊为了逃避爱情,去泰国曼谷研习梵文,途中却在斯里兰卡讲经时,对华裔女子佩珊一见钟情。他自感六根不净,愧对佛祖,悄然回国。回国后在南京陆军学堂教书,随即又与秦淮河歌伎金凤相爱了。两人交往甚密,情深意笃。
但苏曼殊不愿意结婚,这让金凤感到绝望。她曾拿出一块素绢向苏曼殊索画,画还没有完成,她就伤心地离开了他。之后再回上海,他就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稀里哗啦爱了更多的女子。从生性婉慧的花雪南,到亭亭玉立桐花馆,再到行箧中有她多幅照片,时常默默欣赏的素贞。他喜欢歌伎,与他有交往的歌伎,有名有姓的就有28人之多,风流花吹雪,片片不沾身。
在他的一份残账中发现,酷爱读书的苏曼殊花在买书上的钱只有500多元,而同一时期用在青楼舞馆的钱多达1800元。有人断定他心性风流、玩世不恭。但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有他的方式,也或多或少都会被人误解。苏曼殊不是柳永,也不是唐寅。他对爱情有自己的特别理解。他曾对花雪南说:“我不欲图肉体之快乐,而伤精神之爱也。故如是,愿卿与我共守之。”
1908年,苏曼殊东渡日本探母,遇调筝艺伎百助枫子。百助姿容天成,矜持端庄,仿若一株空谷的幽兰,清高绝世。其弹奏的古筝曲悠扬悲戚,触动苏曼殊满腹愁肠。两人引为知音,互相爱慕。苏曼殊暧昧与游离,冰雪聪明的百助看在眼里,她请苏曼殊为她做一幅画以怀念。
苏曼殊挥毫作画时,忍不住热泪横流,他恨自己的无情,也恨自己的多情。对世间美好女子,他一旦遇到身陷情网。情到深处,情欲奔流,利如掣电,却必须克制。但当女子以身相许,他又忍痛拔掉情欲的肉中刺——“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他把自己裹进一件坚硬厚重如乌龟壳的袈裟里,独自去痛苦纠结。世间多少爱情,基于礼法或者现实,都是如此吧?“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苏曼殊的那袭袈裟中,染了太多的胭脂和泪痕。他仿若受到了爱的诅咒,枉爱了那么多人,最后都如他的诗句所言: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
也许民国风流才子一样的放浪形骸,只是苏曼殊的形式。
有一次,章太炎和他讨论佛学,说:“世间确有净土,但是净土在哪呢,我觉得就在我心中,曼殊你觉得怎样?”苏曼殊回答:“先生所言都是佛门大旨,但恕小家直言,这等言论算然高妙,只是小衲听起来,只能入耳,不能入心。”
佛界也许只是他心灵的避难所。在佛门的庇佑下,缓解外界的压力与内心的疼痛。他的思想是超前的,他是觉醒了的知识分子,追求人格的独立与个性的自由。但是污浊腐败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却又每每使他不仅难以独善其身,而且还与社会格格不入。思想超前的人,生错了时代,必定是无比痛苦的。
他一次又一次跪拜佛门,祈求解脱,但佛门亦不能解开他心中之郁结。于是他索性狂放不羁、愤世嫉俗,看不惯所有的一切,我行我素,焚书毁经,喝酒食肉,就如同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流连烟花,狂歌走马,就像禅门的“竹林七贤”,想要为自己的俗世生活寻找佛法上的安慰。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
一件袈裟,终是外物。如果把他看成一个文人,而不是佛门弟子,这一切就自然了。人生无非一个过程,他在35岁的生命里,极尽所能地创造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实在罕见。红尘俗世,不论悲喜,都只是体验,无论爱否,都只有记忆。
苏曼殊的遗笔就一句:“一切有情,都无挂碍。”有情而无挂碍,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