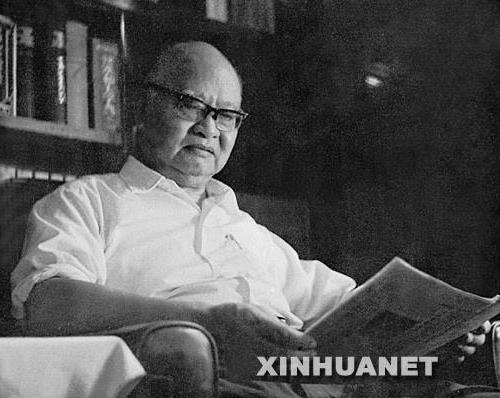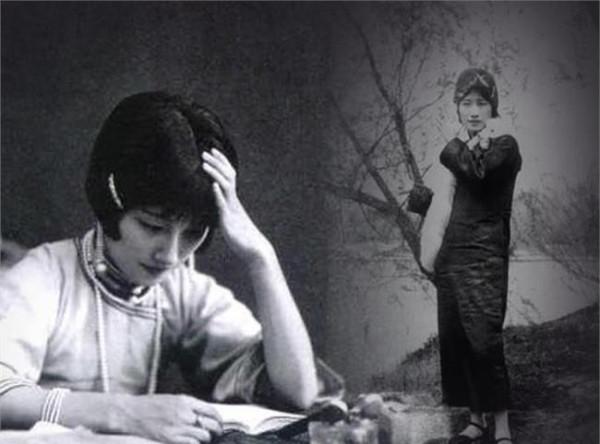【杏花雨小说】刘庆邦短篇小说《杏花雨》
这年的立春和春节没有合上拍,立春立得早,春节来得晚,春天早就化好了妆,节日的锣鼓还没敲起来。这样也有好处,等春节终于闪亮登场时,天气已经不太冷。往年过春节,天也寒,地也冻,早上锅里碗里都结有冰碴子。这年过春节,云也开,河也开,处处暖意融融。

院子里有棵老杏树,安子君带女儿从北京回老家过春节,一进院子就把杏树枝头的花苞苞看到了。杏树哪里都不去,无论她走到哪里,杏树都一直站在老地方等她。只要她回到老家,杏树总是一如既往地欢迎她。杏树所举的虽说不是盛开的鲜花,但满树颗粒饱满的花苞苞也足以让她心生欢喜。

她走到树下,仰脸把数不清的花苞苞欣赏了一下,见每粒花苞都毛茸茸的,花苞的顶端都露出了一点胭脂色。莫道杏花无动静,胭脂一点报消息。照这样的势态来看,说不定在过节期间,或一场春雨后,杏花就会嫣然开放。

果然,过罢春节,当安子君携女儿再次辞别父母离家北上时,杏花已经开了一朵,两朵,三朵。她一步三回头,对杏花有些不舍。春雨细如愁,她没有把雨伞撑开。母亲让她把雨伞打起来,她摇头,说不用,任细雨落在她的头发上,落在她的衣襟上。

在行进的列车上,安子君收到了董云声发给她的一条短信:子君,我爸去世了!安子君看了短信,像是把董云声爸爸的样子简短回忆了一下,没有显得太吃惊,也没有给董云声回短信。车窗外的小雨还在下,遍地刚返青的麦苗一片油绿。停了一会儿,董云声又给安子君发来一条短信:我再也没有爸爸了,我心里好难过,我该怎么办呢?子君,你安慰安慰我吧!
人死如流水,一去不复回,安子君不知怎样安慰董云声才好。她由董云声的爸爸联想到自己的父亲,反正她父亲的身体挺好的。父亲树要自己栽,鱼要自己逮,一个人掀翻一头肥猪还不成问题。除夕那天,父亲还亲自下灶,为她烧了一道她最爱吃的臭鳜鱼。
董云声死了至亲的人,老不搭理人家,似乎也不合情理。安子君想了想,还是给董云声回了一条短信。在信中,她除了按常规礼节说了节哀之类的话,还对董云声说:谁的孝谁戴,求人不如求己。遇到这样谁终究都会遇到的事,别人都不能代替你,也无法安慰你,只能是你自己安慰自己。
安子君和女儿在北京租住的是一间高层居民楼的地下室,她们和众多住在地下空间的人们一起,被说成是“地下一族”。同是一幢楼,人家进楼是往高处走,她和女儿进楼是往低处走。离地下室出口不远处,建有一个小花坛。在花坛一角,也有一棵杏树。
杏树不大起眼,住在高处的人眼高,也许会对杏树忽略不计。而安子君所处的位置低一些,杏树在她眼里还是高的,她每次从地下室里走出来,都愿意仰脸把杏树看一看。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她小时候在老家院子里看杏花看惯了,心里有眼里就有,到哪里只要看到杏树,心里一明,就格外留意。
她老家在长江边,那里的春暖早,杏花自然也开得早。北京在长城边,杏花就开得迟一些,大约会比老家的杏花迟开六七天吧。安子君注意到了,北京的杏树枝头也在喷码儿。
喷码儿不是北京的说法儿,是她老家的说法儿。好一个喷字,无声胜有声。等码儿喷得差不多,接下来就该喷花儿了。如果以杏花开作为春天的标志的话,她在老家过了一个春天,到北京可以再过一个春天。
晚上,董云声给安子君打来了电话,希望安子君能跟他一块儿回一趟老家,跟他爸爸作最后的告别,为他爸爸送葬。安子君给董云声回过短信后,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董云声的爸爸已经远行。听董云声的意思,事情还在那里摆着,还有一些后事需要办理。
安子君一听董云声的电话就有些不悦,说话就有些急,她说:那不可能,我算老几?她没说董云声算老几,眼睛向内,说自己算老几。安子君这样说,因为一年前他们已经解除了婚约,不再是夫妻关系。那,他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呢?按安子君的说法,她和董云声现在的关系也就是路人之间的关系,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谁都不必再搭理谁。试想想,如果跟一个路人去参加路人爸爸的葬礼,那成何道理?!
你是我女儿董泉的妈妈呀,这一点你不能不承认吧!董云声说。
安子君不想承认也不行,她单方面生不出女儿,女儿的确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这是永远都不可能改变的事实。还有,为了保护女儿的心灵不受伤害,他们离婚的事儿没让女儿知道,一直对女儿瞒得严严实实。董云声还担负着抚养女儿的责任,每个月都会按时打到安子君银行卡上一千元钱。
女儿董泉呢,也会经常说到爸爸。安子君在有些事情上一不高兴,董泉就会说,她想爸爸了,她要去银川找爸爸。可安子君对董云声说:一码儿归一码儿,这是两码儿事。你不要把两码儿事混为一谈。
董云声说: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的,码子与码子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不可能分那么清。有时候要一分为二,必要的时候还要合二为一。你实在不愿意跟我一块儿回去也可以,我不勉强你。我带董泉一个人回去就行了,让董泉见她爷爷最后一面。
女儿可是安子君的心尖子,像是她生命的一部分,从女儿出生,到如今女儿长到五岁多,她从没有让女儿离开过自己。若是让董云声把女儿带走,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参加一场悲哀的活动,那是不可想象的。安子君对董云声说:亏你想得出来,我怎么可能会让你把我女儿带走呢!你要弄清楚,董泉的法定监护人是我,是安子君,而不是别的任何人。
这我都知道,我非常尊重你,也非常感谢你,可是……
你不要跟我说可是,可是可不是,现在跟我说可是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后面构不成任何转折。
董泉可能从妈妈的手机里听见了爸爸的声音,她看着手机问:是爸爸打来的电话吗?还没等妈妈回答,她就大声喊:爸爸爸爸!
董云声在手机里听到了董泉的声音,他说:我听见董泉喊我了,让董泉跟我说句话可以吗?
安子君赶紧把手机捂在耳朵上,免得女儿听见董云声说的话。她没让董云声跟女儿说话,却对女儿说:好好在屋里看书,不要出去!地下室信号不太好,我出去接个电话就回来。说罢,带上门就出去了。她一边沿着长长的地下通道往上走,一边继续和董云声说话:咱事先达成的不是有协议嘛,要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不干预对方对今后道路的选择,互不干扰对方的生活。你这是干什么?要撕毁协议吗?
实在对不起,这不是特殊情况嘛!死去的可是我亲爸爸呀,我想我此时的心情你一定能够理解。谁没有爸爸妈妈呢!
在地下室的出口停下来,安子君听出董云声的声音不大对劲,像是双重的声音,既像云中的声音,又像耳边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呢?带着疑问她不由地往小花坛那边看了一眼,见花坛一角的杏树下立着一个人,也在打电话。那个人的身影有些熟悉,安子君再一看,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董云声。
自从和董云声分手后,董云声只身一人离开北京,去了银川,她和董云声已经一年多没见面了。不用说,董云声得到他爸爸去世的消息后,已匆匆从银川赶到了北京。
董云声没敢贸然走进他们共同住过的地下室的小屋,就先用电话跟她联系。董云声身旁立着一只大号的拉杆箱,拉杆箱的拉杆没有合进去,两根金属拉杆还是拉出的状态。董云声就那么一手握着拉杆上面的手把,一手在给她通电话。
这事情意外吗?好像一点儿都不意外。在这个充满意外的时代,什么意外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而意外多了,什么意外都不算意外,都变得很普通。好比移动电话的普遍使用,使人与人之间变得很近,又很远。说很近,是说两个人哪怕相距千里万里,电话一打,就互相听到了对方的声音。
说很远呢,是说两个人哪怕近在眼前,电话信号也要先传到卫星上,在无垠的天空中绕一个很大的弯子,再反射回来,才能送进对方的耳朵。董云声和安子君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
几乎在安子君看见董云声的同时,董云声也看见了安子君,他们都把手机从耳边放了下来。居民小区的路灯不是很亮,他们两个人又都是在暗影里,身影有些朦胧。春天的潮气从地下往上涌,地面显得湿乎乎的。一位提前穿了短裙的摩登女士,边快走边对着手机大声嚷:休想,休想,你就死了你那颗狼心吧,我早就把你看透了!
安子君和董云声没有往一块儿走。他们刚才还在电话里隔空交涉,这会儿竟突然间无话可说。不说难,说亦难,是两难。不走难,走亦难,还是两难。
两难复两难之际,若不是董泉等妈妈等不及,从地下室里走了出来,说不定安子君会转身走进地下室,把小屋的门对董云声关上。董泉从地下室里一走出来,局面顿时不大一样。董泉看见了爸爸,欣喜异常,叫着爸爸爸爸,蝴蝶一样张着双臂,跑着向爸爸扑去。
董云声一下子把董泉抱了起来,说我闺女又长高了,爸爸好想你呀!
我也好想你,我都想死你了,你怎么老也不回来呢!董泉像是怕失去爸爸似的,把爸爸的脖子搂得紧紧的。董泉又把爸爸的脖子松开了,两手捧着爸爸的脸,在爸爸腮帮子上亲了一下又一下。
安子君哎呀了一声,说行了,行了,我说了不让你出来,谁让你出来的!你这孩子,就是不听话。
孩子的作用是强大的,孩子总是父母之间的桥梁、纽带和黏合剂。孩子一出来,他们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孩子身上去了。既然离婚的事一直瞒着董泉,他们就得做出还是夫妻的样子,把戏接着演下去。如果说他们曾经的夫妻戏是纪实版,那么他们目前的夫妻戏就是虚构版,演得有些貌合神离。
虚构的东西需另起炉灶,比纪实的东西要来得艰难。好在他们两个都不愿意当主角,不约而同地把主角的位置让给了董泉,跑龙套似的一切围绕着董泉转。刚来到地下室的小屋,董云声就把拉杆箱打开了,一样一样往外给董泉掏礼物。那些礼物有裙子,有玩具,有画书,还有食品,都是董泉所喜欢的。每得到一样礼物,董泉都高兴得近乎欢呼。
不管如何,董云声对董泉还算不错,让安子君无可挑剔。不过,安子君可高兴不起来,她看得有些眼冷。
不要以为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小孩子有时是敏感的。董泉问:妈妈,你高兴吗?
只要你高兴,妈妈就高兴。你说谢谢爸爸了吗?
董泉说:谢谢爸爸!
董云声说:自家的闺女,不用谢。
董泉问爸爸:你给妈妈买礼物了吗?
还没等董云声回答,安子君先答:妈妈什么都不要,妈妈只要你。有了你,妈妈什么都有了。
爸爸,你这次回来,是带我去银川吗?
不是,爸爸这次是带你回咱们的老家。
是长城外古道边的老家吗?
我闺女记性真好,爸爸只跟你说过一遍,你就记住了。
我还会唱长城外古道边的歌呢!
董云声没让董泉把歌唱出来,他说:我这次带你回老家,是因为你爷爷死了。
我爷爷是谁?在董泉还不会走路的时候,董云声和安子君曾抱着董泉回过一趟董云声的老家,董泉对老家的爷爷奶奶都没有留下什么记忆。从那以后,董云声再也没带董泉回过老家。
你看我闺女,连自己的爷爷都不知道是谁。你爷爷就是我爸爸呀!我爸爸死了,是昨天夜里死的。
我爸爸没死,我不让爸爸死。
你爸爸也会死的,只是暂时还没有死。董云声说着,看了一眼正在看电视的安子君,见安子君也在用眼角瞥他。安子君拧着眉头,目光有些严厉,意思是说,什么死呀活的,孩子还小,你少跟孩子说这个。
有些细节是可以想象的,而有些细节想象得太细也不好。当晚,不知董云声对安子君说了什么样的软话,做了什么样的举动,给了什么样的许诺,反正安子君松了口,答应第二天一早,就带着董泉,随董云声到董云声的老家去奔丧。
也许他们的离婚是以协商的方式进行的,彼此并没有造成很深的伤害和裂痕,对有些事情还留有回旋的余地。还有一个原因不能不说,那就是,他们离婚的事不但没对董泉说,也没对双方的父母说。结婚,由他们自己承担。离婚,也是由他们自己承担。
不管是穿鞋还是脱鞋,都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没必要让家里人为他们多操心。也就是说,在安子君父母心目中,董云声还是他们的女婿。在董云声父母的心目中呢,安子君还是他们的儿媳妇。如今公爹去世了,当儿媳妇的倘若不露面,大面上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
董云声的老家不像安子君的老家,安子君的老家在农村,董云声的老家不在农村。要说董云声的老家在城市,恐怕也有些勉强,因为董云声的老家在山窝里的一个矿区。矿区周围除了连绵的群山,就是众多的农村。矿区好比是外来的城里人插进农村的一只脚,一抬脚就到了农村,不抬脚也被农村包围着。
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土地长什么庄稼。煤矿既然开在了这个山窝窝,入山随俗,其婚丧嫁娶的文化和礼仪就难免会染上当地的色彩。董云声爸爸妈妈所住的两间平房是早些年自建的,与一大片低矮的房子连在一起,构成所谓棚户区。
董云声他们刚走进棚户区的入口,随着一声高喊:老三一家回来了,起乐!唢呐、笙管便吹奏起来。吹奏者吹奏的曲调一点儿都不复杂,高上来,低下去;低下去,又高上来,跟人类的哭声差不多。
吹奏者吹出的音响一点儿都不华丽,朴素得甚至有些沙哑。但正是这样的音响,直入肺腑,直抒胸臆,有着催人悲痛的效果。董云声的眼圈开始发红,安子君的眼里也有了湿意。
棚户区的夹道内白影幢幢,董云声的哥哥、嫂子、姐姐、妹妹等迎上来,不由分说,就用孝布把董云声、安子君和董泉扎裹起来。顷刻间,他们被穿上了孝服,戴上了孝帽,扎上了孝带,几乎都变成了雪人。
安子君哪里感受过这样的气氛,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她有些不大适应,还有那么一点抵触情绪。她的头脑是清醒的,知道自己已经不是董家的儿媳妇。但她得做出还是董家儿媳妇的样子,对董家安排的一切不能拒绝,不能流露出任何别扭的情绪,只能是接受和配合。
爸爸的尸体在屋当门的一张小床上停着,董云声见爸爸的脸色是黑色的,黑得像一块刚从矿井下采出的原煤。爸爸挖了一辈子煤,刚退休就得了尘肺病。煤尘沉淀在爸爸的肺叶子里了,使爸爸的肺似乎也变成了两块煤。爸爸的肺失去了呼吸功能,连被称为严重污染的最糟糕的空气爸爸都呼吸不成了。
以致爸爸连睡觉都无法正常睡,只能坐着睡,或跪着睡。最终,爸爸还是被活活憋死的。董云声叫了一声再也不会答应的爸爸,就跪在床前的地上哭起来。他双膝跪地,双手支地,连头也抵在水泥地上,一边哭一边磕头。
他们这里雨水不是很充沛,但到了夏天,山洪暴发的情况还是有的。雨水在山上越聚越多,就会顺着山沟倾泻而下,形成山洪。山洪在下山过程中,众多支流式的山洪都会积极响应,参加进来。很快,山洪就形成了奔腾咆哮之势,不可遏止。董云声的大哭恰似山洪暴发,呈现的也是不可遏止之势。他浑身哆嗦,失声号啕,泪水奔涌,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悲痛能力和悲痛能量。
董云声自己的耳朵听见了自己的哭声。如果自己的哭声也是一种动力的话,他像是从哭声中获得了新的动力。这种动力推动着他,使他在为苦命的爸爸痛哭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痛哭。董云声在某个沿海城市大学毕业后,选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去北京,一心要在北京找工作,找对象。
他在北京一家公司找到了工作,一个月可以挣三千多块钱。在业余时间,他用撒网的办法在网上找对象,最后网住了美丽的安子君。和安子君成家后,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决心靠自己的奋斗让心爱的子君过上幸福的生活。
他们的打算是,在北京买一套房子,而后再买一辆汽车。为了多挣钱,董云声跳了一次槽,又跳了一次槽。可他每次跳槽的效果都不理想,“槽”里都没有多少薪水可涨。照这样算下来,把二十年的工资攒到一起,都不够买一间房子,更不要说买汽车。
生下女儿董泉后,为了有一个固定的住所,他们不得不在阴暗沉闷的地下室租了一间屋子。这时,随着生活往“低处”走,安子君对他的热情也开始降低。
安子君先说自己瞎了眼,后来就说他徒有其表,上了他的当。有一次,因他嫌安子君买的一样东西太贵了,安子君就跟他翻了脸,提出和他分手。如果安子君提一次两次也就罢了,此后安子君像是把分手的话挂到了嘴边,越提越频繁。董云声也是要面子的人,脸上一挂二挂挂不住,也是一气之下,就答应了安子君的要求。
听一个亲戚说,银川的生意比较好做,董云声就去了银川。他在银川找到的工作是在一家快递公司当快递员,每天骑一辆箱柜式电动三轮车,穿行在大街小巷,给人家送快递。作为一名学经济管理的本科毕业生,当快递员只是他的权宜之计,他的目的是尽快积累一定的资本,办一家自己的快递公司,自己当老板,自己管理公司。
为了多挣钱,他每天早出晚归,跑得马不停蹄。就说今年过春节吧,别的快递员都回家过年了,只有他一个人还在奔忙,连除夕和大年初一都不休息。
为了省钱,他对自己很是苛刻。饿得不行了,他常常是泡一碗方便面充饥。鞋底子磨穿了,他舍不得买新鞋,就到垃圾堆里拣一双人家丢弃的旧鞋穿。爸爸那一辈是不容易,别人哪里知道,到了他这一辈,过得也很不容易,也有道不完的委屈,连老婆孩子都保不住啊!
董云声从没有这样哭过,这一次他是彻底放开了。如果为爸爸而哭只是由外而内,到了为自己而哭,就变成了由内而外。谁都是一样,只有从内心生发,只有为自己而哭,才会哭得这样持久,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爸爸死了,他把自己所有的痛苦都集中在一起,干脆也哭死算了。
董泉被吓坏了,见爸爸跪地大哭,她吓得也哇哇大哭起来。她还没有痛苦的概念,的确是害怕。她以前没见爸爸哭过,爸爸突然间这样大哭,一定是遇到了危险。爸爸的危险就是她的危险,她只能跟爸爸一起面对危险,一起大哭。爸爸哭的是爸爸,她喊着爸爸,爸爸,哭的也是爸爸。
安子君怎么办?来之前,她没打算下跪,没打算哭,要保持自己的形象。按她的设想,她给董云声一点面子,配合董云声走一下过场,也就完了。她万万没有想到,董云声上来就给她来了这一手。以前,董云声在她面前以硬汉子自居,遇事极少掉眼泪。
她看书掉眼泪,看电视剧掉眼泪,董云声还笑话她泪窝子浅,泪水子多。她和董云声办离婚手续的那天,董云声的情绪虽说有些低落,但一滴子眼泪都没掉。看来董云声并不是不会哭,也并不是不会掉眼泪,他一哭竟哭得这般霹雷闪电,一流泪竟流得如此泪水滂沱。
安子君见不得别人哭,见董云声哭得这样痛心,她的眼泪呼地就下来了。她特别听不得女儿哭,女儿和她是连心的,女儿是吓坏了,她是心疼坏了。她对董泉说:董泉,董泉,不要害怕,妈妈在这里!这样劝着女儿,她膝盖一酸,不知不觉就跪了下来。一跪下来,她就加入了与董云声、董泉的合哭。他们的合哭是三重,有男声、女声,还有童声。
董云声的哥嫂和姐妹没有劝他们别哭,哭是孝心的表达,是葬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仪式,哭是必要的。他们已经哭过了,该老三一家子哭一哭了。
安子君与董云声的爸爸只见过短暂的两次面,谈不上有多少感情。她的哭只能从内部挖掘动力,只能为自己而哭。她为自己哭过很多次了,再哭一次也没什么。安子君高中毕业后,就随着一帮北漂漂到了北京,应聘在一家安全生产培训中心工作。
她的主要优势,除了聪慧好学,长相还相当出众。她的一双大眼睛老是水灵灵的,清澈而明亮。培训中心的一位副主任对她颇有好感,就托人给其儿子介绍,希望安子君能成为他的儿媳妇。副主任家的条件当然不错,有大房子,好汽车,存款恐怕也不是小数。
除了副主任的儿子个头稍低一些,说话有些居高,别的无可挑剔。然而,安子君的想法是浪漫的,甚至带有一些艺术性。干吗要别人给她介绍对象呢,网上海阔天空,她要到网上自己谈。
生活上干吗要依靠别人呢,她要靠自己的劳动,开创属于自己的新生活。于是,她操纵长尾巴的鼠标,在网上寻寻觅觅,就寻到了也在网上东张西望的董云声。董云声明鼻亮眼,长腿长身,那叫一个帅气。人说某个香港的歌星长得帅,董云声比那个歌星还要帅三分。
董云声是正儿八经的大学毕业生,不光中国话说得有条有理,外国话也说得一嘟噜一串,让安子君不得不佩服。结婚前,他们双双来到婚纱影楼,光艺术照就照两大本子。翻开每一页,他们的形象无不光彩照人。
他们的婚姻是浪漫了,也艺术了,可在铁的现实面前,浪漫的东西总是易碎的,艺术的东西总是虚拟的,浪漫和艺术都不堪一击。它们既不能代替柴米油盐,更不能代替房子。京华丰富的物质世界让他们炫目,同时也让他们失落。
在经济主导一切的情况下,让他们感到担忧的正是他们的经济命运。琐碎的日常生活没能磨练他们的意志,却对原有的意志有所消磨。渐渐地,安子君有些扛不住了。每次和参加培训班的学员一块儿喝酒,那些学员就对安子君的美发起恭维。
有人问安子君有对象没有,要是没有的话,就给安子君介绍一个。当听说安子君已经有了孩子时,问话的人不愿意相信。更有甚者,当有人知道了安子君找的对象只是一个无根的北漂,直言不讳地替安子君惋惜,说像安子君这样的条件,怎么着也应该找一个北京的富二代呀!
让安子君伤心的事正是发生在这里,让安子君借机为自己痛哭不已的事也是发生在这里。和董云声分手后,有人真的给安子君介绍了一个有北京户口的男人。男人请安子君喝咖啡,看电影,吃西餐,还带安子君到外地旅游,出手就像个有钱人。
可惜男人的有钱没维持多久,就开始张口跟安子君借钱,说是遇到了急事。跟安子君借一次钱不够,过了不几天,再次跟安子君借钱,而且至少要借一万。安子君意识到坏了,她可能是遇到骗子了。她拿不出那么多钱借给人家,人家果然不再搭理她。
这件事情让安子君深受打击,深感委屈。但她把委屈埋在心底,没跟同事说,没跟父母说,当然更不能跟董云声说。委屈也是种子,遇到合适的时机,迟早会发芽儿。安子君的委屈这会儿显然是遇到了时机,不发芽儿则已,一发就是爆发的状态,疯长的状态,一发而不可收。
一些围观的人纷纷对安子君的哭作出评价,认为她的哭是真哭,不是应付。他们说:老三媳妇儿真是有孝心哪,老三两口子真不错啊!
安子君听到了别人对她的评价,像是受到了鼓励和推动,悲上加悲,哭得更深远些。
这场前所未有的哭,使安子君加深了对董云声的理解,也使她对董云声的看法发生了一些转折。董云声不是不会哭,董云声哭起来是很惊人的。董云声有硬汉子的一面,也有柔软的一面。董云声不伤心的时候是坚强,一伤心也很脆弱。总的来说,作为一个男人,董云声的责任更重,压力更大,痛苦也更多,比她活得还不容易。
一场春雨后,当地下室门口的杏花开满一树时,董云声向安子君和董泉发出邀请,请她们母女“五一”放长假时到银川游一游。
安子君明白,董云声表示的是想修好和复婚的意思。安子君没有马上答应,但也没有拒绝,她回信说:到时候再说吧。

![郭宝昌的养母 [转载]《大宅门》编剧导演郭宝昌其人其事](https://pic.bilezu.com/upload/b/25/b25b55da60b4e81b5b0544ff5ba4ee3b_thum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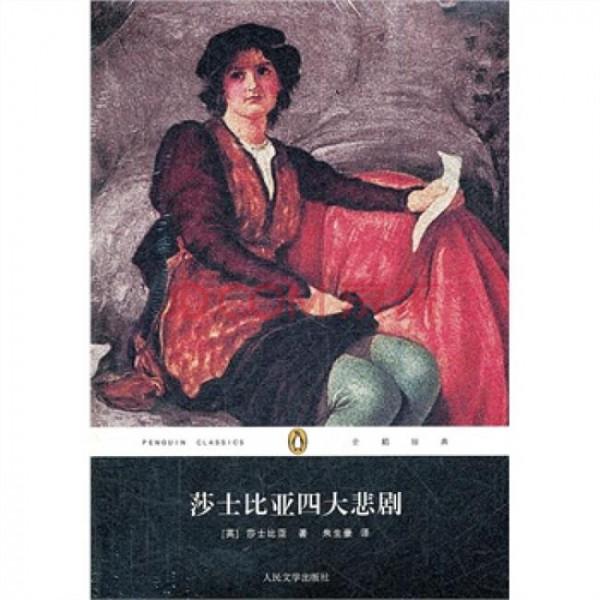
![>《连环画:红楼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扫描版(20册)[pdf]](https://pic.bilezu.com/upload/a/43/a43004ef43b18fe4cda0caeda48a5a60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