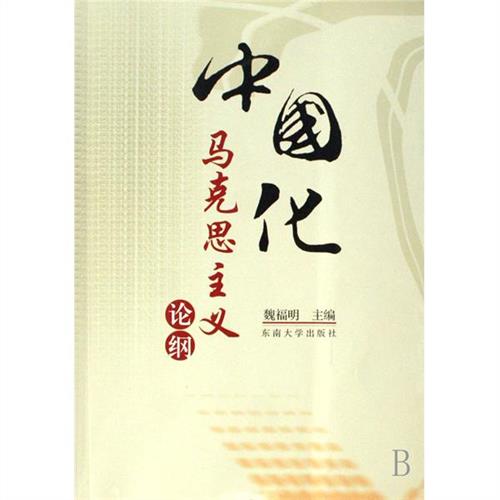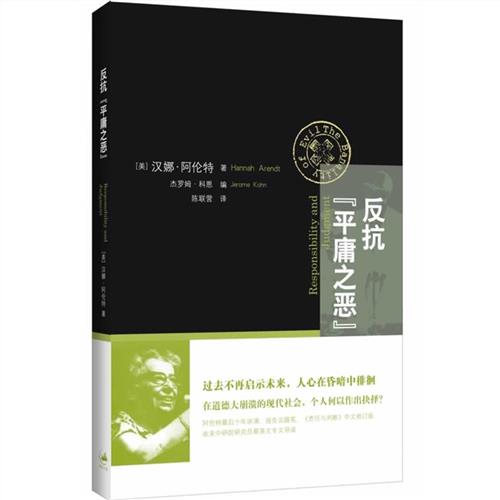【汉娜艾米莉安德森】艾米莉·狄金森日记
今天我看到一棵勇敢的仙人掌,打败了死亡。虽然被冬日的雪所覆盖,但它仍然努力地生长出来,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下。大自然正从冬天的伤口复原,这个春天就是证明。每年她都答应要回来,但今年她却迟到了那么久,几乎快让我们绝望了。现在既然春天来了,我们该可以原谅这个小气的神了。

重生需要我们共同庆祝。虽然我如伯劳鸟一般地歌颂生命,我却从未记下这些时刻。我安安静静地活着,只为了书册,因为没有一个舞台,能让我扮演自己的戏。不过思想本身就是自己的舞台,也定义着自己的存在。记录一个就等于同时记录另一个,就像将开得最美的鲜花夹在书页间一样。所以,让这个日记成为写给自己的信吧,这样就无需回信。
最后一行重复了编号四四一的诗《这是我写给世界的信》,大约写于一八六二年。
这是我写给世界的信
因为它从来不写给我
自然带来简单的讯息
既温柔又崇高的存在
她的讯息是写给那双
我看不见的手
为了她的爱—亲爱的同乡
请温柔地评断、评断我
三月三十日,星期六
我那反抗的心,整天都想远离家务,哀求我跟随心灵行动。维妮昨天自康桥回来,她很担心那些未能完成的事务。今天她很生气,因为我并没有把份内的缝补做好,她还骂我只顾着做白日梦。她并不知道,有四行诗从我心中蹦出来,哀求我要保存它们。
晚餐也延迟了,因为我把烤肉放在火炉上太久,因此爸爸很不高兴。我不知道谁的忿怒让我比较害怕,是维妮的,还是爸爸的。但是为了诗的缘故,我愿意忍受这些。我常常希望自己不用因为家事而浪费时间,但是完全的自由,会让我专注得失去了光彩;我们的黄金时刻,通常都会因为之前的浪费,而更显珍贵。
四月十三日,星期六
这些就是我今天的成果。明天我会隔着篱笆,把它们拿给苏,虽然我心中仍不免有些忐忑不安。苏总是乐于收下我的诗句,并且提出她的意见,纵使我怀疑她与其他人一样,并不明创作对我的意义。以前她还会表现出评论者的热诚,但现在的她,似乎已经忙得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她得忙着当女主人,要将这个身份做的比其他人更好。她的聪明与独特的魅力,让她一直是众人目光的焦点。不过,她仍不断试图藉由社交生活,来填满某些空虚,单纯的家庭生活乐趣显然无法完全满足她。苏的友谊对我十分珍贵,但我和她之间的裂痕却随着时间,不停加深。我们在少女时期的感情,慢慢地松弛了,那时我以为我们永远不会分开,但或许这样的感情,只能存留在我心底。
我永远都会把她当成我的妹妹,但我们却处在阴霆中,那样地不了解彼此。
五月一日,星期三
今天晚上我看着镜子,我生平第一次看见,这张很少吸引我注意力的脸。当然它从未让世界运转。这张脸让我想到麻雀:一只暗棕色的鸟,因为它发亮的羽毛被它的同伴讨厌,却还得在自然的戏里扮演一个角色。我想用文字使人感到惊异,但这个世界却比较喜欢和谐。
我曾经在小时候照过相,那是父亲坚持要我这么做的。从那以后我就不愿再让自己被困在木框里,除非是诗行的框框,人工做的并不能使我满意。我不愿意让父亲不高兴,但我自己就是好肖像,如果他愿意更仔细注视我的话。
艾米莉一生中唯一的一张照片
五月八日,星期三
晚餐在傍晚时就准备好了,而我和白朗宁女士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在她面前,我感受到诗的力量和一个女人的力量。她非常诚实地将她的心还有她的生命转化成诗。诗人是“真正说实话的人”,可是真理却不会受性别所限制。
她的真爱来得很晚,而她的十四行诗可以证明这迟来的快乐的确补偿了先前的贫乏。我曾经羞怯地敲过爱的大门,但是只有诗开门让我进去。我所看过的只是热情的侧影。但热情与创作总是同时来临,那种穿刺精神的感受,同时想象也是诗人的疆域。认识一个就等于认识另一个。
奥罗拉·李没有谈恋爱,直到她变成自己精神的爱侣。男人与女人各有自己的疆界,那些学会自由穿越这种疆界的人真是幸福。自然注定的那种结合轻易来临,对大多数人而言命运是宽厚的。但是一个灵魂有可能进入另一个吗?那么心灵与心灵之间的结合,才是大功告成。
记所述说的那样。
像闪电一样堆积直到结束
接着一点点风化粉碎
所有被造物都隐瞒
这件事—这是诗
或是爱—两者同时到临
我们证明两者却也不知
感受两者并吸收
因为两者都未能活着看见上帝
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三
包沃斯先生写信告诉我们,他会在七月来访,想在安贺斯特凉爽的夏季里避暑。一想到这里,我的心就变得不舒服,呼吸就不太平顺。当身体与心智互相协调时,这个病痛就可以被忘记,就可以忍受这样的绝望。现在心智复原了,身体却还未适应。
我认识山姆,这个我从不敢说出的名字。山姆是我的朋友,因为他是奥斯丁的朋友。但是幻想占据了我的心,让我站不住脚,接着我陷入了难以想象的爱与焦虑。
从我们开始一起喝茶的那个夏天起,我的心便开始欺骗我。那时我们尽情聊天,总觉得时间太少;而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亲密,压迫着我的呼吸、我的理性。我想他也感觉到了,而且他也感觉到无数的狂喜。我知道自己只能透过文字接触他,因为他已经选择了自己的伴侣,这样的关系对他而言是神圣的。所以我只期盼他的了解,让爱变成一个发亮的记号,这样我就满足了。
不过一条延展过剧的绳子必会断裂。我太大胆了!当我试着告诉他我的快乐,想知道他喜不喜欢我或这只是我的想象,我的话失去了控制。它们抓住了我,狂野地在四周跑来跑去。接着我看见他眼里的恐惧。这就像一颗子弹穿过我的心,因为我的心没有方向四处乱窜。我打开自我,将最珍贵的一切展示给他,但他却不觉得有何可贵之处。虽然我们分享过许多心事,我与我的诗却从未能在他的心中久留。
不过我有自己的世界可以说话。所以我用信件来表达自己的爱。我从来不打算寄出去,就让纸页吸收我的痛就好。一颗努力追求却不可得的心灵,让我十分疲乏,我好像听见细微的警告,说爱情不能与智慧共存。这样的选择对我而言太过困难,几乎快将我的心撕裂。这些年的成长带来了平静,也抚平了身体的伤痕。我还没忘记自己的双重目标,但现在单一目标就够我努力的。
这些年少时光,花了我许多心神,但对他而言却微不足道,也未减损我们的友谊。
七月二十三日,星期二
今天我在整理花园时,奈德与克拉拉来访。他们的来访带来欢乐。天色亮得像青铜,而微风也如此清凉。我的小侄子想趁机跨过篱笆。我猜他觉得自己的姑姑是最好的同伴,因为他没有什么朋友。他的妹妹还太小,不能欣赏这个世界,白天时,她的爸妈也没什么时间照顾他们。
当奈德跑到花园去找蜜蜂时,我与克拉拉在谈天,这是我们的习惯也是我们特殊的乐趣。他很幸运有她照顾。她比一般女孩受到更多痛苦,可是她天性里的同情还是超越她的耐心。我看着她的成长茁壮,我有信心她将来一定会过得快快乐乐的,因为她的热情使她的生命更强而有力。
现在她恐惧地想象未来——可是难道上帝的子民不都是这样的吗?能力给了她选择,尽管这世界如此小心眼,但就像许多年轻女性一样,她只看见一条通往快乐的道路。在她二十三岁时,她就觉得自己老了,并害怕自己永远找不着生命的伴侣。因为奥斯丁的家永远不会是她的,所以她想找一间房子属于自己的住处。
我猜想,她一定觉得为什么我不会这么想。或许她没有想到,我曾经有着和每个女孩一样的梦想,直到一个更大的梦想超越它们。接着我就享受到这份自由,写诗跟被爱一样重要。如果现在“妻子”是我的头衔,那我会是诗人吗?“得到家庭却失去灵魂”有什么好处?一个被抓到的鸟就不再歌唱了。
可是克拉拉得倾听自己的灵魂,我建议她耐心点。延迟的梦一旦完成,一定是更美的。
时间很快地过去,一下就一个小时了。奈德与平常一样抗议克拉拉的召唤,但在知道几天后就会回来,他就释怀了。这个野孩子常忘了把东西带回去。今天他把一台木头的玩具车,忘在樱桃树下了。这个小孩知道他的姑姑,不会只还一辆空车的,所以命运告诉我明天得烤姜饼了。
八月三十日,星期五
今天邮局将维妮向波士顿订购的盒子送来了,其中有一件淡绿色的布是给她的。她几乎很难控制喜悦,因为她想到自己将做成的衣服。这样式非常独特,我不知道她可以在哪里穿这样的衣服。明天我们会有一个裁缝来帮忙剪裁;我可以帮她缝。
我自己喜欢白色的。我不必担心样式,而且这个颜色蛮适合我的。我想我很快就不会想穿别的颇色的衣服了。穿白色的衣服,让我觉得自己像是等待诗句的白色纸页。这是胜利的色泽,由那些已经征服的人所穿着。白色的衣服就是简洁,就像最简单的生命形式。
六〇年代以后,艾米莉所穿的一件白袍子,因为她的谨慎,裁缝先把她的衣服跟拉维妮雅·狄金森的合过,两姊妹的体格差不多。
十月一日,星期二
今天我收到希金森先生寄给我的一封信,好像专程为了回答我那些从未出口的问题,他说他很希望能“帮我建立我的艺术,使我能发挥全部的创造力。”他也很重视我们之间的温暖友谊,这同时也是所有努力的基础。
我的老师继续鼓励我前往波士顿,因为在那里我将“发现全世界”,并且寻找精神的活力。他知道我有一些家庭义务必须完成,也知道为何我不愿旅行,但他还是希望能说服我。希金森先生是个见多识广、饱学多闻的人。他很难了解我狭窄的生活圈,也很好奇我的缺乏活动。
但是难道生命得与不停的动作扯上关系吗?难道我得入世才能在其中找到诗的存在?当心智退缩的时候,许多层面被包覆着。思想才是最大的事件,怎么可能不思想而活着呢?有些时候简单的生活反而是最复杂的。我住在父亲的房子里,可是这几堵墙并不能限制我的心。与朋友见面会给我最大的快乐,但分离的代价我却无法承受。
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三
镇上有个女人邀维妮参加一个女子社团,为了改善社会的缘故。现在她脑子里,充满了投票权与改革,可是我相信,维妮很快就会想逃避这些议题的负担,她的热情是可以改变的。
她们的努力为自己带来了荣誉;我不该反对的。可是我向来不与议题妥协。它们的特殊会制约我。谨慎——让我得以唱起更宽广的歌。
时代早已充满了革命。我无需参加她们,因为我有自己的革命要努力。
十月二十七日,星期日
今天真是一个神圣的星期日,快乐早已来到为我们准备这一天。当洛德法官依约来到,我们都聚在起居室喝茶,以社交圈不会允许的方式,交换彼此的乐趣。
不过,今天早晨我们之间有一个超越规范的感受,因为当家人到了教堂,他又来了。从我的窗户看见他走向我们的门口。我听见他敲门,觉得很害怕,因为没有人可以应门。我想躲起来,但我的心给了我温暖的讯息。我不用逃开他,而我也逃不开,一想到他,我的心就无能为力。
开门时我的手在发抖,让他进门时,我的灵魂变得苍白。他说:“我知道其他人都上教堂,但我想到你曾经说你很少去。一股希望使我自镇上来到你家。或许你愿在我走之前,见我一面。我很快就得离开,可是还是很想听听你心里的话。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唐突呢?”
他怎么会知道自己秘密的心愿也会是我的呢?我的心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想法,并将它的形象画在脸上。我欢迎他、,因为我脑中没有别的可能。我们在无底的井里失去现实,让我们彼此的想法互相交融。
我说过这是星期日。他不上教堂,却在早晨为屋顶、黑夜为地砖的大教堂里膜拜。他每天都见到神的作为,可是他不能说出这些事背后神的意旨。他祈求指导,聆听指示。我猜他的心灵比我的更急切。我们在不同的天堂里,遇见自己的上帝,但是今天在起居室里,两者合而为一了。
一小时很快就过了。当他走了之后,我以为那是我的幻觉。他没有告诉我,其他人可能不会了解我们为什么要见面。但这个想法我们都没说出口。这无需告诸天下,我永远不会知道该如何与人分享这种幸福。
十二月十日,星期二
我已度过了我的第三十七个年头。奥斯丁与苏为了庆祝这一天,来我们家喝茶,把小孩留在纽曼家。他们带了另一本狄更斯的书送我。维妮与母亲做了鸡肉沙拉,还有金银相间的蛋糕。家庭和谐是最好的礼物。
倘若狄金森家不在一起了,有人还会记得这一天吗?生命与我的友情比其他人更加坚实。有许多我爱的人,生命早已抛弃了他们。是谁让我有这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从未停止好奇,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一只伯劳鸟?我们会活着就足够令人惊讶了。事件只能为神秘锦上添花,所有的明日都不过是推测。
现在我更常听见日子向终结进行的踏步声了。我不能让它们不带点东西给未来,就自行离去。
四月十二日,星期日
今天早晨花园出现青鸟。雪大多融了,它们忙着找寻地上的生命。终于,我可以更深的呼吸,再听见春天轻轻的脚步声。我绕着花园散步。日光也融化了寒冷,还有我的袍子也够暖。大自然清楚地说话,好像它知道“这就是上主创造的一天。”
人们从教堂回来,讨论强金斯先生的布道,用父亲的话说:“比他平常差多了,”而那嘉乐的女孩受洗了。典礼还有那小女孩让母亲印象深刻,她在晚餐时不断地说这两件事。
父亲什么都没说,只是专心地切着鸡肉,但随着母亲的话越来越多,我无法形容他看着我与维妮的眼光。似乎有那么片刻的悔恨,我们没有子嗣可施行受洗的仪式?我总是想,他要我俩永不离开家。我们没有什么访客,但他也从不反对这点,虽然有时他会直接告诉我们。他完全不了解女人的心,他只懂得自然分配给女性的角色。或许这些年来,看着出嫁的机会越来越远,他担心自己也是葬送机会的元凶之一。
或许我对他的诊释并不公平,将其他人的怀疑归给他。我知道世界是怎么想狄金森家的女儿,因为我们的生活并不遵循着它的规范。维妮与镇民很熟,他们也与维妮很熟。如果社区不认识我,因此做出自己的揣度,我也不在乎。我的生命是个彻底的秘密,连维妮都无法分享。
我保留了许多事,但是说出来却压抑了人的幻想;隐私是有报酬的,基督教我们如何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
我不会有肉体的子嗣,但我有神圣的安慰。上帝给了我一种不同的繁衍方式。我的小孩来自于我的心灵,我永远的子嗣,我灵魂的狂喜。我欢迎这快乐的阵痛,让诗与创造者分离。现在让岁月见证它的成长,让未来为这个选择评断。这些事我会向父亲解释,如果我可以的话,也请他耐心地等待将来的收获。
爱德华·狄金森死于一八七四年。艾米莉因肾脏疾病于一八八六年去世。第一版的艾米莉·狄金森诗集出版于一八九〇年,因此父亲与女儿都未能见证这个成果。
艾米莉·狄金森传记电影《宁静的热情》(2016)剧照,封面图同
以诗歌颂世界的女诗人
洁米·富勒
艾米莉·狄金森在一八八六年与世长辞;而她深锁在盒子里的大量创作诗篇,则是她留给世人的最大厚礼。纵然在她有生之年,她的作品未能获得当时的青睐,然而周遭众人对她的不解与误会,却丝毫无法低损她丰富的创作天分。
艾米莉死后,世人才重新定位她的诗人身份,同时也认清了自己错过些什么。
艾米莉出生于一八三〇年十二月十日,在三个小孩之中排行第二,家庭是马萨诸塞州安贺斯特的一个富有家庭。她的祖父是山谬尔·富勒·狄金森,他是安贺斯特大学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父亲爱德华,与她的哥哥威廉·奥斯丁·狄金森都是相当富有的律师,传承了家庭里开放的传统。艾米莉曾在安贺斯特学院及圣约克山女子学院接受教育,可是她在圣约克只待了两个学期,之后她就回家,终其一生未再离开。
艾米莉相当恋家,所以她甚至不肯离家做短暂的旅行。在一八六四及一八六五年间,她曾在波士顿住了几个月,以便让医生治疗她奇怪的眼疾,而她回来以后就再也不曾离开。从一八六〇年到一八七〇年的十年间,她变得更加孤僻,最后甚至不肯接见大多数访客,也不到隔壁哥哥家去拜访。
到了某个时期,或许是在七〇年代中期,她开始只穿白色的衣服。从她的信件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暗示,里面提到艾米莉在二十岁之前,就开始感受自己诗的创作力,但已经被确定写在一八五八年以前的诗并不算很多。在那个时期,她已经开始用她闻名的形式写诗,也奠定了她成为美国最伟大诗人的地位。
艾米莉·狄金森的人生大都是在她出生的房子里度过的,这栋砖造房屋是由她的祖父在缅恩街上所建造。因为经济上的困难,狄金森家在一八四〇年卖了这栋房子,移到北欢乐街的房子住了十五年,后来爱德华·狄金森在一八五五年又把这栋房子买回来。艾米莉最喜欢这栋房子的地方,就是东边的温室,她在那里种了许.多冬天能开花的植物,并且在窗户边的小书桌上,她写了许多诗。
玛莎·狄金森·比安琪是艾米莉的侄女,也是家族最后的幸存者。她继承了这栋房子,并在一九一五年将它卖给当地的教区牧师。接下来这一年,这栋房子被重新装修,也拆掉了温室。在拆掉这片斑驳的墙壁时,其中的一位工人发现了一本皮面的书。
显然它是被藏在墙壁里或是塞在缝隙间,在这个时候艾米莉已经是安贺斯特家喻户晓的名字了。结果这位木匠不但是个爱诗人,还是她的崇拜者之一,他一打开这本书就发现,原来这是艾米莉的日记。他告诉自己的孙子,他感到一阵“狂乱的颤抖”。
因为这个发现是如此令人震惊,所以他将这本书藏在他的午餐盒里,并在工作结束后把它带回家。在他仔细阅读每一页之后,他告诉自己,他应该将这本日记送交给能够将之公诸于世的人。
但他念了又念,越来越被诗人的魔咒所吸引,竟然开始想象自己是她的密友。于是他说服自己,无需将这本日记送交出去。最后,在良心谴责的问题完全克服之后,他将这本书藏在卧房一个橡木箱子里。接下来的六十四年之间,他常取出阅读,直到他完全将日记内容熟记为止,甚至连他的家人都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
在一九八〇年他以八十九岁的高龄逝世,在此之前他将这个收藏告诉他的孙子(因为他的独子比他还早离开人世),同时也坦承自己阅读的快感,总是掺杂了无休止的罪恶,他要求孙子想办法弥补自己的过失。然而,这位孙子也继承了对诗的热情,他的良心也很容易麻木不仁。
所以他一方面计划将这本日记永远占为己有,另一方面也决定该如何处置它。经过了许多年,这本书的编辑通过了许多渠道,在当事人都匿名的条件之下,获取了这份珍贵的文件。现在,经过将近七十五年的延宕之后,这本书终于能满足所有狄金森迷的需要。
这本日记是一本小小的、深棕色的书,大约是五乘七英寸的大小,里面的空白页被设计为做任何形式的书写。里头的记载每则都有日与月的日期写在抬头处,不过年份的记载只出现过一次。日记是用墨水写的,划掉或修改的字并不多。有可能艾米莉先以铅笔为部分、甚至是全部的日记打草稿,就像她写诗的方式一样,但是其中的几则记载却好像又有别种做法。
日记开始于一八六七年的三月,结束于一年多之后,一共有一百〇二则记载,显然其间的间隔从几天到一星期都有。第一则记载说明了,为什么艾米莉·狄金森要写日记,但一八六八年四月突然结束的原因却不太清楚,但最后一则日记的确有结束的感觉。正如艾米莉在其它地方所说的,“我的生命太简单艰苦,以致于有人可能为此感到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