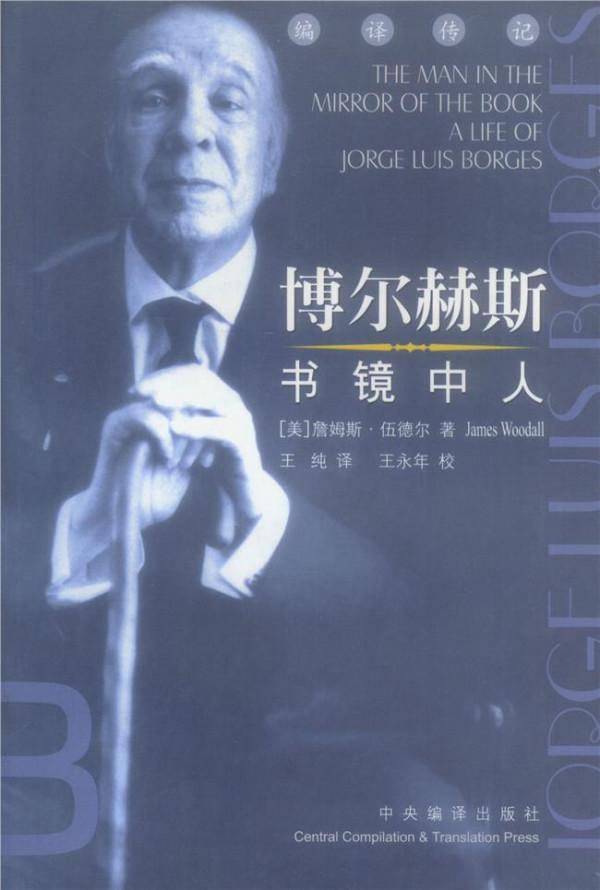博尔赫斯小说《南方》:一首优美而悲壮的诗
如今你在我身体里,你是我朦胧的命运。
那些感觉至死才会消失。
——博尔赫斯
像所有的男人一样,他生平也玩过刀子,但他只知道刺杀时刀刃应该冲里面,刀子应该从下往上挑。疗养院里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落到我头上,他想道。
“咱们到外面去。”对方说。
他们出了店门,如果说达尔曼没有希望,他至少也没有恐惧。他跨过门槛时心想,在疗养院的第一晚,当他们把注射针头扎进他胳臂时,如果他能在旷野上持刀拼杀,死于械斗,对他倒是解脱,是幸福,是欢乐。他还想,如果当时他能选择或向往他死的方式,这样的死亡正是他要选择或向往的。
达尔曼紧握他不善于使用的匕首,向平原走去。
这是博尔赫斯的小说《南方》的结尾部分。
匕首,恶棍,旷野,死亡,一触即发的械斗。这一切似乎就要在一次偶然事件的瞬间发生了,却又戛然而止。博尔赫斯是那种语言抵达事实速度极快的作家,就像武侠里传奇的“小李飞刀”:拔刀,掷出,刀子的飞行路线,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刀子一闪,已射进了你的身体,鲜血渗出。
博尔赫斯的小说总像诗一样精炼,优美,而又不失史诗般的故事性,将往昔的某种生活方式梦幻似的呈现。
一首诗,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故事来读;而一个故事,我们居然也可以把它当成一首诗来读。(这难道是一种奇怪的阅读现象?)小说,是故事。但好小说,伟大的小说,本质上却是诗。然而,博尔赫斯笔下的小说(或诗),却富有哲学、美学的魅惑力。这种魅惑力被卡尔维诺概括为,“我在博尔赫斯的身上发现一个概念,亦即文学是由智性所建造、支配的世界。”(见《卡尔维诺评博尔赫斯》)
只要一接触博尔赫斯的小说,你就会被他的文字勾引进那个“由智性所建造、支配的世界”。我阅读博尔赫斯的感觉,被略萨用文字准确捕捉:“我一边翻阅,一边感到惊奇,如同我第一次读他的作品那样,为他行文的优美和简洁、故事的精巧和善于结构故事的完美手段惊叹不已。”(见《博尔赫斯的虚构》)
博尔赫斯最精致的小说,我以为集中体现在:《玫瑰角的汉子》,《小径分岔的花园》,《马可福音》,《埃玛·宗兹》,《南方》诸篇。其中,《南方》被博尔赫斯自诩为“最得意的故事”。
阅读博尔赫斯的小说,是对读者智性的一次考量。初读《南方》,我便私下强烈地认为:它和鲁迅的《孔乙己》,可以排进世界十大短篇小说之列。随后,我不断地重读,但始终沉溺在最初的感觉里,无法超越。至今在小说结尾留白处,仍赫然呈现着当初的红铅笔批注:
1、 首先是一个关于归乡的传奇故事。
2、 命运不可逆转地决定于某些细小的偶然事件。
3、 未消失的祖辈英勇精神在一个男人身体里的复活。
4、 “南方”作为抽象概念是一个无法抵达的梦。(这样的结尾,如果换了鲁迅,会写下去,让血淋淋的结果呈现,这是由中国语境决定的;而显然博尔赫斯不会这样做,这是由其美学理念决定的。时间并非直线的,结果未必是死亡,甚或只是达尔曼的一个梦。也许他从未离开过城市,南方于他始终是个抽象概念(这是一种写法,但不无可能)。
这些心领神会,直到不久前才得到了验证。我偶然从网上看到一段资料:1976年3月,博尔赫斯在印第安纳大学演讲时,谈到创作《南方》是受了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螺丝在拧紧》的影响,他有意尝试一次写三个故事:传奇故事,寓言故事,梦的故事。我吃惊地发现,我的领会(理解)全部落入博尔赫斯当初的精心设计里,毫无创造性可言。
如今,我已经拥有了一套博尔赫斯作品集和一本《博尔赫斯谈诗论艺》。我希望:当我这样写下去时,会生成某种新的感觉。
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给所有的人设置了相同的迷宫。这是一个宏大的、布满迷径错途的网状系统。------我必须做的事是在所有交叉口竖立起路标,帮助人们通过危险地段。”(见《文化与价值》不同的阅读姿态,或者观察方式,或者思维方式,决定着你的理解视野的走向及深度。
作为“传奇故事”的《南方》,三言五语就可以说清楚:胡安.达尔曼,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市立图书馆的秘书,一次小小的事故让他患上了败血症。在经历了一段生不如死的医院生活后,他幸运地活了下来,然后选择去从祖辈继承下来的南方庄园休养。
南方的气息唤醒了达尔曼的生活欲望。在接近故园的一家小店铺里,他却意外地受到了一个恶棍的再三挑逗。他也曾想“忍”一下算了,但当店主莫名其妙地叫出他的姓氏后,面对死亡的再次威胁,他再次做出了生活的选择:毫无畏惧地捡起了一个高乔老头扔给他的一把亮晃晃的匕首。
在这个传奇故事里,我们惊异地清晰地看见了一个平日里忧郁孤寂的卑微的人,对死亡的向往式的选择,以及那种决然的赴死心境和勇气!死亡,是永恒的一种方式。永恒,以死的方式在瞬间得以呈现。其实这一切,早在小说的开篇就已经得到了暗示。
只不过,博尔赫斯有意抹杀了偶然与必然的界限,让读者意识到同一性的赫然在场。小说一开篇,就描述了达尔曼拥有“两个格格不入的家世”:一个是作为福音派教会牧师的祖父,一个是作为作战步兵二团英雄的外祖父。
在两个格格不入的家世之间,达尔曼选择了浪漫主义的先辈,或者浪漫主义的死亡的家世。这样看来,小店铺事件,激活了沉睡在达尔曼日耳曼血液里的先辈的英雄精神。对此,残雪以一个作家审视另一个作家的视角,对达尔曼的英勇赴死行径深情地写道:“这种选择达到了美感的极限,是人类的骄傲,是精神不朽的象征。
当我们凝视平原上这个人那笨拙而坚定的背影时,我们会不由得感叹道:人,究竟是这大地上的一种什么奇迹啊!”(见《残雪自选集》)
有一种流俗的但不无道理的观点:任何小说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我的确在小说《南方》里,看见了博尔赫斯的影子,甚至分不清握紧明晃晃匕首的,是卑微而高傲不屈的达尔曼还是身体孱弱而博学优雅的博尔赫斯本人?手握匕首,就是抓住了永恒。因为匕首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永恒的”。(见博尔赫斯诗作《匕首》,另,博尔赫斯有一篇关于匕首的精彩故事《遭遇》。)读一读《博尔赫斯传》,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看法。
在博尔赫斯戏拟的《南部美洲百科全书》的关于自己的“词条”里,他写道:“他出自军人家庭,非常怀念先辈们那可歌可泣的人生。他深信勇敢是男人难得能有的品德之一,但是,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信仰却使他崇敬起了下流社会的人们。”在献给被高乔游击队杀害的祖先弗朗西斯科的《猜测的诗》里,他这样描述死亡:
如今即将死于非命,暴尸沼泽;
但是一种隐秘的欢乐
使我感到无法解释的骄傲。
但博尔赫斯是个博览群书深谙哲学的讲故事的老手,他并不满足于只写一个“传奇故事”。在《杜撰集》的“1956年补记”里,博尔赫斯狡猾地介绍说:“《南方》也许是我最得意的故事,我要说的只是既可以把它当做传奇故事的直接叙述来看,也可以从别的角度来看。”别的什么角度?他没有说。
说实在的,我并不喜欢所谓的“寓言故事”,这或许缘自早年读《伊索寓言》的恶感。按照“寓言读法”,我们会看见另一个关于南方的故事:卑微的达尔曼,在经历了一次死亡的挣扎后,无限向往远在南方的故园。他愉快的幸福的踏上了前往南方的旅程,却因偶然事件死在了就要抵达家园的路上。
南方杀害了他。一个人居然死于他所热爱的事物。这似乎是王尔德所说的“每个人都戕害了他所热爱的事物”的颠倒。我怀疑这样的寓意,会给读者带来什么快乐、什么真理?
我确信博尔赫斯在写作《南方》时,心里想的是一个关于“梦的故事”。博尔赫斯以文学的“梦的故事”,否定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关于梦的解析:愿望的达成。幻想领域的梦,常常给现实带来这样一种糟糕的真相:未能抵达。
这是博尔赫斯从卡夫卡的小说《城堡》里看出来的主题。(见《卡夫卡及其先驱者》)未能抵达,是一种人的存在的真实状况。其中深含哲学、美学的况味:未能抵达,投射着人的处境、挣扎和不屈的精神。(中国诗歌《蒹葭》预言了博尔赫斯的美学观念)时间、梦、无限、游戏、循环、本体、真实性、双重性、永恒性,这些与哲学、美学纠缠着的题材,都以故事的形式萦绕在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里,变成了文学,在虚构的笔调里把它们幻化成了文学想象力的组成元素。
略萨独特地指出,博尔赫斯是在从事着“物质世界幻觉化的事业”。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野性十足的恶棍,草原上玩刀子的骑手,总是强烈地吸引着博尔赫斯的目光。
博尔赫斯在达尔曼身上投射了自己的影子,投射了自己的梦想。
拥有一注从浪漫主义先辈继承的产业的“南方”,在抵达之前对于达尔曼而言,只是一个符征,一个抽象概念,一个等待他归去的梦(家,故乡)。现实的生存状态让他感到厌倦,命运的毫不容情(败血症)使他恨透了一切。他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悲哀,甚至失声哭泣。
死里求生,灵魂深处,他听见了“比较古老塌实的南方”的召唤。于是,在“早晨的黄色光线下”的梦幻般的时光里,他幸福的动身前往南方。城市,也迷离着南方老宅的气氛:窗户、门铃、大门的拱顶、长门厅和亲切的小院。(迷离似梦)
在火车站大厅里,他抚摩着一只黑猫,似乎领悟了“瞬间即永恒”的真理。在列车上,他取出第一册《一千零一夜》,以挑战者的姿态得意地认为,以前的不幸已经一笔勾销,他已经逃出了不幸命运的循环,走向了追求永恒之路。他看见秋日大地上的一系列景致,却有种“偶遇”的感觉,“仿佛平原上的梦境”。
尽管列车错过了惯常的车站,达尔曼并不在意,平原上三叶草的气息令他“心醉神迷”。杂货铺,简陋的建筑使他想到《保尔和弗吉尼亚》里的插图,他却没有意识到,在法国圣比埃尔的笔下,保尔和弗吉尼亚从小青梅竹马,却终未能结合。
(多么精巧的暗示!)达尔曼看见了南方的象征,一个老高乔人:黧黑、瘦小、干瘪,像件一动不动的东西,像块流水磨光的石头,像句几代人锤炼的谚语,超越时间之外,处于永恒。博尔赫斯注解说:达尔曼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所属的南方的集中体现。于是,当小庄园的雇工恶棍一再向他挑衅、店主喊出他的姓氏后,他无畏地捡起了老高乔人扔给他的匕首,紧握着,向平原走去。
达尔曼别无选择的选择了“直面死亡”。他内心充满了人生解脱后的“幸福”与“欢乐”。匕首,生里求死(瞬间永恒),在他的血液里迅速滋长,成为他热血沸腾的一种渴望,毫无恐惧。“能在旷野上持刀拼杀,死于械斗”,与其说是达尔曼要选择或向往的梦境,不如说是博尔赫斯内心深处的一个无比壮丽的幻梦。手握匕首,向平原走去的达尔曼,带着博尔赫斯的壮丽之梦,在瞬间幻化成了一种“永恒”。
英格利斯说:家是一个很多人愿意为之赴汤蹈火的政治概念。(见《文化》第九十三页)我们从不为“未能抵达”的境遇,而抛弃这个人间最美的概念:家园(或故乡)!
在“梦的故事”里,我们不仅看见了一种优美,也领会了一种悲壮。
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南方》当做关于一个老高乔人的“匕首的故事”来读。这想法的启示,来自于博尔赫斯的另一篇小说《遭遇》:我跟着表哥去参加一个烧烤聚会,客人是一群年轻人。我溜出去,在一个神秘的房间里看见了一些被用得出了名的刀子。
后来,两个年轻人争吵起来,要决斗。我说出了藏武器的房子。一把带U字形护手柄的匕首和刀刃上镌刻着一棵小树花纹的刀子,分别被两个年轻人选中。决斗中,带U字形护手柄的匕首捅进了一个年轻人的胸部,他死了。
后来,一位退休的警察局长听了故事后,断定两把匕首早先分别属于两个结了怨仇的刀客,他们互相寻仇但从未见面。这使博尔赫斯有理由认为:两件武器沉睡在房子里,直到被人触动唤醒。人的夙愿沉睡在他们的兵刃里,窥伺时机。
当达尔曼幸福地向往南方时,一把象征南方的匕首沉睡在一个老高乔人的腰间,等待着它的新主人。在一个洒满夕阳余晖的小店铺里,匕首终于等到了甘原为南方拼杀的达尔曼。达尔曼,骨子里是个南方草原上的骑手。
这种读法的意义何在?我一时说不清楚。
余华在《温暖的旅程》里将博尔赫斯与鲁迅并举,说他们都“是我们文学里思维清晰和思维敏捷的象征”;又将《南方》与《孔乙己》并举,说它们“都是叙述上惜墨如金的典范,都是文学中精瘦如骨的形象”。斯言颇令人解颐。
我曾经希望我的学生也知道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博尔赫斯,多接触些富有智性的文学。
在教学鲁迅的《孔乙己》时,最后我指点学生们来比较阅读《南方》。从文本语言的角度切入,直至抵达两种文化的精神。我当时以为:理解《孔乙己》里未说出的有难度,如果看清了达尔曼毫无畏惧的英勇选择,也就看清了孔乙己懦弱而悲惨的死,也就听出了鲁迅的“呐喊”之声。(现在我意识到,也许存在另一种可能:另一个问题的介入,反而会混淆了最初的问题。比较的副作用。)
我的学生还小,豆蔻年华,再精致的分析和解释都没有用。但我确信:当我高声朗诵《南方》的某些句子和语词给他们听时,有一种情感,有一种精神,将随着朗读者语调的跌宕变化而激荡他们纯净而稚嫩的心灵!(康德所谓的启蒙?幼稚就是如果没有外人的指导就无法运用自己的理解而表现出的无能------理性为其客体提供理解和有意的使用。见《文化》第九页)
因此,关于《南方》,我只能写下残雪所理解的标题:一首优美而悲壮的诗。优美,是指来自语言文字的魅力;悲壮,是指来自人类精神的动力。
我知道,对于伟大的短篇小说《南方》而言,我的评论文字只不过是匆匆过客。但令我确信无疑的是:在这些评论性文字背后,我证明了一个关于理解现象的理论。
(博尔赫斯作品系列之《虚构集》,王永年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