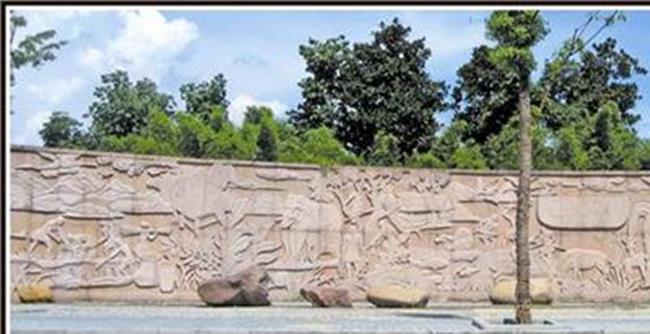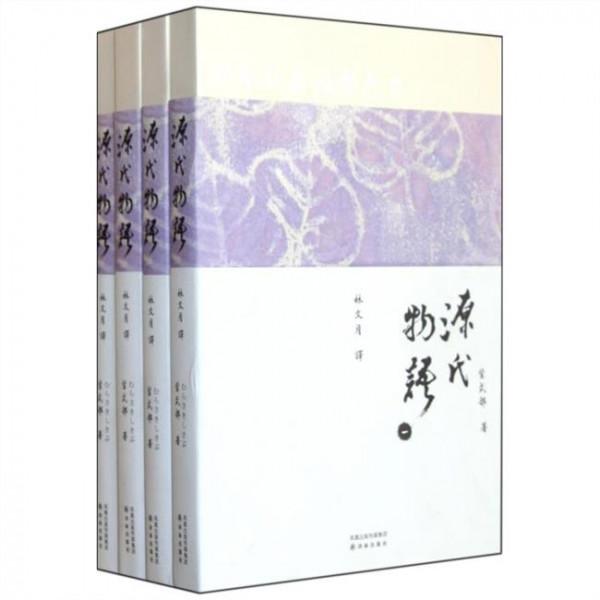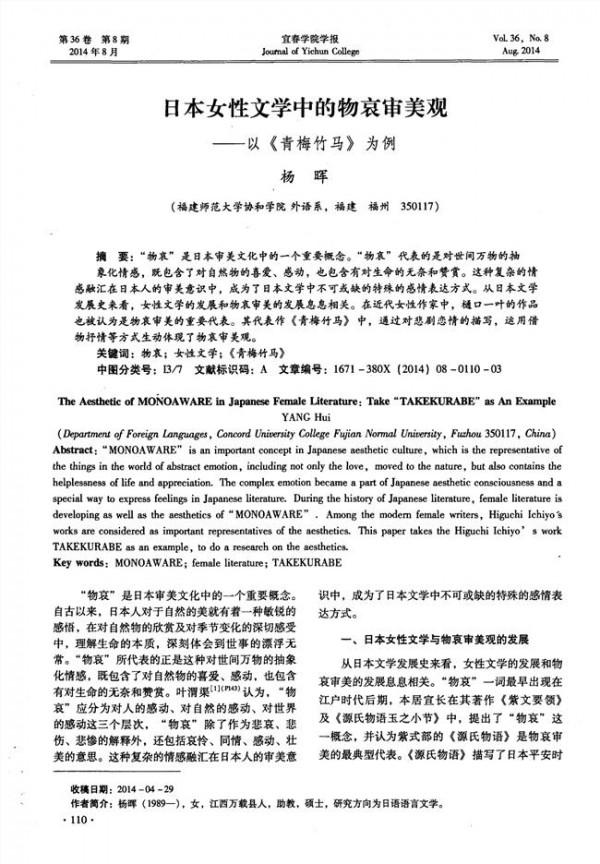【樋口一叶《青梅竹马》】无可奈何花落去 ——评樋口一叶《青梅竹马》
在《青梅竹马》的结尾,美登利在院子里捡到了一朵纸水仙花,虽然猜不出是谁丢的,但她却怀着不胜依恋的心情把它插在小花瓶里,独自欣赏它那寂寞而清秀的姿态。后来她无意中听说,在她拾花的第二天,信如为了求学穿上了法衣,离开寺院出门去了。

整个故事在这里戛然而止,只余下淡淡的惆怅,和似乎预示着不祥的袅袅哀音。这种对人生遭际无可奈何和默默接受的态度,不仅贯穿了樋口一叶全盛时期的创作轨迹,也昭示了作者的人生困局,和终究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

早在周作人推崇樋口一叶之时,就有评论家将她与当时的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庐隐做比,认为她们同是感伤的悲观主义者,她们笔下的人物都是找不到出路的,渐渐地在黑暗冰冷的现实中失却了生活的勇气,最后只能负荷着冷酷、无情的现实,在悲哀中走向人生的尽头。

但是由于日本文学传统和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审美取向差异过大,庐隐作品中那种“总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的风格,在樋口一叶的作品中是看不到的。
《青梅竹马》的整体色彩是浓艳而轻快的,仿佛是繁花锦簇的浮世绘,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如果你被浮在表面的热闹所吸引,那你很有可能会忽略了,在浓重的色彩底下,正轻柔地哼唱着一首哀而不伤的和歌。

一个是注定要穿上黑色法衣出家为僧的十五岁少年,为人检肃持重,厌恶世俗奢靡;一个是未来将追随名妓姐姐在“花街”卖笑维生的十四岁少女,素来轻浮活泼,不以卖笑为耻。这样身份地位喜好秉性都南辕北辙的两个人,势必是没有未来的,但是这一切都无法阻止他们彼此之间产生一些微妙的感觉。
与罗密欧与朱丽叶那种一见钟情便迸发激情所不同的是,东方的爱情是在朝夕相处中朦胧而生的,充满了细水长流的默契和小心翼翼地试探。信如和美登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邻居和同学生涯,与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同窗生涯皆是如此,而英台在“十八相送”的暗示与表白,则与信如和美登利在雨天的窘迫和挣扎如出一辙。
文中直接描写信如和美登利的段落和笔墨少之又少,对话则基本没有。二人的心思都是通过他们的行为来展现的———言语可以欺骗别人和自己,但是下意识的行为则无法控制。这种高超的叙事手法和留白技巧,与其说像庐隐,不如说像同时代的短篇小说圣手泉镜花,泉镜花的名作《外科室》和《琵琶传》两篇如同《青梅竹马》一般,没有浪费一字一句去描写主人公爱情的萌芽与发展,“情”字不在文中,却体现在他们的一举一动之中,让观者不禁慨叹,如果彼此无情,又何至于此?
信如因为怕别人闲话,刻意板起脸来,装作冷淡地不理美登利,和《红楼梦》中薛宝钗因为听母亲和王夫人总提“金玉良缘”,所以“总远着宝玉”一样,是少年情窦初开之时的懵懂与自矜。然而情感总会战胜理智,就像宝钗会情不自禁地坐在午睡的宝玉身边做针线活,信如也会在不经意之间,刻意绕路到美登利住的大黑屋前一样,“任是无情也动人”。
樋口一叶的文学基因,是深得中国传统文学和 《源氏物语》 真味的,像是半悬在夜空中的冷月,情思若隐若现,那么美,又那么凉。
然而樋口一叶能够得到超越时代的赞誉,还在于她不仅仅写的是爱情小说,她还关注着爱情之外更广阔的现实世界。《青梅竹马》与其说是“爱情之殇”,不如定义为“青春之殇”,因为无论是信如、美登利,还是田中正太郎,他们都不得不面对童真的丧失,而沉重地戴上社会身份的面具,被自己的社会责任所绑架。
正如文中预示的那样,象征爱情的红友禅布条,和象征着纯洁的纸百合花,最终都孤单单地躺在格子门外的泥地里,落得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结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