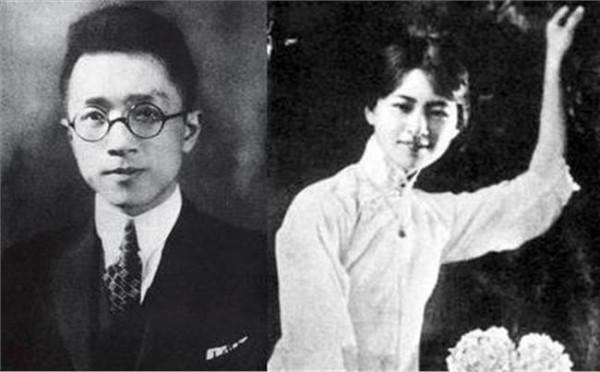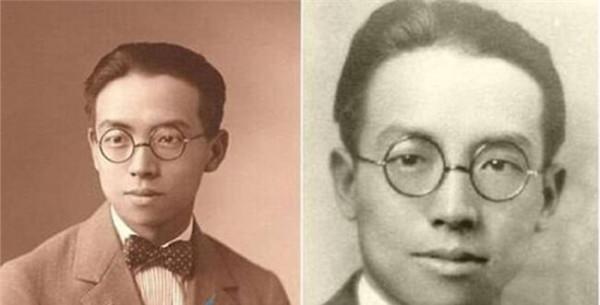【费正清和林徽因】费正清夫妇与林徽因
1942年9月25日费正清从昆明飞往重庆。在昆明等待航班的那几天,费正清借机看望了大学中的一些朋友。
北京胡同婚礼上的费正清夫妇
费正清夫妇与林徽因等
费正清夫妇与梁思成夫妇
左起:查良钊、胡适、梅贻琦、黄钰生

梅贻琦校长比费正清记忆中的要更加消瘦,衣着破旧,为人依然热情。张奚若一家住在秦氏宗祠中,钱端升和梁思成夫妇则住在昆明五英里之外的乡村。张奚若陪同费正清驱车到了龙头村,访问了钱端升。返回昆明城后,费正清参加了梅贻琦校长在家中的宴请。

费正清当年的文稿如此记录:“梅博士的房子很大,尽主人之谊,邀请所有教职员工,他们大多数在顶楼住宿,也没有多余的地方接待其他访客。据温德说,梅博士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600元,而这次宴会的花销绝不少于1000元。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送了梅博士一瓶一英寸高的治疗疟疾的阿的平药片,这应该可以换回1000元了。”
战时通货膨胀带来的反常现象和昆明教职工的生存状况令费正清“极为震惊”,他立即写信向华盛顿作了汇报。我后来偶然读到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冯至先生回忆联大生活的文章,明白了费正清何以“极为震惊”。冯至提及抗战结束后西南联大经济系教授杨西孟先生在上海《观察》杂志第三期发表的一篇文章,《几年来昆明大学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实值》。
杨教授从生活费指数为100、薪津约数与薪津实值相等的1937年算起,往后几年薪津的实值“如崩岩一般”地降落。
根据杨教授的计算,到1943年下半年昆明的大学教授下半年的薪津实值只等于战前法币八元三角,即是削减了原待遇百分之九十八。1944年、1945年上半年薪津实值盘桓于十元左右。亲历了抗战中高度通货膨胀下的昆明生活,杨教授感觉有如“噩梦一场”,他感叹道:“在抗战后期大学教授以战前八元至十元的待遇怎样维持他们和他们家庭的生活呢?这就需要描述怎样消耗早先的储蓄,典卖衣服以及书籍,卖稿卖文、营养不足、衰弱、疾病、儿女夭亡等等现象。
换句话说,经常的收入不足,只有消蚀资本,而最后的资本只有健康和生命。”
费正清从昆明向北飞行。“越过一座又一座翠绿的山脊,绿色植被下是红色的土壤,半山腰布满稻田。我们上升到1.2万米高的云层中,随后又下降,河流和山岚一览无余。”但落地后,重庆给费正清的印象远不是在天空中升降时感受到的那种诗意:“此地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因为没有平坦的陆地。
人们简直成了力图找到安身之地的山羊。”在这个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岩石重叠的半岛上,费正清度过了十五个月。他后来回忆说,冷战或是中国革命都没有令他感到“烦恼”。在重庆十五个月是他烦恼的日子:晴天时日机轰炸,日常遇到的问题是潮湿。
重庆有很多费正清十年前在北京就认识的朋友。费正清拜访了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邂逅前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在重庆郊外访问了国立中央大学和南开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的何廉也是费正清的老朋友。特别让费正清兴奋的是,1942年9月26日,他在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宿舍区见到了老朋友梁思成。
费正清说,梁思成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足足有五分钟。这是他们自1935年圣诞节分别后的重逢。11月下旬,费正清搭乘小火轮沿着长江逆流而上访问李庄。
费正清的印象是,梁思成的家庭生活一如既往地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生活水平的降低使问题更加基本、简单。梁思成喜欢吃辛辣的食物,林徽因则喜欢偏酸口味。我们后来听到的关于他们纯美的爱情传说省略了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费正清当年的文稿详细叙述了梁思成家生活窘困的境况。费正清在李庄的一周,由于天气寒冷,大部分时间在床上度过,他被学者朋友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感动。
林徽因在李庄居住的卧室
左起:施嘉炀、钱端升、陈岱孙、金岳霖、周培源、萨本栋、张奚若
与左翼人士的交往,是费正清在重庆的另一重要工作。费正清在1943年的9月驱车前往文化工作委员会夏季使用的农舍,郭沫若和主要同事热情接待,宴会上喝了几瓶极品美酒。费正清感觉他和郭沫若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了”。
10月,费正清又应邀参加了郭沫若的五十岁生日宴会。随后,他又结识了茅盾和陶行知。费正清敏锐地发现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实际困境,他当年的文稿写道:“事实上,这个委员会更像是一种限制行为的围栏,已有很多知名作家被圈在里面。假如他们离开这里前往延安,将会对统一战线造成一场灾难。”有意思的是,1972年费正清访华之前,老朋友郭沫若也表达了欢迎之意,但郭沫若并不在费正清想见的朋友名单里。
费正清坦率地说,一旦和乔冠华、龚澎、杨刚等成为朋友,他自己也受到“左翼分子”的影响,而他个人也喜欢相应地对其施加影响。费正清意识到,这样的互动,既是个人行为,也是政治层面的互动。费正清后来回想,他对中国“左翼分子”的兴趣受到家庭的影响,即倾向于支持受迫害者的自由主义的观点。
费正清也试图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保持某种平衡,他在1943年10月的记录是:“这里生活的主题似乎就是物价与革命。我与菲利普·斯普劳斯一起宴请了国民参政会的共产党员董必武老先生和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
前者说着令人费解的方言,后者则思维活跃,不时会冒出一个新想法。为了验证他们的说法,第二天早上我又去走访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战区党务处。周三与蒋介石的首席日本问题专家共进晚餐,于是我在想,周四我应该拜访共产党人士,这样才能保持大致的公平而没有偏见。”但费正清敏锐地发现,1943年正是蒋介石集团走向末路的开始。
即便是落实中美文化关系项目,费正清也周到地考虑了左翼人士。战后重返中国,1946年6月初,费慰梅和费正清为了挑选华北联合大学的四名学者前往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考察,经北京前往张家口。在那里,他们与周扬、丁玲、成仿吾、艾青等共进了午餐。
费正清提到的这个细节,也让我感慨周扬、丁玲、艾青十年之后关系的变化。8月,周扬几个人在上海准备出发前往美国。14日,郭沫若、茅盾、胡风、吴晗等四十多人在郭沫若家为周扬送行。
胡风在日记中写道:“郭家晚饭,为周扬饯行之意。”这个交流考察计划因国民党政府拒绝给周扬等四人颁发护照而落空,周扬只能返回延安。我曾经设想,如果周扬能够成行,在美国考察交流一年,他的文学观会不会有所变化。
费正清将自己在战时中国的朋友分为两类:一类是受西方教育的追求自由主义的教授们,其中很多是三十年代初在北京相识,如今再次重逢的老朋友;一类是作为左翼分子的新朋友,他们也是西方教育在中国的产物,而如今则成为共产主义的拥护者并为之奋斗。
费正清逐渐意识到:“作为老一辈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权力的辅助者而非掌控者,因此他们并不能起到领导作用。而另一方面,年轻的左翼分子虽然不够强大,但是他们充满希望且足智多谋,也许有机会在未来有所发展。”费正清特别强调,“我的这两类朋友都在与当权者进行着殊死斗争,我将他们视作道德英雄。”
此时,费正清的信念是,中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现实社会中的内在产物,CC系和戴笠的特务机构无法将其压制,蒋介石也根本无法与其对抗。对革命并无兴趣的费正清,在重庆卸任时产生的这一信念,只是源于“某种共鸣”。他恰如其分地对自己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给了这样的定位:“在革命中,我只是一个多管闲事的旁观者,但我能够感觉到革命的风向。”
1943年12月,费正清带着这样的信念,回到了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