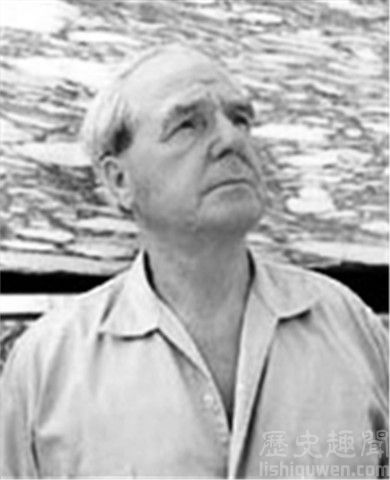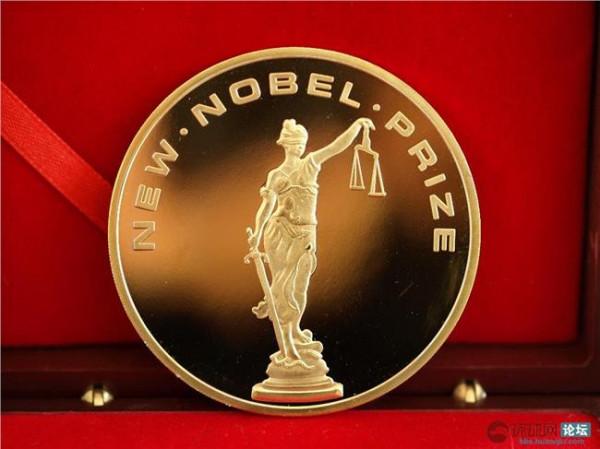摩尔根文明 摩尔根与“政治文明”
最近,“政治文明”这个概念悄然进入了我们的政治语汇中,这使我产生了某种也许值得一说的好奇心。
在人类学这个行当里,“政治文明”也曾是一个关键词。对此,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便是一个例证。一般认为,《古代社会》这本书叙述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它集中分析了仍然流行于当时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当中的各种“亲属制度”;另一方面,它花了大量笔墨来描述世界诸文明的政治-法权制度中“亲属制度”的遗留因素。
乍看起来,《古代社会》一书,与“政治文明”的概念完全没有关系——这本书里铺陈的大多是“政治文明”产生之前的诸种与“亲属制度”相关的社会形态。
然而,为了写一本关于摩尔根的书,我重新阅读了他的《古代社会》,从中获得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印象:其实,整部《古代社会》所呈现的,恰恰是“政治文明”的生成原理。
读《古代社会》使我们认识到,在摩尔根的定义中,“政治文明”指的就是所谓的政治社会,而政治社会是与氏族社会相对的、在历史时间上“先进于氏族社会”的社会形态。对于政治社会的形成而言,人际关系从血亲-姻亲关系体系的约束中解放出来,进入超越血亲-姻亲关系体系的地缘组织-管理,这是最重要的前提。
摩尔根的确有点“民族中心主义”,他认为,这一历史的超越,首先发生于欧洲的希腊,在雅典的政治制度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在雅典文明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开始不再以血亲-姻亲的原则来结合。
早期的政府为了实现“政治文明化”,将原来遵照“氏族社会”原理组合而成的村社改造为区域性的行政管理单位,使这些单位一层层区分,用军队的管理方式来组织,使之最终能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政体。
“政治社会”的本意,原来在于以军队的管理方式来造就一个超越“氏族社会”一盘散沙面貌的“民族”(nation)。然而,这种统一的“民族”的出现,需要民众的参与。为了实现这种参与,既有的“氏族社会”的某些因素得到保留。
其中,最重要的,乃是“氏族社会”民主选举领袖的制度。为了揭示“氏族社会”民主选举制度的实质,摩尔根总结了自己在其中从事过实地社会调查的易洛魁人氏族制度的经验,费了一番心思在世界范围内搜寻同类经验的“历史遗留”,面面俱到地罗列了“氏族民主制度”的特征,得出一个饶有兴味的结论:“政治文明”既是人类脱离蒙昧、野蛮的“血亲社会”的成就,又是对这些社会中“民主制度基因”的继承。
摩尔根写作《古代社会》的一个目的,确是旨在对文明社会产生之前“亲属制度”在社会结构中的关键作用展开探索。因而,中国的前辈人类学家(也称民族学家)也有理由将精力集中于《古代社会》对于亲属制度的分类研究上。
历史也是这样发生的。过去,中国人类学家将《古代社会》的叙述框架运用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研究上,从国内丰富的民族志案例中发现了依据血亲-姻亲制度的原理组合起来的诸种“前资本主义”和“前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系列。
在古代史研究中,前辈学者则更注重恩格斯笔下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斯大林的“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接着“原始社会史”,追溯中国文明的“生产方式”和“阶级矛盾”阶段化演变的线索。除了极其个别的例外,无论是人类学还是古代史研究,都极少关注到摩尔根原著中的“政治文明”这个概念。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国人如此排斥在摩尔根的书里占有如此之高地位的“政治文明”概念呢?原因当然要到50多年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内部去寻找了。我们不能忘记,一度专攻摩尔根著述的美国人类学家怀特曾说,摩尔根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儿”。
或许正是因为摩尔根的这一“时代品格”造就了他的“政治文明”理论;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产儿”摩尔根提出的“政治文明”理论才被抛出我们的理论视野之外。而即使我们已懒得求索这里面的历史因由,我们也还是应当看到,摩尔根的“政治文明”理论,与我们今日政治话语中的“政治文明”之间,还是有诸多相关的纽带。
话语意义上的“政治文明”该如何定义,我不了解,但我大致知道,大凡用这个概念的人,都想借它来指一种对某种新政治体制的预期。广义上,“政治文明”被认为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现代化”怎么解释?难度也很大。
从政治文化上看,它一般指的是在政治体制上的“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指的便是那一能使我们脱离旧有政治面貌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的“政治文明”,与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相关诠释还是有关系的。怎样使政治生活既能统一于某一值得追随的一体化机制中,同时又能摆脱权力的过度集中?怎样使政治生活既整合为一种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进而使自身与传统的“非法权性社会关系体系”区别开来,同时又使之能在相对宽松、令人容易接受的条件下集纳民众参与?这些问题,似乎便是“政治文明”一词所要解决的。
倘若“政治文明”是这样一个政治的辩证法,那么,它在130年前已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中得到了隐晦的表述。所不同的是,对于摩尔根来说,“政治文明”中柔性(民主)的基因,源自于“氏族社会”的启发;而今日我们通常认为这一点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现在的“政治文明”,更多的受已走在我们前面的“雅典人的后代”的启发;而若说摩尔根的“政治文明”理论有何精彩之处,那这正在于,它为我们指出,雅典的“政治文明”,是在包括我们祖宗在内的人类祖先的“氏族民主制度”基础上演化出来的(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一生想说明的历史,便是早期文明中血亲关系与王权政治之间的藕断丝连的关系)。
这也就是说,若不能基于全人类(包括西方和非西方)的政治经验来想象未来,任何的“进步”的观念便都可能流于表面化。
重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仍是有其意义的。至少,这能使我意识到,摩尔根预示的雅典民主政治的最终胜利,也是摩尔根的幽灵给我们的告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