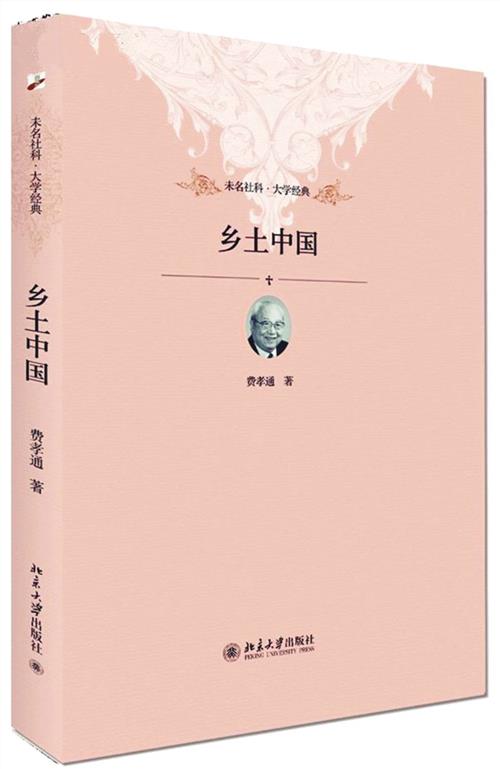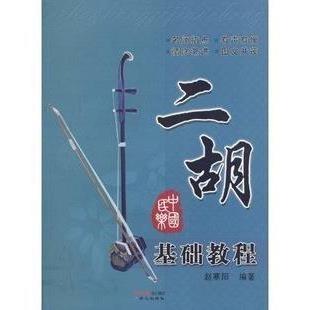【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发展为中国法治实践所需要的中国法理学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中国的法理学乃至法学伴随着中国法治实践的进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笔者试回顾70年来中国法理学的发展历程,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为未来中国法理学提出更大的愿景和发展目标。
新中国70年法理学发展的历程
我国的法理学从其产生开始,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门类,法理学在我国始于上世纪初。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苏联法学教育及其理论的影响,我国的法理学被冠之以“国家与法权理论”或“国家与法的理论”之名称。
上世纪50年代由我国学者撰写、翻译、出版的著作大都以这两者命名,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国家重新重视法制,法学院逐渐恢复和重建,作为法学院学生基础必修课之一的法理学,仍是以“国家与法的理论”之名目和内容来讲授。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政治学学科的恢复和重建,也由于法理学界对法学学科体系尤其是对其中的“国家与法的理论”学科的探讨和争论,原有的国家理论逐渐地从这门学科中分离出去,归属于政治学学科范畴。
这时,与现代法理学意义较为接近的“法学基础理论”得以产生。1982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法学教材编辑部审订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将此学科定名为“法学基础理论”,这一名称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对外文化交流的逐步扩展,西方法理学不断被介绍进来。尽管“法学基础理论”作为一种“官定”的法学学科名称,但法理学界已不满意于此。于是,以“法理学”作为学科命名的教材、讲义、著作等逐渐在我国的部分区域内和院校内使用,原来的以“法学基础理论”作为专业的研究生招生也有冠之以“法学理论”或“法理学”专业之名。“法理学”作为一种较为通用的法学学科名称,逐渐被法理学界人士所接受。
1994年是我国法理学取得较大发展的一年,其标志是几部在全国或部分院校、地区通用的法理学教材相继出版,这些教材大多采用了“法理学”这一学科命名,并且在学科体系、结构、内容、观点等方面都较以前有大的突破和进展,使我国法理学教学呈现出百花齐放、多元并进的新局面。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法律体制面临着同国际惯例接轨的问题。同样,我国的法学理论体系、法学学科体系也面临着同国际通用惯例相衔接的问题。“法理学”作为一门为国际法学界所通用的法学学科,取代了我国原有的“法学基础理论”。
一门学科的命名,表面上看似乎仅是一个名称问题,但它却像一面镜子反映了时代发展的特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理学这门学科所经历的“国家与法权理论”→“国家与法的理论”→“法学基础理论”→“法理学”的变化看,它打上了历史时代的烙印和痕迹。由最初的对“法理学”持排斥批判态度,到后来的被接受并使用,其中无不反映了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并且,与学科名称相关联,它也反映了这门学科内容的变化和差异。
法理学学科名称和体系的变化,也反映在法理学问题的研究上。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法理学界解放思想,对于一系列重大的法理学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如法的阶级性、社会性问题,法治与人治问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问题、法的继承性问题、民主与法制问题、法制现代化问题、法律文化问题,等等。
这些讨论推动了国家的法治进程,为党和国家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新世纪中国法理学发展的特点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法理学步入了最为辉煌的发展时期。法理学学科体系不断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扩展,思想内容也越来越深入,学科队伍也不断壮大。法理学由过去主要关注较为抽象性的理论问题逐渐转向中国的法治实践问题,法理学越来越接地气。
尤其是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将其载入宪法,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任务, 中国的法理学界围绕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推动了依法治国向纵深发展。总结中国法理学的发展特点,我认为最为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关注实践,二是多元发展。
关注实践。法理学作为法学学科的基础性学科,一般将其特点归纳为抽象性、概括性、一般性、普遍性,以及概而言之的理论性。但随着中国法治实践的不断推进,以及对于法理学“实践理性”学科属性认识的不断深化,我们越来越认为实践性也是法理学的重要特点之一。
法理学来自实践并服务实践。美国法学家德沃金教授在论述法理学与法律实践的关系时讲到:“在法理学与判案或法律实践的任何其他方面之间,不能划出一条固定不变的界线……法理学是判决的一般组成部分,亦即任何依法判决的无声开场白。
”德沃金教授的这段论述表达了法理学与法律实践的关系以及法理学对法律实践所起的不可替代的功能。正是对于法理学实践性特点的重新认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法理学界紧紧围绕中国的改革和法治实践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如关于依法治国方略的研究,法治与改革的关系研究,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研究,法治体系的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研究,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研究,等等。
这些研究都是围绕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重大主题而展开的,对于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多元发展。进入21世纪之后,同时代的变化相呼应,中国的法理学同整个中国法学一样,呈现了一个多元发展的格局。大一统的法理学格局得以改变,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五彩缤纷、多元并存的法理学新格局。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法理学队伍的扩大且多元并存。
在从事法理学工作的学术队伍中,有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法学教育的老一代法学家,也有接受过西方法学教育和苏联法学教育的老一代法学家;有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法学学者,也有七十年代末恢复法学教育后四十多年培养的法学学者;有我国自己培养的“土生土长”的法学博士、硕士,也有留学西方、接受西方法学教育归国的“洋博士”,等等。
这种多样化的教育背景,使法理学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研究视野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法理学多元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中国法学流派已初具萌芽,有关在一些重大法理学问题上的争论已经显现出这种萌芽。法理学的多元发展还表现为法学研究方法的多元。虽然研究方法是同研究对象密不可分的,但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使得法理学也呈现出一种多元发展的趋向。
展望未来:与时代同行,发展为中国法治实践所需要的中国法理学
法理学到底有什么作用和功能,这是中外法学家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创始人李达先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出版的《法理学大纲》中讲到法理学的性质、对象、任务时指出:“法理学的研究,首先要阐明世界法律发展的普遍原理,认识法律的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认识特定历史阶段上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其次要应用哪个普遍原理来认识中国的法律与特殊的中国社会的关系,由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路线,展开与之相适应而又能促进其发展的法律理论,作为改造法律充实法律的指导。
”李达先生对于法理学的性质、研究对象、任务等的论述体现了他的唯物主义法学观,以及高度注重法律与社会实践的关系。这些闪光的观点作为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法理学问题仍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我认为,中国法理学的未来目标,应该是发展为中国法治实践所需要的中国法理学。这一目标的确立,是建立在对于法理学实践功能的认识基础上的。
法理学除了具有“法律观念的启蒙,法律理念的确立”的功能外,它对社会实践、法治实践也有重要的功能。在当代中国法律实务界乃至于法学界,有一种普遍的认识,认为法理学只是法理学界自身的事情,法治实践、法律实务不怎么需要法理学。
60多年前李达先生曾揭示过这一现象。李达先生讲到:“法理学的研究,在中国这样不发达,据我看来,主要的是由于法学家的不予重视,好像认为是一个冷门,教者不感兴趣,学生也勉强听讲。因为应考试、做法官或律师,都不需要法理学。
在培养注释法学的师资与司法人才的今日法学教育环境中,这许是法理学的研究所以不发达的原因了。”当然,60年后的中国法理学比起李达先生当年描绘的状况有了很大改观。法理学作为法学的一门基础学科被置于法学的二级学科之首;各种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中法理学也有了一席之地,等等,但这些仅是一些表面上的变化。
问题的实质在于:法理学是否真正的深入到法治实践中,也即法治实践需不需要法理学,这是法理学发挥功能的主要标志之一。
法理学与法治实践是互为的。一方面,法理学尽管是抽象性的、概括性的、一般性的、普遍性的和理论性的,但法治实践却不能没有法理学。德沃金所讲的“在法理学与判案或法律实践的任何其他方面之间,不能划出一条固定不变的界线。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法治十六字”方针。试想,如果一个立法者没有对法治的深刻理解力和洞察力,没有对法律的深刻洞见和社会关系对法律的需求的精确判断,如何去创制为社会所需要的科学的法律?一个立法者如果不了解法律规范的科学合理结构,不懂得立法的技术性要求,如何去从事具体的立法工作?一个立法者没有对法治的目的、价值的深刻理解,又如何创制出蕴含有民主、正义、公平、公正等价值的法律?再比如,一个执法者或者一个司法者,如果没有对法治精神、价值、理想、原则等的深刻认识,又如何能保证公正的执法和司法?尤其是在法律出现漏洞、空白、不完善等情况下,又根据法治的哪些原则、精神、价值等去合理地使用自由裁量权,公正的判决案件?即便对一个守法者而言,如果没有确立正确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以及对法治的信仰,又如何去遵守法律、使用法律?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具有法理学的基本素养。
正是从这些意义上,德沃金讲的在法理学与判案或法律实践的任何其他方面之间没有一条固定不变的界限。它们之间相互渗透,法理学渗透于法律实践之中,而法律实践又离不开法理学。
另一方面,法理学也离不开法治实践。离开生动和火热的法治实践,法理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法治实践是中国法理学发展的基础源泉和动力机制。中国的法理学紧扣中国法治实践,吸收和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形成自己的理论。
法治实践为法理学提供营养和动力。法治中国建设既是一个法治实践充分展开的过程,也是法理学对法治实践进行指导的重要场域。法理学并不只被动、消极、滞后地反映法治实践。法理学要顺应时代潮流,对发展变化着的社会实践作出合理的、科学的理论分析。先进的法学理论可以对法治实践进行指导,这是我们熟悉的辩证法。
面对未来,中国法理学的发展还须紧扣法治中国的实践进程,关注实践,研究实践,向实践学习,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使法理学有其扎实的、可靠的基础。同时,我们应重视法理学的相对超前作用和对实践的引领作用,大胆借鉴古今中外法理学、法哲学的优秀成果,正确处理应然与实然、理论与现实、价值分析和实证分析等诸多矛盾和关系范畴,为法治实践服务,在实践中检验和反馈法理学研究成果的有效性和有用性,在这种意义上,法治实践是检验法理学成果的重要标准。
展望未来,中国法理学的任务应是:与时代同行,发展中国法治实践所需要的中国法理学。
(作者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