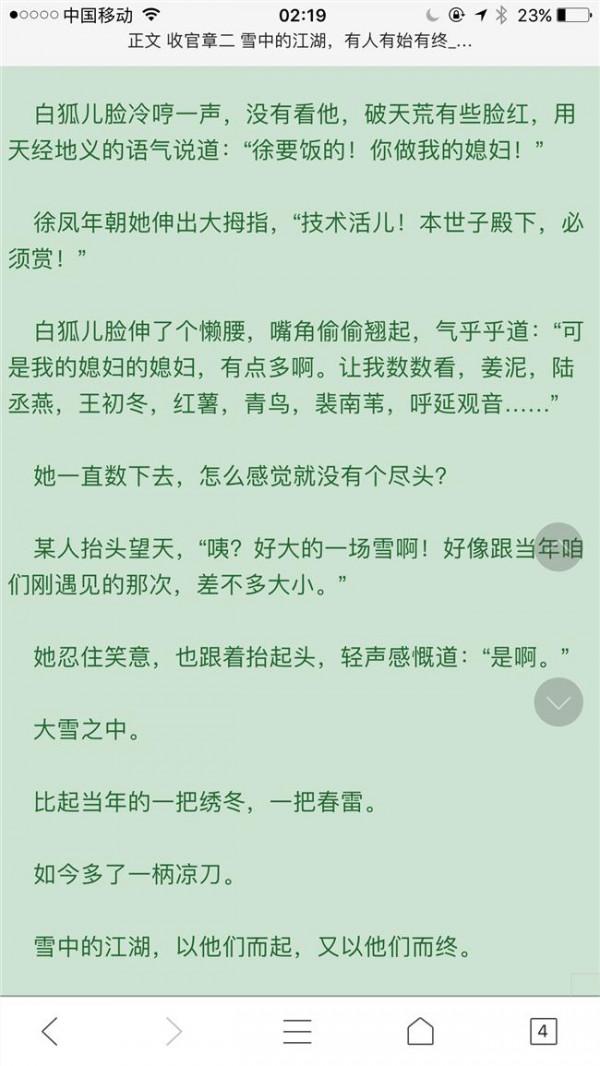【张立宪老六】十年《读库》老六张立宪:“我没那么重要”
老六:原名张立宪,因喜好数字六,自称“老六”。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著名出版人、作家。出版随笔集《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现任《读库》主编,跨工种作业,完成一本书的策划、组稿、编稿、设计、印刷、宣传、发行各环节。

《读库》:张立宪主编的综合性人文社科读物,取“大型阅读仓库”之意,每两月推出一期。于2006年正式创刊,奉行“有趣、有料、有种”方针。
2016年《读库》的轻型化改版,让看惯了它十年模样的人难免有点猝不及防。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对《读库》长久的信任和钟爱,和其带来的阅读仪式感、至少是一种在电子时代难得的来自纸的厚重感有相当的关系。

老六认为这种“不习惯”、“不喜欢”都很正常,但不觉得这将会成为太大的问题,起码从目前来看,订阅量没有减少(现在有13000个全年订户),还能支持这个方案继续往下走。他常说“把书做对”,但如何是“对”,却是在不断变动当中,并没有一个一贯的、统一的标准。“我们现在对书的理解不同了,这是不可逆的。我们在十年前做不出这种设计(新版),但现在会觉得,原来那种设计不如这个好。”

“不如这个好”,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他发现我们现今的中文图书有一种超过其必要性的大和重。三年前,老六就曾和原三联书店副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汪家明以及设计师陆志昌聊起过“把书做对”这件事。当时老六做了三个减法,希望分别减轻读者财力、视力、体力上的负担,也就是不要设计过度,不要让读者拿着觉得费劲,而要是有一种舒服、舒展的感觉。

从2015年最后一期1506到2016年第一期1600,新的版本来得挺突然,像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但其实也是多次实验和试错的结果,“蓄谋已久”,只不过读者大概从未注意过。这两年,原版的《读库》如约按期出着,实验和试错却在《读库》出的其他图书上悄悄进行着。什么样的开本规格,什么样的版心尺寸,什么样的内文用纸,每张纸重多少克,就这样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确定了下来。
老六觉得,这一切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原来的版本也不是“不改不行”,相反正是因为还能“继续往下走”,才让他们多了些宽容悠然的时间和空间来探讨各种新方案。
《读库》内在蕴含着的变动的因子,似乎从来没有停过。往更早里说,大概是从老六设立之初就已开始。拒绝一成不变的专栏面孔,拒绝读者们看烦了的熟名字,拒绝那些在百度Google谷歌上一搜就几万条的人事,而是每期每期都去挖掘一些陌生人写的陌生故事,不吝篇幅地把他们放在头几条稿子上。
后来,又鼓捣出了一系列精美又别致的Notebook(笔记本),据说卖得比书还好,成了不少人的伴手礼;鼓捣出了各式各样的书册,其中不乏《青衣张火丁》、《护生画集》这样的“高端”制作;鼓捣出了《读库》的直销网站和微信微博,以至现在每一册书后面勒口上印着四个大得无法忽视的二维码,取代了原先计划经济气息浓厚的“邮购信箱”……
从全部事实上看,《读库》早已是个广义的、量变型的产品。
十年里,老六觉得自己也有些改变。
去年11月,《读库》十周年年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举行。老六一边给员工和读者们放着电影,一边“探讨人生”,总结自己十年来的变化。在读了几千万字别人的命运和故事之后,他开始发现,“自己没那么重要”。
在编《读库》之前,他在报社、杂志社、电视台、网站、出版社都工作过,担任过记者、编辑、校对等各类工种,却突然在36岁那年从石家庄返回北京的大巴上陷入一场“精神危机”,简单来说,就是对这种“一眼望到底的生活”产生了怀疑。
于是,尽管后来即将去一家公司上班,还被许诺了不错的职位和不错的收入,他还是撇下目测财源滚滚的前途跑去编书了——按照他设想中书该有的样子。这就是《读库》。约稿、组稿、编稿等种种编务工作也由他一人完成,一编就是十年。
这个故事流传甚广,多多少少被渲染成了出版界的传奇。但老六实在不愿意以任何方式去重新回顾,一提起就会被他“残忍”地掐灭。“个人选择而已,我不希望这听起来是一个皆大欢喜、大快人心的故事,证明我选对了或怎样。就算《读库》现在很惨,我也不会觉得我当时选择错了。”
“没那么重要”的另外一重表现还在于,他不喜欢被贴上“一个人”的标签,也反反复复在媒体和公众面前自我澄清、解构所谓“孤胆英雄”式的“孤独造书者”造像。“每年六本《读库》是我来编,具体的案头工作是我来做,但不可能只是我一个人。”很多文化人、朋友都属于他的“云编辑”小组,被他拉来筛选、审校。这些夹带着《读库》书稿的人散布在京城各个角落、各个咖啡馆和各个饭局,办公空间从他车公庄的办公室,扩展到无穷大。
“现在的视野更宽广了,但视野不来自我,而是来自于整个平台的扩大,参与到编选、筛选、推荐过程中的人越来越多,给我‘举报’各种线索,告诉我谁谁谁那儿有好稿子。”老六自己也没想到,编《读库》初期,他怀里揣着只够填满最近几期目录的存稿量,但现在能储备起格外丰富的“粮食”,挑拣起稿子来从容多了。
意识到“没那么重要”后,老六想对《读库》做一件事,叫做“去人格化”。塑造了十年的《读库》在他手里有了人格,和张立宪或者老六这个名字紧紧捆在一起,连以前向他狂伸橄榄枝的猎头公司似乎都认定了这一点,再也不打这个“《读库》主编”的主意。
更多人参与进编审工作,《读库》正式团队也由一个人变成三十多个人,“人格化”难免受到些稀释,但老六承认自己还没想好怎么去“去”。“这是一种模糊性的选择,没有一个固定的比例,你不能说就是二比八或是四比六。”
他一直信奉马克思在编《莱茵报》时说的一句话:“一切报纸都应该是独裁制。”“独裁制”和“去人格化”看似矛盾,但老六觉得一点也不:“就像一个人又在生又在死一样,真的有这种两面性。你决定‘独裁’的时候,你要想到它的反面。当你被各种意见冲击的时候,又要保持一种决断的能力。”
当然也有不变的。比如心态,“抱歉,真的没有什么变化”。老六说,当初钱很少的时候,甚至需要向人借钱的时候,没觉得苦得过不下去了或多么悲情,现在“我们有钱了”,却也还是战战兢兢,紧张地处理稿件,不敢有什么懈怠。“这跟我们这个行业有关。原来账面上是三千,现在可能是三百万,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做文化的)意义仅仅是利润吗?不是的。”
生于11月的老六有点爱说自己是“天蝎座”。以为他对星座有关注,他却连连摇头:其实并不信,只是和朋友开玩笑。
不过天蝎座有几个特点倒是和老六本人颇为契合,比如倔强和敏锐。这一点不用看他本人,从他编的书里就能感觉到。2006年正式发行的第一期,头条文章是关于郭德纲的,他约东东枪对郭德纲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贴身采访。那时,郭德纲还没有全面获得他后来的名望,东东枪也还不是微博大V,但他在郭德纲还没红的时候就已经听了郭好几年的相声,堪称不二人选。
不久后,当觉悟过来的媒体铺天盖地报道这个草根相声明星时,《读库》拿出来的是占据了整整76页的长文,离当事人最近的距离,最长的采访时间,最精细的观察,使它和这本新生读物脱颖而出。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周云蓬身上,老六“派遣”绿妖去采访这位盲人民谣歌手,3个月的采访结束后,绿妖成了周云蓬的女朋友,可见交流之深入。
这些传奇故事差不多已经成了口口相传的段子。但让人惊奇的是里面所体现出来的老六看人看事的敏锐度:他总会找到正确的人去做正确的事(包括他自己),然后不惜成本、不计篇幅、不留遗憾——所谓“三不”原则。
相对应的是更加著名的“三有原则”:有趣、有料、有种。为了这三个原则,老六和《读库》把很多人们早已习惯了的文体拒之门外,包括学术文章、文学作品、艺术评论、个人感怀等等。这样划出一条线来,萃取出来的却是活的故事(现在有个更准确流行的说法,叫做“非虚构”)。
老六和他的朋友们曾经盛赞过一篇马宏杰写的《刘祥武相亲记》,讲一个湖北青年农民在“传后”需求下的曲折相亲经历,故事后面隐藏着一个普通中国农民的善恶观念,以及他和这个世界打交道的方式。
老六文化圈子的朋友很多,用这些名字来填满《读库》的目录,完全不是什么难事。但他坦言说,现在跟朋友们约稿其实不多,因为读库不希望做成一个圈子式的东西。每次的头篇文章都是些素不相识的作者,通过种种渠道到达他面前。“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用表面的花哨和热闹来掩盖内心的贫乏和单调,希望《读库》是真正能带来新鲜感的”。
十年来,《读库》从内到外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气质和风格,和它背后老六的“稳定”有关。从三十几岁到四十几岁,“老男人”气息依然浓烈,但这种浓烈又是用平淡、平静的方式一个字一个字地铺陈出来,并一个字一个字让读者建立起了信任。
然而,站在十年的节点上,老六自己却说不清他在漫长时间里所从事的工作应当怎样去给予回望:“这件事模糊性很强,做出之后,你都总结不出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的动机是什么。你总结了五条十条,但真正的动机可能是在这五条十条之外,这就是这种智力活动的微妙的地方。”
“把书做对”。不光是“做好”,而且是“做对”。这个“对”的内涵很值得咂摸,也让老六在很多人心目中以一个图书手工艺人的形象出现,浑身洋溢着一种工匠精神——尽管老六在媒体上反复强调《读库》是工业化成功的结果,出版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行业。
这或许是相比起流程,人们往往对老六编书的细节更倾向于印象深刻的缘故。从2006到2016,老六一直在写着编辑手记和杂感,仿佛对过手的文章和书都珍而重之,年末之时要再重新反刍一遍。甚至是笔记本——2007年,老六头一回做了两个小册子,作为礼物送给全年订户,用的素材其中之一是设计大师张守义的插画。
他设想的颜色是青底橙字,但无奈订购的纸显示不佳,只好把字换成银色,这让他耿耿于怀不能容忍,于是从册子甫一诞生起就打算“穷兵黩武”一把,寻找重印的机会。后来,他果然得以按原样重出,报一“纸”之仇。
2013年,《读库》推出林海音的经典之作《城南旧事》。这本书早已版本无数,但在台湾格林文化公司见到的有“最美插图版”之称的关维兴插图本《城南旧事》,依然让老六禁不住“色心大动”了。这本书被老六做得极为精细,内文的校勘、注疏,形式上的用字、用纸、印装,都格外讲究,光是书名题字,就提早在心里备下了三个人选的预案。
因为书中涉及许多北京风物,老六还找来古建和方言发面的专家一起来做了一份《<城南旧事>名物考》。
老六的细致匠心总是体现在一些细微之极的地方。“比如用纸,有没有人平时关注不同的纸质,甚至翻看一下《中国纸业》杂志?我前段时间听说一家纸厂有了新纸,是印军用地图的,没有横纹和纵纹之间的不同抽缩率,就留心上了,买一本用这种纸印制的书看看。”
他把他编的书比喻成一棵棵树,而他自己就像是园丁。“很难说会和哪棵树保持长久的关系,但是他打理的苗圃却是一辈子,这个需要浇水了,那个需要剪枝了,有的果实成熟需要采摘了,有的尝尝觉得还有点生,要再长长……每棵都是自己的孩子,都充满感情,不可能说永远困在一棵里。尽量把每一棵树服侍好,并不是每棵树都适合你养,也并不是你有机会来服侍每一棵树。把自己眼前的、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好就行。”
惊人细致的执行力,敏锐的嗅觉,专业的精神能给一个编辑以在行业内安身立名的资本,也会给他适应工业化的保证。换言之,一个有着工匠精神的编辑,为了创造出好的产品,往往会更为恪守工业化的行规。从这个意义上看,“匠人”和“工业化”或许并非决然对立的概念。至少老六总是把自己放在他所身处的行业当中来考虑问题:“这个时代需要专业化、职业化的人,我从事这个行业,希望能够做到让消费者、用户、读者对我们有信任感。”
这似乎也能够解释读库这些年在互联网上的新动作。老六本人对网络兴趣索然,“没那么深刻地分析过”,工作重心还是纸书,但《读库》的网络直营却走在了同行前列。相形之下,一些着急“互联网思维”的传统出版单位倒是没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起色。
《读库》起初只是想逃离图书电商不合理的“压迫”,然而后来却树立起一种新模式,也可看做对整个图书工业产业链的完善。“互联网本身是一个工具和朋友,让互联网介入到纸书的其他环节,包括营销、推广、和读者建立联系等。或许有一天彻底互联网化,我们也不拒绝那种变化。”
很多问题其实老六自己是没太想清楚的,或者应该说是他目前还没有想去想得特别清楚。
比如今年即将推出的“读小库”系列。“读小库”这个听起来有点卖萌的名字,是《读库》推出的少儿读物品牌。比起市场上同类少儿读物,“读小库”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色呢?老六摇摇头。“每个编辑都有自己对图书的理解,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行业。有的书我觉得不出不行,不出就要出人命,但别的编辑可能会觉得不值得一出。”说完他又补了一句:“正是因为大家有这么多种选择,才会有千姿百态的图书市场。”
又比如读库团队现在的三十多个人。老六喜欢把90后称作“小朋友”,《读库》现在有好几个这样的“小朋友”了,最小的一位是95年的。有没有想过专门去为90后做些什么产品呢?老六还是摇摇头,他的团队里出现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不是“刻意的选择”,而是“自然流动的结果”。“我不喜欢标签化,比如90后或70后,没有这个概念。”
对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模糊”的行业,不想,大概也算是一种踏实的远见,所谓“无为而治”。顺便提一句,老六还在高群书的电影《神探亨特张》里当过男主角,演一个便衣警察。电影后来得了金马奖最佳影片,老六也差点当了回“影帝”。但他表示,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次,以后也不会“触电”。“它只是我和我的好朋友做的一个东西,恰好是个电影。”其实这句话,在某些意义上,大概也能借用在《读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