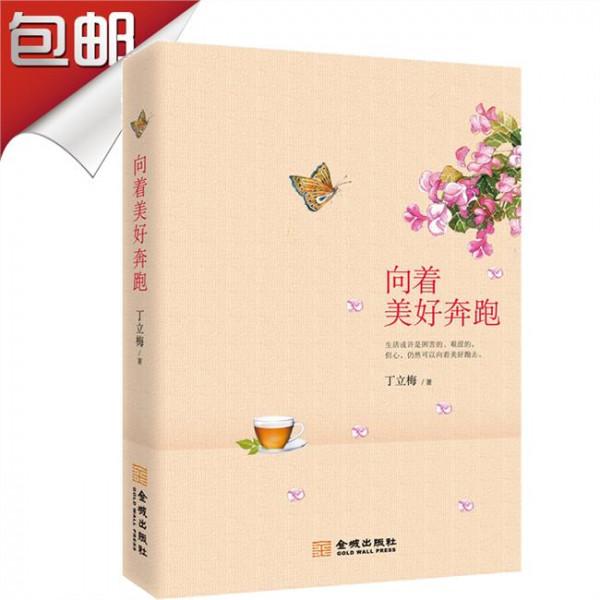【有些爱的句子】【摧残长篇】有些爱注定……(二十)
柏松沉默了一会,叹口气,说何时是个头。我说我们这一代人死了就到头了。柏松说我们才四十岁,还有二三十年要活,文化大革命和后续的影响前前后后夺去了我们二十年的时间,后二十年还要还债的还债记仇的记仇,我们这一代人就不能有自己的生活吗?我感伤地说生不逢时,这就是命。

柏松走了,我哭了,为我们之间纠葛的结束,为我将要孤独一人度过的下半生。哭了一天,眼红肿地回到住处,还是不想吃饭,进门就躺下了。
夜里十点多钟我还睁着眼看天花板,母亲也没睡下,轮椅走动声在屋里响着。我知道她也是睡不着的,这四天我慵懒着,也没搭理她,吃喝拉撒睡她都自己做着。我不知道她坐在轮椅上是怎么收拾一切的,每天进门的时候我虽然不说话也不看她,但我会深深吸口气闻气味,发现不对劲我就会去收拾。可每天闻到的气味很正常,我也就没有行动,我在下意识地“报复”母亲。

轮椅走动声终于没了。我半醒半睡了几个小时就天亮了,起床来头很疼身子也重,真的病了,我却不能再休病假了,咬着牙也要去上班。刷牙的时候突然感觉牙膏很恶心,控制不住呕吐起来。胃是空的,吐出来的都是酸水,呛进鼻子里去了,一下眼泪鼻涕也来了,嘴里还哇哇地吐着。动静很大,惊动了母亲,轮椅声朝我响来,不想给母亲找我说话的机会,我极力想控制住自己,可饿了几天的胃失控了,不停歇地痉挛起来,我就不停地作呕。
母亲靠近,看了一小会,低低地问,“怀孕了?”做母亲的是不是都这样敏感?我有点厌恶母亲的猜疑,想呛母亲一句,可我说不出话来,还在恶心呕吐中。母亲要我快漱口把嘴里的牙膏沫子洗掉,我照做了,稍好一点,但胃还在小翻腾。
洗了脸我忍住恶心,急忙去找饼干盒。我平时都会为母亲准备一些饼干,防止我有事回来晚了母亲饿着。找到饼干盒时它已经空了,我很失望地看着饼干盒,对母亲怨恨的心减轻了一点,原来这几天母亲都是靠饼干充饥。如果我今天再不搭理她,她就要饿着了,这也许是天意在告诉我该原谅母亲了。
决定上班前去买些饼干和菜回来,中午就开始做饭恢复正常的生活。想着心思忘记了眼前,胃也不闹腾了。我穿外套准备出门去,母亲喊住了我,我转过身看着母亲,母亲从荷包里掏出几颗糖朝我递过来。
我迟疑接还是不接,母亲柔柔地说吃几颗糖压压吧。一切回到我小时候,母亲温柔,糖块诱人,我的泪水又弥漫出来。我贪恋儿时的幸福,朝母亲走过去,朝母亲手里的糖块走去。接过糖,母亲拿糖的手空了,那只手又柔柔地捏住我拿糖的手,轻轻地问是怀孕了吗?
很想知道母亲在乎什么在意什么敏感什么,我真的怀孕了她会怎么处理。我不作回答低下头去,给母亲一个我真怀孕的假象。果然母亲信以为真了,她声音颤抖地问几个月了,我低着头还是一言不发。母亲心痛地说难怪那个人敢上门来求和,原来是胜券在握了。母亲的语气有些激动,但还算平和,我等着母亲下面的话。
估计母亲也在想对策。沉默了十几分钟,我就乖乖地站着等着。静静等待的十几分钟里,我内心是无比活跃的。我想的都是母亲网开一面答应我和柏松复合,想的是母亲叹气后反来劝我和柏松好好过日子,不计较他姐姐们了。人总是在节骨眼上才能明白自己想要的,我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发现我的期望是想和柏松生活。
母亲终于开口了,第一句话说出来差点把我的胃又刺激得翻动起来。
母亲说做流产去。这就是母亲的决定,母亲还是要隔断我和柏松,不惜残害一条小生命来达到她的目的。我很失望地问母亲弟弟的死让她不痛心吗,母亲的泪水也在眼眶里打转,母亲说痛心。我说我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杀死他我也会痛心的。如同我肚子里真有孩子一般,我被母亲的决定伤心得无以言表。
我痛哭起来,质问母亲恨草菅人命的人,自己怎么也草菅人命起来。母亲说孽种不能和其他孩子一般等同。我说如果她答应柏松的求和,我和柏松结婚了,我肚子里的孩子也和其他孩子一样了。母亲说柏松家的孩子都是孽种,和结不结婚没关系。我说我筱冬妹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是孽种了?柏松也没做杀人放火的恶事,他的孩子怎么是孽种了?
我和母亲为“莫须有”争吵起来,母亲态度很决绝,我也越来越坚决。最后我摔门而出走了,没有买菜也没有买饼干,没有回去做饭,下班也不想回去,走到远远的街头去坐着看月亮。
母亲是没生活自理能力的,两三天自己还可以应付,时间久点就卡不住了。她也想说服我快点去做掉孩子,就电话把两妹妹叫来了。两妹妹赶到苏州来,去绣坊找到我,然后给我请假,拉回住处,我们四人面对面来“谈判”。大妹是清清白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她和母亲一个立场。小妹妹年纪小,对文化大革命的记忆模糊,对家里的深仇大恨也没什么切肤之痛,所以她的态度是中立的。
我们的话题又从柏松和他四姐谈起,都是老话重谈。我坚持对事对人,母亲和大妹妹坚持蛇鼠不可能同窝,同窝的就是同性格的。我说好吧,我不和柏松来往,但不能要求我做其它的事。
母亲说一定要做掉孩子,那个孩子就是条小蛇,我说我愿意做农夫,愿意被蛇咬。大妹妹说没结婚生下的孩子是私生子,大人和孩子都会招口水和白眼的。我说那是母亲不同意我和柏松结婚才造成的私生子,口水和白眼母亲要承担一部分。母亲说如果孩子不是柏松的,是任何一个男人的,她什么都愿意承担,如果是柏松的,她什么都不会承担。
我笑了一下,说世俗的东西不是谁想承担就承担,不想承担就不承担的,孩子生下来,走到哪里去都是姥姥的外孙,脱不掉干系的。母亲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反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做。母亲说因为爱我,我赌气说我所做的一切也是因为爱。母亲问我还爱她吗,我同样反问母亲希望我幸福吗。谈话再次陷入僵局。
小妹妹先是劝母亲放手,不成,又劝我放弃,我同样不松口。小妹妹急哭了,说大风大浪都过来的一家人怎么不能好说好商量了?小妹妹的哭声又唤起我们共同的回忆,是啊,大风大浪的时候都能同心协力,都能牺牲自己保护家人,现在风平浪静了却不能和平共处了。
母亲语气缓和了些,对我说她的反对是为我好,柏松不是我值得依靠和托付的人。我问为什么,母亲说是直觉。这样的话语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也有直觉,可我的直觉是柏松对我是真心真意的。
说服不了我,母亲妥协了,说我执意要生下孩子,和柏松结婚,她就不拖累我了,她和两妹妹过日子去。母亲说这话的底气是不足的,两妹妹也没接话。两妹妹都是和公婆住一起的,不可能接母亲去同住。还有老宅子的分配也让两妹妹心里不舒服着,虽然她们没说过,但我看出来了。按照祖辈的习俗,母亲名下的财产只有和母亲姓的子女能继承,也就是我和大哥两人是继承人。母亲也多次说大哥不回来了,老宅子就过户到我名下。
内心里还是爱母亲的,不想把她挤到旮旯里去。再说柏松也离去了,估计他彻底死心了,也没必要为“莫须有”闹得家无宁日。我松口了,无限伤感地说我就享受着母爱过完残生吧……(待续)

![心怀感恩与爱同行板报 [心怀感恩与爱同行]学会关爱 心怀感恩](https://pic.bilezu.com/upload/e/fe/efef7f30108fe1f160818f642c2dd7d5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