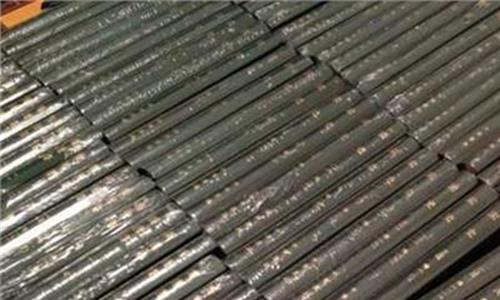元史与新元史
2018年10月11日,上海古籍出版社举办了整理本《新元史》座谈会,邀请了复旦大学的姚大力教授、傅杰教授、蒙元史青年学者邱轶皓,上海师范大学的虞云国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教授,以及本书整理者黄曙辉先生、李伟国先生一起围绕柯劭忞和《新元史》进行了讨论。

整理本《新元史》
柯劭忞“半路出家”重写元史
“二十四史”是对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加上后来的《清史稿》即为“二十五史”,其实,早在此之前,开明书店在民国时就出版过一套《二十五史》,除二十四史外,另一部被收入其中的就是《新元史》。

《新元史》的著者柯劭忞(1848-1933),字凤荪,又字凤笙,别号蓼园,山东胶州人。清同治九年举人,光绪十二年进士,曾任翰林院日讲起居注。宣统二年选为资政院议员,出任山东宣慰使,兼督办山东团练大臣。民国三年,选为参政院参政、约法会议议员,均辞未就。
任清史馆总纂,又代理馆长,纂修《清史稿》,总阅全书。《新元史》是他个人的一部重要著作。姚大力教授在座谈会上就这一点特别肯定了柯劭忞在史学史上的地位,他说,二十世纪初期有三部旧式史书,《清史稿》之外的两部,一是《新元史》,一是《元史新编》,这两部元史都是后代学者以一己之力重写过去的历史,延续乾嘉学派的传统、舆地之学的路径,成就中国史学编纂史上旧史书之绝响,而在这三部著作中,柯劭忞可谓占了一半之功。
柯劭忞一生治学,身兼小学、经学、史学、词章四段。张尔田称他于“天文、历算、舆地、声韵、训诂,靡不综贯”。于经学,柯氏治《穀梁》,有《春秋穀梁传注》行世。而在诗词上,王国维更是称许道:“今世之诗,当推柯凤老为第一。
”虽说《新元史》是柯劭忞的重要著作,但事实上,他四十岁前专力于校注《文献通考》,可惜由于捻军战事影响,稿本全失,这才改治元史。作为一个“半路出家”治元史的学者,柯劭忞为何会选择重写元史?他的《新元史》究竟价值如何呢?
《元史》成书仓促,多有不足。因此,不断有学者补订、考证元史。这大概也是柯劭忞决心重写元史的原因之一,另外,座谈会上李伟国先生提到,柯劭忞认为自己当时再写宋史已无什么新材料,而元史在他看来当时是有一些新材料的,虽然这些材料在后人看来也没那么新了。
柯氏所著《新元史》共二百五十七卷,广泛参考了西方史料和清代钱大昕以来各家研究《元史》的成果,可谓总其大成。所以,书成之后,即由教育部呈送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由他颁令,将其列入正史。章太炎则评价说:“柯书繁富,视旧史为优,列入正史可无愧色。”
《新元史》的尴尬:地位不低,评价不高
据介绍,上海古籍出版社此次出版的整理本《新元史》,以庚午重订本为底本,“退耕堂开雕”初刻本为校本,参校以《元史》、《续文献通考》、元人碑传、文集等,遇有异同之处,凡可判定为《新元史》明显讹误者,适当改字出校,否则以异同校列之,或不出校勘记,以尽量保持《新元史》原著面貌。
这项工作自2012年启动,历时五六年,中间曾因整理难度大,工作推进慢,后在李伟国先生努力复校之下才终于完成。整理有难度,一则来自考订不同版本之间的讹误,二则是《新元史》在总各家之成的同时又将自己的观点、判断杂糅其中而未作说明,所以要辨析起来实为不易。
这一点也是《新元史》颇受批评质疑之处,虽位列“二十五史”之中,史学界却未真正把它利用起来,甚至连一些基本问题在此前都尚不明朗。
座谈会上,李伟国先生说,此次整理本《新元史》搞清楚了一些过去没弄清楚的问题。比如,柯劭忞是什么时候萌生编纂想法的,什么时候搜集资料,什么时候开始撰写,什么时候初具规模,什么时候成书,排印刊刻,什么时候被定位为“二十五史”之一的?虽然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些问题,但已有相当的了解。
座谈会现场
《新元史》未能被学界所重视,最主要的原因是柯劭忞集各家之成,但在引用他人之说和自己的考证之间却没有做明确的说明,以至于阅读、使用者难以辨析。就这一点,邱轶皓在发言中说,虽然《元史》文字粗糙,资料不足,但还是保留了史料的原貌,而柯劭忞著《新元史》虽说是想要补充《元史》史料之不足,但作为私人著说,他集合各家之言,挑拣筛选融进了自己著史之框架,虽说组织严密但反而增加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错误。
傅杰教授说,柯劭忞要做的是自己的史论,对于这样一本著作,如何评价它要看是什么人来读。如果只是作为一般阅读,那么《新元史》不失为一种选择,所以像章太炎不治元史但想了解元史的人对《新元史》的评价就很高,而对于专治元史的学者来说,就是另一种观感了,他说,陈得芝教授对《新元史》的评价就很不高。姚大力教授则说,事实上,对元史有深入了解的人在研究中是不会把《新元史》当作史料来引用的。
如何重新看待、利用《新元史》?
对于《新元史》屡屡遭人批评之处,虞云国教授从史料学角度谈了他的看法,“为新元史的缺点做了点辩护”。虞教授指出,在史料提要、目录学类的书籍中往往提到《新元史》,地位很高,却评价很低,或者很简略的提及,甚至干脆不提,他认为这种态度应该有所转变。
就人们批评《新元史》不重资料出处,学者不敢引用的问题,虞教授认为,《新元史》本来就是另造一史,属著述类,而不是像魏源、屠寄的书,属于史考。所以,人们就这一点的批评恰恰是柯劭忞的史学抱负。
第二,在史料价值的问题,柯劭忞在著述过程中,利用了大量他所能看到的清人成果和二手的西人研究的成果,有其独到的史料价值。第三,有人批评说,《新元史》采纳《元史》等前任成果之时继承了其中的错误,同时自己又有新错,取舍增删,也未尽得宜。
虞教授说,事实上,任何一部颇具规模的史书,都能找到这样的问题,不能对《新元史》太过苛责。第四,有人批评柯劭忞没有在书前说明著述体例的问题,虞教授说,史家著述的发凡体例未必一定要在前面加以说明,而就“二十四史”来说,司马迁和班固是在书前做了说明的,而没做体例说明的也是有的。
第五,有人认为当时已是民国,柯劭忞仍在史论中言“史臣曰”,实在不合时宜。但实际上,柯劭忞本就以遗老自居,不接受国民政府给予的官职,《新元史》避讳时也是避清讳。
所以,就人们批评最多的这几点来说,虞教授认为这些都是可以放在当时的情况下加以理解的。当然,这也不是说《新元史》没有缺点,虞教授在座谈会上指出了两点,一是《新元史》没有艺文志,二是柯劭忞在个别的时间断点上有问题,比如帖木儿推翻察合台汗国,建立帖木儿汗国的时间就值得讨论。
李伟国先生也认为,柯劭忞虽未明确概括体例,但全书结构一遵正史,还是清晰而严谨的。且柯劭忞于宣统初年所作对魏源《元史新编》的评述,也可以看作对《新元史》编例的表达。至于取材的问题,柯氏已在《新元史考证》中作了补救——虽然《新元史考证》内容相较简单,相较《新元史》有疏漏和无法对应之处,但总得来说《新元史》仍旧是有它的价值。
虞云国教授指出,《新元史》是当时西北史地之学大背景下的一个重要史学成果,可以与魏源的《元史新编》、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屠寄《蒙兀儿史记》做个比较。相比之下,《新元史》的价值在于它是另造一史,而且是完成稿,纪、表、志、传都是完整的。
就1840年前后西北史地之学兴起之背景下的元史研究来看,虞教授认为给《新元史》一个中肯评价应该是:它广泛采用了新材料和清人的成果,组织系统较为严密,不能取代《元史》,但有其价值。
虞云国、姚大力
姚大力教授则认为,《新元史》对于重新思考和史实辨析有启发和借鉴之用,并在发言中具体举了三例加以说明。其中一例是关于崖山海战的时间问题。姚教授说,《宋史》中记载的崖山海战的时间是二月六日,大量材料也证明应该是二月六日,但奇怪的是,《元史本纪》中对于这一事件的时间记载完全是错的,记为“正月甲戌”,而《新元史》记载的则是二月七日,修正了《元史》的错误,但与二月六日又差了一天,其中有什么缘故,已不可知,但这个日期应该是有根据的。
而这么一条有价值的改动,在《新元史考证》中却没有体现出来。姚大力教授说,要更好的利用《新元史》,需要重新认识柯劭忞的成就和不足。《新元史》中吸收的新材料,新成果可能是以不大准确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可以利用,又要特别辨析,由《新元史》温故知新,可以求得元史深一层的理解。
傅杰教授也肯定了柯劭忞的学问以及他在《新元史》中所体现出来的史学追求。他还特别指出,在重新看待《新元史》的同时,也应该重新评估柯劭忞。傅杰教授说,近代史学家牟润孙对柯劭忞的学问尤其熟悉,他对柯劭忞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钱大昕之后第一家,但同时牟润孙也说,大家谈柯劭忞都会谈其《新元史》,但实际上,评价柯劭忞的学问不能以《新元史》为标准。
也就是说,柯劭忞与其《新元史》仍需要在史学史、史学研究中被学者们给予重新思考和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