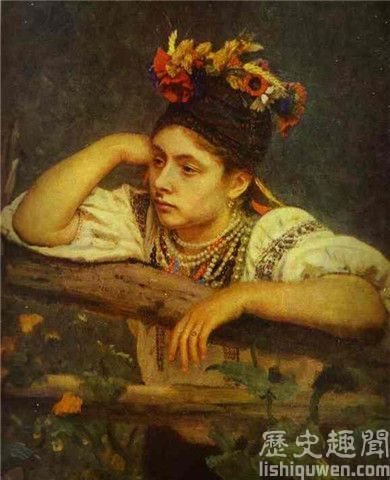【列奥施特劳斯】列奥·施特劳斯到底说了什么?
或许正是由于施特劳斯思想自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遭到的不同诠释和误读,美国正统的施特劳斯学院派弟子才要在最近几年纷纷跳出来为自己的老师正名。刚刚由商务印书馆引入国内,于2006年首次在美国出版的《施特劳斯的真相:政治哲学与美国民主》(The Truth about Leo Straus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American Democracy)就是这么一本正本清源之作。

本书的作者扎科特夫妇(Catherine Zuckert and Michael Zuckert)都曾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在施特劳斯执教多年的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取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现在也都执教于美国著名的天主教私立大学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更都被公认为当代施特劳斯学派的重要成员。

在我个人看来,这本书可以说出色的完成了两个任务,一是理清了施特劳斯本人到底说了什么,尤其是他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关键性评述,澄清了施特劳斯被媒体和一些学者妖魔化的问题;二是探讨了施特劳斯本人的政治思想是如何影响当代的施特劳斯学派的,对施特劳斯侧重点不同的解读是如何造成了施特劳斯学派内部不同派系的分歧的。

关于施特劳斯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他本人几乎从不引用任何当代西方学术成果,更没有像与其背景相似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那样参与当代公共事务讨论(阿伦特和施特劳斯都是因战乱迫害而在二战前夕从德国逃到美国的犹太人。

两人都着迷于古典政治哲学,都曾深受海德格尔影响,还都曾在芝加哥大学教过书,但其政治思想和观点却截然不同),但外界却十分热衷的把他与美国当代政治,尤其是右翼政治联系起来。
在很多人眼中,施特劳斯更是可以被称作是为里根和布什等右翼政客所信奉的“新保守主义”之父。于是,探讨施特劳斯本人对美国的主张和评价就成了研究施特劳斯主义时谁都绕不过去的问题,而《施特劳斯的真相:政治哲学与美国民主》一书就是借着对此问题的探讨向人们展现了施特劳斯的整个思想体系和施特劳斯学派的内部分歧的。
施特劳斯在认识美国上曾有三大看似不能自洽的核心命题,而研究它们间的矛盾关系也就成了理解施特劳斯真正思想及施特劳斯学派的重要切入点,这三个命题分别是:
美国是现代的。
现代性是坏的。
美国是好的。
但凡有一点逻辑的人都能看出这三个命题是不可能在毫无条件约束下同时成立的。那么它们到底对施特劳斯分别意味着什么,施特劳斯又是如何把它们融为一体的,这正是我们下面讨论的关键所在。
1. 美国是现代的:
这可以说是三个命题中最好理解的一个命题。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建国是启蒙主义的产物。它是建立在施特劳斯眼中现代政治哲学的开创者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 所重新定位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上的。美国的《独立宣言》更是自由主义奠基人约翰.
洛克(John Locke)思想的翻版。去阅读美国的开国文献,无论是美国宪法还是为了通过宪法而著的《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这个通用的中文翻译其实是一个错误的翻译),你都会发现美国区别于古代的两个现代性特征,即权利优先于善,制度优先于品行。
我们可以说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政治哲学和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则是在自由主义后启蒙思想的一个极端表现形式,同属现代政治哲学范畴,这点后面会谈到)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以一种善的求索为导向,而后者以权利捍卫为核心。
柏拉图之所以要强调“哲学王”(Philosopher King)无非是因为他的世界里需要一种至善的生活,即对自然真相求索的哲学式生活,并且当这种至善生活的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时,就有了一个《理想国》(The Republic)。
与之相反,现代政治哲学则从根本上否认一种至善生活的存在。它认可或至少是承认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平等存在。正是为了防止不同生活和观念之间冲突和摩擦不至于带来集体毁灭,才要设置出了一个“井水不犯河水”的权利边界,个人权利才成为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
此外与古典政治哲学追寻至善理性,勾勒最佳政体不同,现代政治哲学中的权利还是从人最大的激情和最本能的欲望,即霍布斯丛林中对死亡的恐惧那里推导出来的。从这点上说,现代性的转变本质是一种放弃崇高目标而只去在乎可实现性的转变。
正是由于现代性哲学理念上的权利优先于善,才有了其政治设计上的制度优先于品行。换句话说,既然政治哲学放弃了对善的求索,那么良好政治秩序就不可能像古代共和国那样取决于教育和德性塑造,它所能依靠的就只能是完备制度下的激情的满足。
过去被视为罪恶的人类私心和私欲经由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见的手”成为了效力最大且经合理制度安排可能带来最好结果的积极因素。而美国的三权分立和宪法制约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即用设计上的激情与激情的碰撞让私利去制约私利,从而带来人们物质上的满足和生产力的发展。
2.现代性是坏的:
施特劳斯之所以会选择批判看似带来人类解放的现代性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威胁人类社会发展甚至生存的现代性危机。可以说,身为犹太人,在魏玛共和国长大成人的施特劳斯亲自经历了现代政治的极端病变,即共和政体的消亡和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崛起。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危机就在于其所蕴含的价值虚无、历史主义(Historicism)和实证主义(Positivism)。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取代了对至善生活求索所带来的现代权利观念。而在施特劳斯看来正是这种权利主导的现代性思潮让我们逐渐失去了自身行动和选择的理论支撑。由权利带来的对各种观点和生活不做孰优孰劣的比较表面上似乎带来了一种解放人性的宽容,但实际上这种对价值判断的回避最终只会使得我们无法去论证宽容是一种优于不宽容的价值。
这也就是为什么施特劳斯强调当我们用“权利”二字去把道德政治问题简化为技术问题时,我们就可能陷入了一种可怕的自甘堕落的价值虚无。
由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所开启的第一波现代性思潮很快受到了他们后一辈思想家的批评。但在施特劳斯看来这些思想家本身并未超脱于现代性,所以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只是带来更加糟糕的结果。卢梭(Rousseau)就是这里首当其冲的例子,是他最先不堪忍受一套自我贬损的理论学说,并重新主张我们要重视个人权利外的“德性”。
在卢梭看来,我们不应该像霍布斯和洛克那样在“自然状态”中推导出基于人贪婪自利的“自然权利”,而是应该认识到社会中存在的私欲和嫉妒恰恰是贫富差距和私有财产出现后的历史产物。
因此所谓的“人性”该被归为是独一无二的历史进程的而非自然本身,而正是卢梭的这种历史观念开启了包含黑格尔和马克思在内的第二波现代性思潮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大程度上的价值虚无。
以国人熟知的马克思为例,他明确否认了道德观念的永恒性,并把它们仅仅看成在特定历史阶段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识形态反应。本该超越于人类最本能物质欲望的道德观念在马克思学说中堕落成了从属于并服务于经济利益的工具。
这种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就导致了以尼采为起点的第三波现代性思潮,即除了否认永恒的道德观念(即所谓的“上帝已死”)外连历史的自身发展也不承认,而把历史看成是完全人类创造的结果,成为一种认为我们现在可以去重估过去的一切价值且一切观念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的历史主义。
施特劳斯曾表示每一波新的现代性思潮都导致了现代性危机的加深,并带来了更具破坏性和灾难性的政治运动:第一波思潮促成了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国家,第二波促成了共产主义运动,而第三波则促成了法西斯运动。
3. 美国是好的:
从表面上看,对现代性持否定态度的施特劳斯是不太可能去认可美国这么一个现代国度的。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国内的所谓“施特劳斯主义者”会认为20世纪以来的全世界,无论是当今以西方民主宪政发达国家,还是昔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都是要被施特劳斯所唾弃的。
可事实上无论是在反法西斯主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还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角逐的冷战中,施特劳斯本人都是坚定的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国家一边的。这就引出了他关于美国的第三个命题,即美国是好的。
其实如果我们细致的了解了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批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对现代国家美国的判断上施特劳斯会做相应调整。这种调整当然不是因为施特劳斯是美国人,被爱国主义或者国家主义洗脑让他为自己的国家盲目摇旗呐喊。
事实上施特劳斯之所以总体上认可美国首先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建立在洛克思想,即第一波现代性思潮上的国度。这就决定了在施特劳斯的思想体系中,它是要优于进一步加深现代性危机的第二波和第三波现代性思潮的及其所代表的国家的,即二战中美国的对手法西斯德国和冷战中美国的对手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
美国对施特劳斯的第二个积极之处在于表面上脱胎于第一波现代性思潮的美国在施特劳斯眼中可以用他所推崇的古典话语得到重绘。按照他的观点,用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对多数权力实现制约的美国完全可以被视作一种古典政治哲学中的良好政体,即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一书中所阐述的综合君主、贵族和平民元素的混合政体。
美国的代议制度下的官员选拔也并不是由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批判的古代纯粹民主平等原则,即抽签所决定的。相反代议制选举体现的是古人所推崇的贵族政治正义原则-优绩(Merit),即愿最优者获胜而非绝对政治平等。
正因为此施特劳斯才认为美国的这种自由主义式的民主多少可以从他所赞扬的古典政治思想那找到有力的支持源。存留前现代遗风的美国(这里还包括被施特劳斯所强调的另一古代遗风-宗教信仰)也就被施特劳斯看成是一个大体上还算正面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施特劳斯对美国的这种肯定并不是绝对的。美国的优秀是有条件的,即与第二波和第三波现代性思潮相比的优秀。正因为美国也夹杂着第一波现代性思潮的弊病,施特劳斯才不可能像一些美国的保守派一样把自己的国家说成是一个完美的国度或人类唯一的希望。他也不太可能去赞同小布什式的将民主政治强加于人的威尔逊主义,毕竟威尔逊主义本身乃是他所批判的现代性的产物,是违背他所赞赏的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的。
对施特劳斯关于美国三大命题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帮我们理清了施特劳斯思想的整体思路。它们之间的微妙复杂关系也造就了当代不同派别施特劳斯学派的导向和分歧,而这正是《斯特劳斯的真相:政治哲学与美国民主》一书所讨论的另一主要内容。
按照扎科特夫妇的观点,正是三大命题的紧张关系为各派施门弟子划定了界限和阵营。按照他们在美国地理上的分布,当代的施特劳斯学派可以划分为东岸派(the East Coast)、西岸派(the West Cosat)和中西部派(the Mid-West)。
三大派别分别会选择性的舍弃或不强调三大命题中的一个。与施特劳斯本人相比,东岸派对美国局限和缺憾的指责往往公开的多,即它们不再那么坚持“美国是好的”这个命题。为很多人所熟知的,由施特劳斯最出名弟子,曾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执教的艾伦.
布鲁姆(Allan Bloom)所作的畅销著作《美国精神的封闭》(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就是这一派系最著名的代表作。该书通过讨论当时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来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
与之相反,西岸派则试图回避“美国是现代的”这个命题,从而突出“美国是好的”。由曾在加州著名的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雅法(Harry V.Jaffa)所著的《分裂之家危机》(Crisis of the House Divided)就是反应这一派系观点的作品。
该书试图用苏格拉底与忒拉绪马霍斯的论辩的框架去解读林肯在1858年竞选总统期间与道格拉斯进行论辩时的精彩演讲,从而凸显美国古典哲学的本质,进一步去肯定美国在施特劳斯思想中的正当性。
而缺乏明显代表人物的中西部派与东岸和西岸相比则对施特劳斯思想做了最激进的改造,即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以重返古典而著称的施特劳斯的第二个也是最核心命题,“现代性是坏的”。他们选择用探讨现代政体下的积极因素来减轻施特劳斯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从而实现“美国是现代的”和“美国是好的”两个命题更完整的自洽。
受制于篇幅限制,我不能在这里对《斯特劳斯的真相:政治哲学与美国民主》书中对施特劳斯学派的讨论做更详细的阐述。如果日后有机会的话,还会与大家更多的分享一些关于施特劳斯学派的内容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