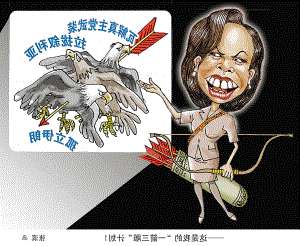京剧高庆奎 论余叔岩、高庆奎、马连良三杰
苏少卿(1890-1971),徐州人。票界名宿、戏剧评论家。字相辰,艺名寄生。自幼喜爱京剧,曾发表过大量有关京剧、昆曲等戏曲剧种的文章。苏少卿对全国名伶名票在艺术上的得与失,大都进行过评论,实为伶人知音。
他主编过《戏剧半月刊》、《大戏考》、《袖珍戏考》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之约,长期主持广播京剧讲座,为传扬京剧艺术做了大量工作。1956年经梅兰芳介绍至北京中国戏曲学校任教,为培养新一代艺术人才勤奋耕耘。

得高君来书,嘱论过去老生三杰:余叔岩、高庆奎、马连良三人唱法,卑人近日为衣食奔忙,无多闲暇,无已,姑略论文。
高君意谓,兹三君者,高志其志,绝不依草附木,去做旦角之挎刀副将,能独当一面,其志可嘉。卑人则言,艺术之评价,不在戏码名次之前后,而系乎自己之真本领。昔谭鑫培先生不得志时,不免唱前三出。再就戏言戏,刘先主微时归附十八诸侯,戴武生巾,穿箭袖马褂,交椅无分,侍立于堂下,关、张是时为弓箭手,又立于刘玄德之侧,盖大丈夫能屈能伸,蛟龙不得水,蝼蚁从旁笑之矣。

马连良之《借东风》
方四大名旦盛时,坤旦继之亦渐露头角,老生一行,遂俯首贴耳,降身为附庸小国,藉糊其口。上述三杰能力争上游,羞为副车,各独树一帜,与名旦坤伶逐鹿,固人中之杰也,但此乃领袖欲之表现。比之商贾,工心计者,喜独资营业,不愿合股而为副理耳,其艺术之高下,固不在此也。

试论其唱艺,庆奎在民五六年问,为硬里子老生,吾观老谭演戏时,亦常见其台上出人,尚无所建树,至民十吾离平时犹然,其独当方面必在民国十年后,挂头牌之十余年间,亦自有其地位,吾听其最后一次为全本《探母》,地在上海,天蟾抑大舞台,不复记忆,是日因取调过高,唱至“弟兄分别十五春”时,嗓忽变哑,勉强终局,再过数年,即因病完全失音,潦倒以殁。

至今常在无线电台听其《斩子》《逍遥津》学刘学孙之唱片,许多人士谓其响遏行云,其实即其毁败嗓音之原因。好似小笔写大字,只见剑拔弩张之势,终至一蹶不振,论其唱工,好大喜功,不择精细,是其弊也。
高庆奎之《坐宫》
余叔岩之唱,无腔不巧,与菊朋晚年之无腔不怪,可谓无独有偶,此皆由于体力、精神、嗓音皆软弱之极,不复能唱谭派刚劲、简练之音调,于是就以仅有之气力嗓音,而一趋于纤巧以媚听客,纤巧妩媚之为音,在旦角尚为下品,万不适用于老生,老生角而笔笔偏锋,是舍正道而入下流,辞将相之尊,而乐打莲花落居卑田院也。
今以其人唱片为证,如《摘缨会》《沙桥饯别》,皆王帽戏,皆张二奎以龙凤之姿,歌钟吕之音,实大声宏,句句中锋,极富丽堂皇之致,令人闻之想见,兴君一派太平景象,二奎以下许荫棠、周春奎、德建堂、韦九峰之徒,尚优为之,老谭貌瘦而声清,所不敢尝试者也。
乃叔岩不自量力,台上所不演者而偏偏收诸唱片,试一听之,只觉一片哭声,呜呜咽咽,君王安慰对方人之剧情,乃惨凄如此,此声尚以中兴之人君乎哉?王帽戏自有此种唱片为楷模。
于是昔日雍容华贵之正声,遂扫地尽矣。不意票友之学余派者,开口即唱此段以鸣取法乎上,习而不察,黑白混淆,此真戏曲声音之大不也。
唱法中原有巧之一字,以救笨拙,但不可纤,纤则穿凿,难免添灭过度之弊。叔岩于巧固有工力,惜少硬扎之音与口劲之调剂,至年愈晚体愈弱,声愈悲全以小腔儿补缀其短。徐凌霄评叔岩晚年之作,谓之“秋坟鬼唱”,一语破的,固盖棺定论,然其早岁之唱,尚不无可取(菊朋早年胜于晚岁百倍,二人正同),亦不可一笔抹杀也。
余叔岩便装照片
至马连良仍活跃于舞台,其唱如何,有目共赏,有耳共闻,兹不具论,一言以蔽之,戏曲为纯粹高尚艺术,断非商品,唱法声音,关系尤大,足以直接影响世道人心,应与金钱钞票绝缘。唱者目的全在拜金,其货色必随花钱人之好恶而变质,吾今正吃酒,请以酒喻,酒肆之酒,务掺水以多赚钱,友朋之藏酿,务出其良者以娱客,其目的不同故也,知此乃可以言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