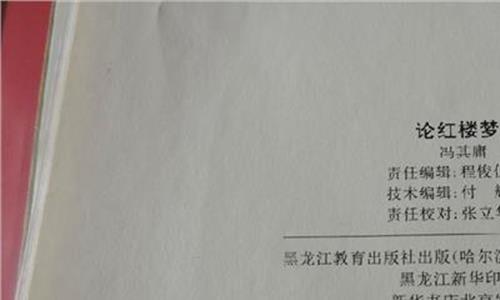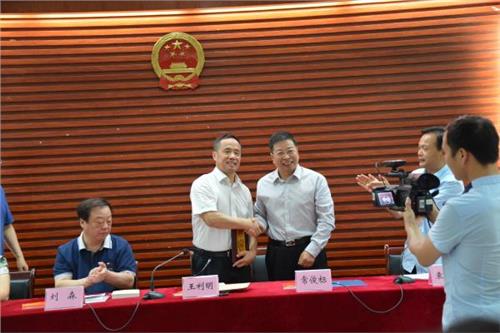【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走进徐正英教授的办公室,就不禁惊叹于环绕整个房间的三面“书墙”,老师兴致勃勃地给我介绍他的藏书,井井有条,这一面是出土文献,那几柜是唐以前的作品集子、古代文学理论,少部分现代人的研究等等。与其说这是办公室,不如说是徐老师的书房,注意到书桌上放着的两个橙色的耳塞,老师笑着说,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这里读书,读书是一种精神需求,一种生存方式,带着耳塞读书心静,这里甚至是他的宿舍了。

一、求学经历——“形势所迫”的最好选择
“没什么兴趣转换不转换的问题,要我说,都是形势所迫。”当问到老师是如何将自己的学术兴趣转移到出土文献的校订和阐发上时,他只是笑着淡淡地这样说。
徐老师是79级的大学生,以安阳地区文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他填报的第一志愿是郑州大学中文系,是他在县教育局帮忙的中学老师发现后在重点大学一栏代补了一个志愿,,时年十九,尚不知道中文系是学什么的,以为可能是让当作家。本科时热衷创作,写过的小说还在学校的创作比赛中获奖,但因为少年时患过流行性脑膜炎,死里逃生,写小说时日夜兴奋总是失眠,导致神经衰弱,为身体故,只得放弃创作。

徐老师回忆在第一次现当代文学的课上,任课教授抱来一大摞书,才第一次认识到,原来文学院并不是教人以文学创作,而是要读这么多的书,教人进行文学研究,去研究别人的作品。于是转向学术,喜欢小说,喜欢现当代文学,可是他的老师告诉他,要研究现当代还必须得有古代的底子。

这才下功夫接触古代文学,兴趣还是在小说,元明清又成为主攻方向,最爱是《红楼梦》。本科毕业时因为导师是研究宋代专家的缘故,毕业论文做的是辛弃疾的闲适词,分配回安阳师专后,仍然教授元明清文学,侃侃而谈自己最喜欢的小说,学生教职工接踵而至,窗边都趴着旁听的人。
后来国家让本科毕业在高校执教的老师进修硕士课程,徐老师又去往复旦学习两年,王运熙先生担任名誉班主任,毕业时论文写作在班里拔得头筹,王运熙先生将他推荐到郑州大学,郑州大学需要六朝文学与文论的教师,于是他离开安阳跟着俞绍初先生做起了《文选》研究,在各地奔走收集资料,为此,又投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曹道衡先生门下访学一年,很是做了一番事业。
又因为郑州大学校长要求60后的青年教师都得提高自己的学历,徐老师不得不准备攻读博士学位。
因为少年时并未学习外语,考大学没考外语,又颇费了一番周折,恰逢西北师范大学设立古代文学博士点,半年之内突击日语,得偿所愿。博士导师赵逵夫先生是先秦文学的名家,赵先生要求自己的学生都跟着他做'子'的研究,徐老师觉得自己先秦底子欠缺,在'子'的研究上实在做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怎么办呢?只好另辟蹊径,终于找到出土文献这一领域,既不脱离先秦的范围,且很少人从文学的角度去研究挖掘,老师于是又下大功夫学习甲骨文、铜器铭文、文字学,博士论文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有关出土文献中文学思想的论文,都很有学术价值,多篇被学术期刊转载收录。
“要说兴趣,那还是小说,但是搞先秦研究,应该是最适合我的”。徐老师说,他的这条路是倒着来的,从现当代到元明清再到唐诗宋词然后魏晋、先秦,最后发现先秦的思想著作才是基础,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原创和根,最好的治学道路,应是先有这个“根”再顺着往下延,童子功必不可少,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之后时段的文学现象及其思想源头。
二、学术的路——“读基本的书、解决基本的问题”
现在徐正英老师的主攻方向是出土文献的研究,对这些文献中涉及文学的方面进行考辨和阐发。徐老师介绍道,出土文献的主要特点和优势就在于它们年代早、真实性强,当然这是与传世文献比较而言。传世文献本就有年代越近资料越丰富,越久远越匮乏的特点,尤其先秦,传世文献数量很少,而且难以判断其真假,所以出土文献起到的是很重要的补充作用,而且其作用也主要是辅助传世文献。
因为就数量而言,出土文献(敦煌文献中的佛经除外)所有的加起来不过5000万字,而传世文献则有22亿之多。所以对于先秦时段的文学研究,二重证据法(即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结合)是很重要的研究方法。
就算到研究生阶段,大多数同学还是无法十分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一个有志于古代学术研究的青年学子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兴趣点呢?从哪里入门又如何坚持?正如徐老师在谈到自己的求学经历时说的那样,就古代文学,甚至就整个文学学科来说,最适宜的路,是要从最基本的书读起,从先秦经典、诸子百家起步,读这些著作,然后就像一条顺流而下的江河,自此发源,延伸到后世丰富的文学现象,才算是有了根基,也不至于做出仅仅浮于表面的东西。
对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徐老师一直坚持“读基本的书,研究基本的问题”,这也是他对急切求知的青年学子们的良好建议。话虽简单,但却具有能够拨开种种浮躁和泡沫的力量,让有意于探究文学问题的人,沉下心来,落脚于那些与我们的传统真正相关,真正有益于学科的领域和关键点。
以上是比较宏观的建议,再具体一些,当你能够静下心准备进入自己的那片学术领域后,最好的选择方法,就是“排除法”,把不适合自己的排除掉,不仅学术,职业的选择也是这样。徐老师笑谈,“我当然明白自己不适合做官,不适合做生意赚钱,所以把它们就都给排除掉了……”当选择做好了,真正地开始做学术、做研究,就不能仅凭着兴趣,“坚持”是最最必要,第一步很难很难,走在途中遇到很多的阻碍折磨以后,还能不忘最初走出来时的坚定决心,继续向着那个期望中的目标前行,才尤为可贵。
徐老师说的时候,仍然面带着微笑,随手撩撩头发,眼镜又快滑到鼻尖,好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笔者知道,这才是如金子般学术的本心与寻常。
文学之于生活——“无用乃大用”与“愚不可及”
笔者曾在本科选修徐正英老师的课程,在第一节课上,老师跟我们聊起文学,他说“文学,无用乃大用”,那时他眯着眼在黑板上写下这句话,然后良久沉默,之后是否有解答,有些遗忘,但是这句话却成为心底一个时常浮现的疑问,这次终于有机会再向老师讨教。
徐老师举了一个叶嘉莹先生的例子,就拿小孩子的教育来说,那些标语口号,永远不会让孩子知道他为什么是一个中国人,只有传统的文化熏染,特别是古典诗词,才真正地能够深入人的内心和气质,让他有一颗敏锐的心去了解生命的厚重质感。
人的活着,是需要根基的,就像日常生活里每一个人都属于一个“家”,或者都在寻找一个“家”。“寻根”,似乎是一个永恒的命题,那么要是人能自觉到自己的精神需要,他又该向哪里“寻根”呢?往宽泛里讲,徐老师谈到的是存在于文学之中的人类共同的情感经验,从古至今,就像少男少女萌发爱意那么自然,这样的情意总没有变过,而我们便可以在这样的心灵相通中,找寻到慰藉和归宿。
再说得更切实际些,文学里保存了许多可以让我们的国家更有竞争优势的力量,所谓“软实力”,拼的就是文化,文化要往外推,要让别人认识得到,还得往本源上找,比如“孔子学院”,不论它究竟成效如何,至少是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时候,需要“孔子”这张名片。
徐老师甚至说到钓鱼岛的问题,在明清文人的歌咏中,早就存留许多有关钓鱼岛的真情书写,诗歌中对钓鱼岛那样的高度心理文化认同,那么它是我国固有领土还有什么疑问吗?不是中国的又会是谁的呢?这不比官方打几次口水仗更有说服力吗?
谈完这些稍显严肃的话题,徐老师环顾他的书屋,半晌无话,忽的默默说,“有志于做学问就要像孔老夫子说的‘愚不可及’”,笔者有些没听清,又问了一句,老师又郑重地说“愚不可及!”说完又笑起来,搞创作和面上学问可以耍耍才气,玩玩灵性,要做真学问大学问就不能单靠耍灵性了,用最愚笨老实的办法潜下心来扎扎实实攻读基本经典、解决基本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暂时绕过去了,将来还得回来从头补上,做出大学问的人往往不是最聪明也不是第一学历最亮的人,可能就与此有些关系吧,太聪明了,牌子太亮了,就多了优越,少了敬畏。
“愚不可及”四个字闷闷地击打在笔者心上。老师说,这就是他现在的想法,以平常心做平常事,做自己应该做的工作,不做分散精力的事情。说着拿起他正在阅读的书,“你看,我最近正在读《周礼》,很难,但也要一字一句的细细看,细细研读。”笔者只是不住点头。
告别时,夕阳的影子已经落在屋里,桌上是徐老师那副橙色的耳塞,笔者不禁想,就算没了它,这一个空间也总会是安静的。
(文:文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 蒲南溪 图:文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