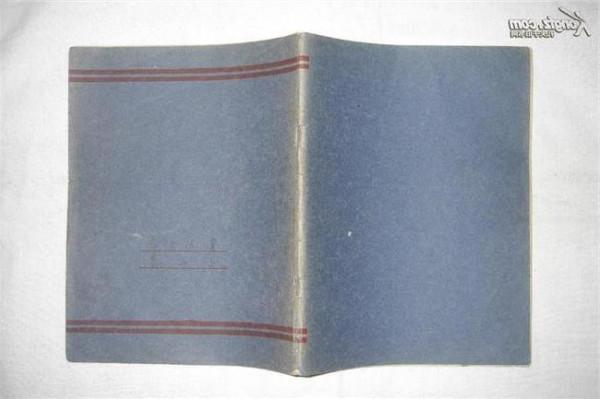【维多利亚整形医院】在弯直之分出现以前:维多利亚时代的性与性别
这是一个堪称典范的维多利亚时代家庭,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不过还是让我们借用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最喜欢的一种文学手法,将本森家的屋顶悄悄地掀开一角,朝里面偷偷窥探一下吧。
这是1853年,爱德华刚满23岁,英俊潇洒,意志坚定,已经开始了一项前途光明的职业生涯。坐在他膝上的是表妹米妮,一个可爱的孩子气十足的12岁小女孩。爱德华刚刚亲吻了米妮,以确定他们俩的婚约。时光飘过40多年,再次掀开这家屋顶的一角,我们发现已是成年人的米妮与露西·泰特(Lucy Tait)一起躺在自己的婚床上,露西是前任大主教的女儿,那时她应爱德华的邀请和本森一家生活在一起。

爱德华去世三年后,米妮和露西搬进了位于苏塞克斯郡(Sussex)的家中,米妮的女儿、埃及古物学家玛格丽特也搬来和她们同住,而且也带来了一位亲密的女性朋友。
至于本森家的男孩子,事实是,这三兄弟都终身未婚。

而与他们同时代的知情者都非常清楚,他们三人对男性存在着十分浪漫的情感,只不过他们在这方面很有可能从未付诸过行动。正如西蒙·戈德希尔(Simon Goldhill)在他那本充满睿智和微妙表达的书中所写的那样,本森一家确实是一个非常古怪的家庭。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给他们的子辈和孙辈们留下了一种沉默寡言、守礼拘谨的刻板印象,将他们从这个印象的牢笼中解救出来是几十年来学者一直忙于从事的一个项目。剑桥大学教授戈德希尔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富有深刻见解的贡献。

但是,当含糊暧昧变成了崭新的前沿事物,对于我们这个性和性别都开始趋向"异端邪说"的时代来说,更能引起共鸣的,正是本森一家能够告诉我们的那些在历史记载以前发生的故事。随着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大量奇事怪闻如今被一一证实,这种关于"同性恋"(homosexual)和"异性恋"(heterosexual)的严格界定相对来说算是比较新鲜的事物:贯穿20世纪晚期性景观的明线为"出柜"(指公开自己的性倾向和性别认同——译者注)提供了二分法的选择。
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在性和性别的问题上,人们的态度更加灵活宽容。在那个时代,如果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产生了浪漫的情感,可以被看作是为将来的婚姻所做的最好的准备。但如果男人与男人之间发生了性行为,则被视作一种犯罪行为(在英国,女同性恋法律是不会追究的),不过几乎没有因同性间激起的欲望而被定义为同性恋身份的个案。
直到1950年代早期,一个男人与另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是不需要认为自己在任何方面"不正常"的,只要他控制好不穿女性化的服装、行为举止不要流露出所谓的"娘娘腔"或"皇后"(皆为对举止女性化的男同性恋的蔑称)模样。
从本森家的屋顶向内窥探的目的,也是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发明现代关于性取向的名词之前,人们是怎样生活的?
在本森家庭发生的所有事情中,最让我们感觉惶惑不安的是爱德华和米妮的罗曼史。米妮11岁时爱德华就决定要娶她为妻,然而在她母亲的坚持下,他同意推迟到等米妮满18岁时才举行婚礼。选择一个年幼的女孩做自己的妻子,爱德华这样做其实是既出于感情又精于算计的:他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筹到足够的钱来结婚,而且这段婚前时间正好可以利用来塑造这个未来的妻子,以让她适合日后他在宗教上的虔诚追求。
至于米妮,正好处于孩子气的少女时代,也急于讨好自己心爱的人。
爱德华向来专横跋扈,喜怒无常,非常情绪化,同时又着魔于细节,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家长。他的孩子都非常惧怕他。"他经常在家里天雷地火似地发作,完全没有考虑过我们稚嫩的心灵能否承受这一切。"他的儿子弗雷德这样写道。
米妮一直忍受着爱德华的蛮横霸道,不断迎合迁就他的野心和抱负,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给他以安抚和慰藉,还经常替他款待大批的宾客,因为这是高级牧师必须承担的职责,只有偶尔几次因为身体不适例外。
但是,在这位大主教的婚姻生活中,不仅仅只有一个顺从的妻子默默支持丈夫的故事,还有更多的事情在同时发生着。米妮与其他女士的亲密友谊屡次发展成为风流韵事,其中有一次与一位霍尔小姐的友谊让她延长了在德国的旅行,造成了与丈夫和6个孩子(年龄分别从7个月到11岁)长达半年的分离。
就算大家都公认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习惯使用夸张放纵的语言来维持女性之间的友谊,米妮写给她心仪的女性朋友的信件仍然是异常浪漫的:"你拥有了我?还是我拥有了你?我的心充满了真挚的爱意,当你我在周四和周五相拥而坐时——当我们紧紧拥抱着彼此,当我们热烈地亲吻之时,"在另一封写给同一位女性朋友的信中,她的语气充满着同样的狂喜:"我真挚的爱人,我最纯真的爱,你看,我就是你最真挚的爱人,是你最纯真的爱。
"
爱德华·本森十分清楚自己妻子对其他女人的渴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个事实。关于这件事两夫妇进行过讨论,彼此之间并没有隐瞒。爱德华曾把米妮抱在自己的膝上,和她一起为这些心灵骚动进行祷告。
"啊,我丈夫因为我而忍受的痛苦,他所承担的一切,他多么爱我,对我多么温柔。"多年后,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而且,确实是爱德华邀请了比妻子年轻15岁的露西·泰特搬来和自己一家生活在一起。为了表达对爱德华这一慷慨行动的敬意,以及对"婚姻中爱情的成熟和力量"的尊重,米妮也努力调和自己对性和精神的双重渴望。
如果"爱是上帝",正如她已经开始相信神的存在,那么激情也应该可以不需要通过身体的实质表达而存在——尽管,正如她自己也承认,只要泰特小姐还躺在她的身旁,这张床就仍然是"她们犯错的领域"。
所有这一切听起来都令人感到困惑,但是对戈德希尔来说,这才正是关键所在。尽管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道德的确定性似乎是绝对的,但在有关浪漫的情感和性的问题上,那个时代仍然允许存在各种的模棱两可,即便是在最受尊敬的家庭中也是如此。
爱德华和米妮的婚姻"复杂纠结、敏感脆弱、体贴又忠诚",正如戈德希尔所描述的那样,但这段婚姻一直伴随着米妮对其他女人的爱。诚然,本森夫妇这段婚姻的复杂性给他们双方都带来了痛苦,而且毫无疑问,父母之间这种错综复杂的感情状态也令他们的孩子们深感困惑。但值得称赞的是,戈德希尔并没有试图去清理本森家族情感状态的复杂局面。
与当代最优秀的传记作家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避开了传记写法的惯例和所谓的确定性),戈德希尔利用自己笔下的主题存在的内在冲突,将读者置于一个极其陌生又极易迷惑的世界中。他没有脱离时代背景将本森一家草率地诊断为一个压抑的同性恋家庭,相反,他将笔墨放在着重描述"在传统生活里,轻松的激情与艰苦的日常之间"能够做到的含糊容忍与包容和解。
尤其重要的是,戈德希尔十分欣赏本森家族在大量出书的同时也具备着既乐于探索又懂得控制分寸的美德,他们的著作中有很多是专门记述自己家庭关系的书。
在本森家族中,阿瑟著有两卷本、长达1000页的关于他那位令人敬畏的父亲的传记,弗雷德著有三卷回忆录和记述母亲在父亲死后生活的书,休写下了自传体的沉思录——本森家族在写传记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热情。
这里列举的仅仅是本森家族出产的大量著作的一部分(亚瑟的日记达到180卷),还不包括他们最能够自由发挥的关于家族生活中各种事件的小说。然而,正如戈德希尔指出的,本森家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们虽然喋喋不休著述极多,但又非常善于在某些话题上保持缄默。
亚瑟长篇大论的传记作品几乎完全没有透露对自己威严的父母的感受,他这样写道:"父亲的心思和想法全都深藏不露,一直隐藏得很好,直到现在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谜。"相反,在阿瑟创作的一本小说中,一个名叫阿瑟的小男孩在一张纸片上写下了"我恨爸爸",然后将这张纸片埋进了花园里。
对于本森夫妇这种纠结恼人的婚姻关系,阿瑟和弗雷德都同样感觉十分费解。弗雷德几乎成功地将米妮和爱德华塑造成了正常的普通夫妻形象,他把父亲向那个11岁女孩求婚的往事描述成了一个真实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爱情故事。
尽管阿瑟也承认父母的婚姻关系紧张,但在他的书中只是避重就轻有所保留地描述了一下,他写道,米妮结婚后,她"开始忧虑自己是否能给我父亲带来他所希望得到的那种爱"。
最重要的是,作为这个家庭的两位主要回忆录作者,亚瑟和弗雷德对与性有关的问题都处理得十分谨慎。在今天,我们给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s)和性别认定(gender identities)分别命名,为的是让生活能够更加自由自在,坦诚已经成了获得解脱的一种方式。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本森一家培养出了一种被戈德希尔称为"极其坦率的间接表达"方式。要理解他们在某些话题上总是三缄其口的原因其实也不难,从他们的回忆录中其实可以发现,某些没有明确挑明的怪异事实始终存在。以亚瑟为例,这似乎是他对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一个恰当的描述,但十分矛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他用了很大的篇幅和很多卷书来描述。
"每个人可能都会认为从这些日记中可以彻底了解我的生活,但事实并非如此。"阿瑟在日记中若有所思地写道,他记录下(但并没有点明)他存放在他的"小心锁好,而且戒备森严的房间里"的写作主题。尽管他详尽地记述了自己与所关心的男人们充满激情的友谊带来的快乐,他还是十分谨慎地守护着他们之间柏拉图式的界线。
虽然他非常享受在游泳池晒成古铜色的身体,但仍然小心翼翼地绕过了任何带有色欲的话题。阿瑟十分困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着"一个被困在男性身体之中的女性的灵魂"。
尽管"同性恋"一词已经流传了开来,但直到1924年,他去世的前一年,他才开始使用这个词语。他是在和弗雷德就这个话题进行了一场理论性的对话之后使用的这个词语,他是这样写的——"同性恋性问题",这样的表达方法让人感觉他对这个词语很不熟悉。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本森家族的选择性缄默,就是了解比亚瑟性格更阳光的兄弟弗雷德的表现。虽然弗雷德活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于1940年去世,是家里最后一个离世的人),他见证了全新的社会道德习俗,但他仍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紧抓着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的遗产不肯放手。
他看到了保持缄默的美德 ——或许更重要的是,还看到了保持缄默的好处。这种做法为一个人的隐私奠定了牢固的基石。没有说出来的和无法名状的,都为行动留下了自由的空间。
弗雷德对自己母亲的婚姻做出的高深莫测的评判是十分有个性的:"如果说她的婚姻是一个错误,那么自从这个世界开始,又有哪一段婚姻可以算作成功的呢?"在他1930年的著作中,弗雷德认为在这个坦诚日渐增多的时代,备受谴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缄默和秘密"需要被捍卫,它们"十分有益但同时又过分迂腐守旧"。
在同一年,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她同时拥有一个丈夫和一位女性情人)表示,她对模棱两可的性态度的日渐沉沦感到悲哀。
与弗雷德·本森不同,她对自己曾经接受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教养毫不留恋,然而当同性恋和异性恋这种二分法确定下来以后,她看出了这种分类方法造成的损失:"人们不断地设法给这种容量极大的激情进行命名和缩窄它的内涵范围,我认为这是绝对错误的——他们总是想给它们钉上木桩,或是把它们用屏风围住圈养起来。"
随着模棱两可状态和中间地带的再次出现,它们看起来不可避免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感受到的有所不同。本森一家写出数百万字的著作,为的是寻觅能够确定性别身份的生命基石。如果他们生活在今天,爱德华、米妮和孩子们一定会登录Facebook,从一个内容广泛的现成清单中做出选择——这张清单从泛性别(pangender)到普通顺性别男性(the plain-vanilla cis man),无所不有——然后再去和一大群"网友"分享结果。
所有这一切的讽刺之处在于,当争取同性恋权利运动被视为对社会秩序的严重威胁时,没有一个同性恋自由主义者会认为这一切是可能实现的。夹在维多利亚时代对待性问题的灵活宽泛与新千年激增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问题之间,20世纪晚期这种直男或同性恋(straight-gay)的基本模式看起来毫无疑问是过时了,甚至已经有点庸俗乏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