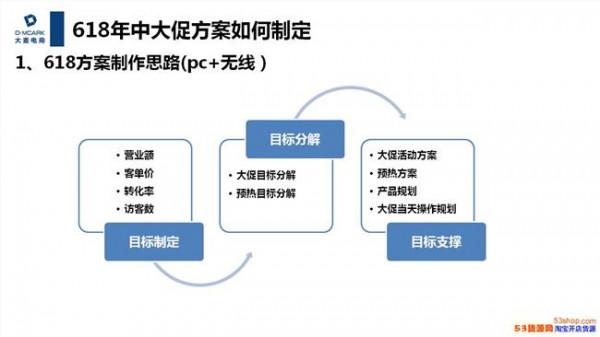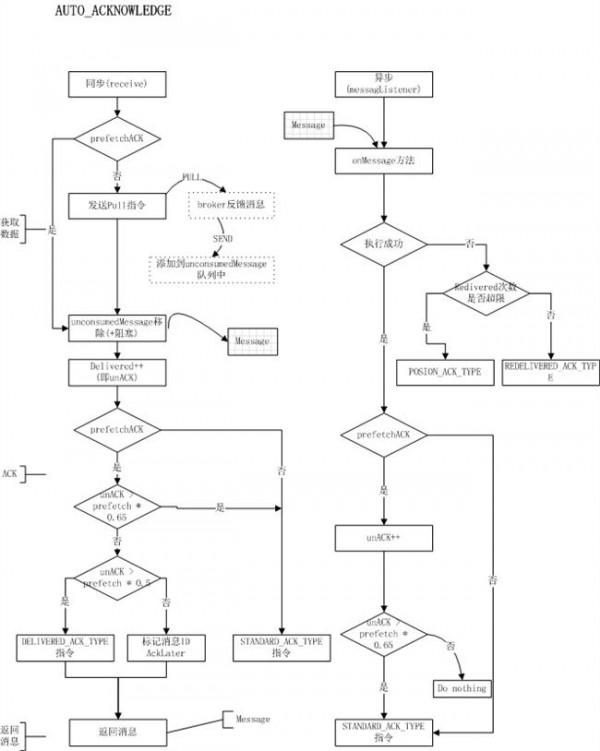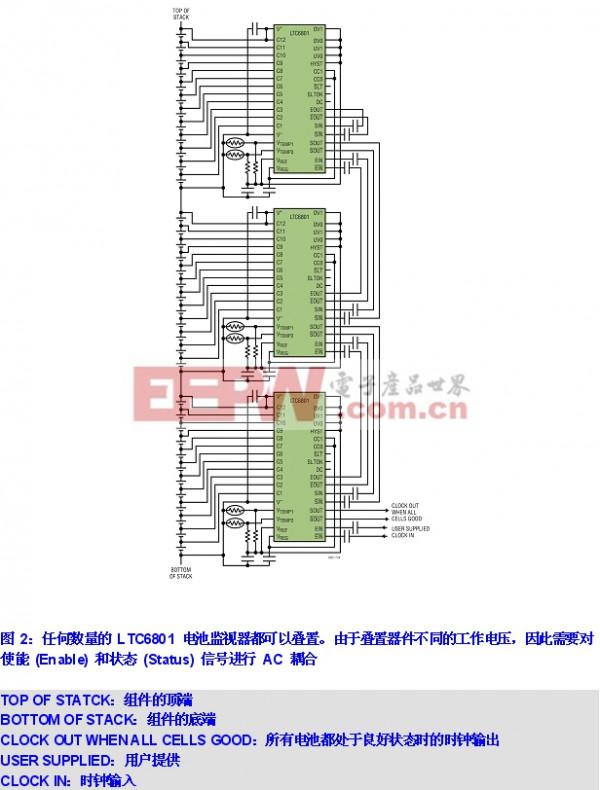我是周赟 周赟:要立法 先问逻辑或方法上是否可能
近些年来,诸如“小悦悦”案等现象真可谓屡见不鲜。老实说,稍有良知的人大概都会对“小悦悦案”中的“路人”感到愤慨、甚至恶心;进而可能也多少会为当下社会的道德滑坡感到忧虑、痛心。人们从各个层面提出应对之策。有人甚至还提出设立“见死不救”罪的立法建议,似乎法律应当迅速介入相关问题,并通过立法——执法——司法一条龙服务尽可能快地扭转相关局面。
记得黄仁宇在研究中国历史后指出,传统中国文化有一种很独特的现象,即凡事首先问的是道德上的好或坏,而不问方法上是否可行;久而久之,竟演变成了凡事只问道德上的好或坏,而压根不问方法上是否可行。举例说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毫不利己、一心利人”就是典型:在这些口号或做法中,言说者就基本只考虑道德的制高点,而对于逻辑上或方法上是否可能的问题就基本没有考虑。
很大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见死不救”的法律规制问题同样具有如上属性。大概没有谁会否认见死不救在道德上的可恶及可恨之处,然而,是否因为它的道德上之不可取,法律就应当伸手管一管此类问题?如果法律要管,它该怎样管?一俟我们进入到该如何从法律角度规制这些现象的层面上,就会发现,所谓“见死不救”——以及其他相类似的道德问题——立法规制就不过是又一种“道德上正确但方法上不可行”之吁求。
法律没有办法让每个人变“好”,它唯一可能做成的事情是防止人们“坏透”、也即“坏”到社会秩序的维续都不可能之程度。法律无法“拯救”社会道德滑坡乃至道德本身。法律面对道德问题时的“无能为力”,早在我们古人那儿就已经得到了雄辩的论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提倡“德治”的儒家还是反对德治、提倡“法治”的法家双方都得出了几乎完全一致的结论:如商鞅就明确指出,“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相爱。
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商君书·画策篇》);汉时桓宽在《盐铁论·申韩》中也断言,“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至于儒家,则更是从来都反对以“法”、“刑”、“政”之类的强力手段来治理国家,因为这些手段所能达致的最佳局面也不过是“民免而无耻”而不可能是“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的良善状态。
何况,在这个韦伯所言之“诸神与诸魔”的现代性社会,法律本来也不应该被轻易用来推广一种或一些道德。何谓“诸神与诸魔”?这关联着对启蒙运动的认识。所谓启蒙,简言之,即用自己的理性来面对、把握、判断并解决问题,并学会不再迷信任何某种先在且统一的权威。
也正因为启蒙运动将万物的判准交由人的理性,因而人们常说启蒙运动“唤醒了人”而贬斥了各种迷信中的“神”。然而,通过启蒙运动,“人”固然从“神”那里解放出来了,但却也带来了这样一种副产品:既然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理性作为万物判准,那么,在很多问题、也许尤其是价值道德问题上,就注定会出现一种多元化的追求。
这样一来,你认为好的东西,可能恰恰是别人认为坏的东西。申言之,你的“神”可能恰恰是别人的“魔”;相对应地,别人的“神”也正可能就是你的“魔”。
应该说,韦伯的这个判断确实深刻地道出了现代性社会的根本困境:因了每一个人主体性的唤醒,现代性社会已经丧失了统一的价值判准。
不难想见,在这样的社会中,某一部分人、即便是一个社会的最大多数人所认定的某种道德或价值标准,从根本上讲也未必一定比另外一部分人、有时候哪怕是少数人的相关道德或价值标准更为可取。在这样的前提下,考虑到国家法毕竟是一种社会公器,因而当然不应、或至少不应轻易被用来推广哪一种或者哪一些道德。
也许有人会说,就算某些地方性或集团性较强的道德确实没有资格获得法律这一公器的推广,但至少“见死当救”这样的普适性道德可以用法律来推广。严格说来,我并不决然地反对法律推广任何一种道德,毋宁说,我反对的仅仅是用法律来推广私德、也即部分私人所认定的道德,而并不反对运用法律来推广公德、也即维护一个社会基本秩序所必须的底线道德。
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一个道德共同体,需要维续某些基本的道德。如果某种道德是社会公德,那么它就可能可以获得法律的支持。
在这里,之所以仅仅是“可能”,是因为此种社会公德还必须符合前文第一个原因中所谈及的另一个条件,即,这种道德可能被法律所推广。因此,就“见死当救”问题来说,尽管它可能是社会公德,但由于法律事实上的无能为力,因而我们当然也就无法苛求什么。
总之,在现代社会中,只有当一个道德问题同时符合如下两个条件时,法律才应当介入,否则,法律就不应介入,这两个条件是:第一,此种社会道德是或至少涉及社会公德;第二,法律正好具有针对它所带来的问题之调整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