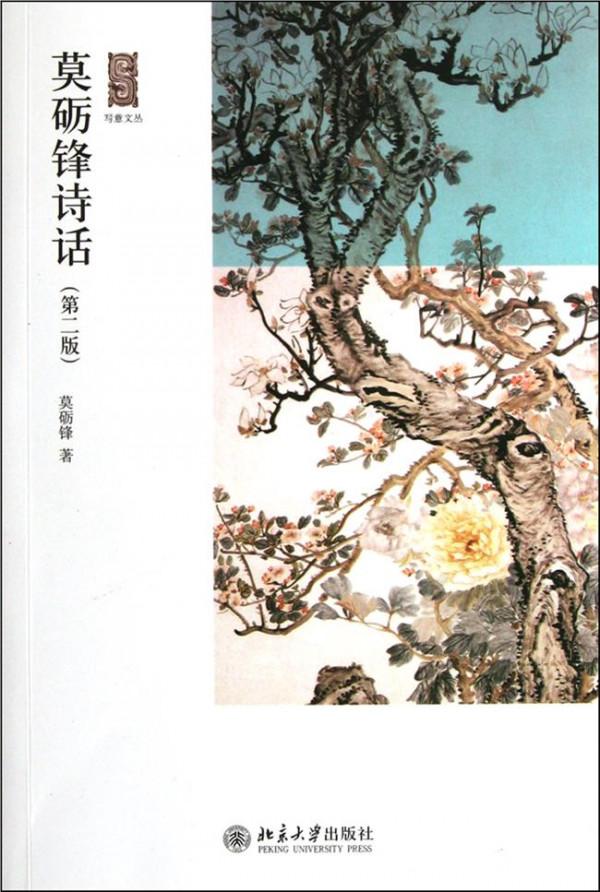莫砺锋于北山 怀念于北山先生
近日正在写一篇关于陆游与杨万里的论文,就把《陆游年谱》《杨万里年谱》二书放在案头,以便逐年比照二人的事迹。论文还没写完,忽然怀念二书的作者于北山先生。于是将书架上的《范成大年谱》也取下来,三书同读,并把论文搁在一边,先写这篇短文。
《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6年9月同时推出的,其实《陆游年谱》初版于1961年(1985年又出过增订版),《范成大年谱》初版于1987年,此次均是重版,只有《杨万里年谱》是首次问世。
至于三书的撰写、修订过程,则前后长达36年。对于三书的学术价值,出版社所撰的《出版说明》说得很清楚:“于北山教授编撰年谱,一改此前年谱纯客观记录之作法,融年谱、评传为一体,关键处不乏自己的评论、分析,体现了学术进步之迹。
”“其篇幅之巨,考证之详,至今无可替代者。”这个评价非常准确,非常到位,我完全同意。正因如此,2007年我收到于先生的哲嗣于蕴生教授惠赠的三书后,当即插到离书桌最近的书架上,以便不时翻阅。
于北山先生出生于河北霸县的一个农家,幼年就读私塾,抗战时投笔从戎。1950年起先后在南京市第九中学、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和南京师范专科学校任教。1962年师专停办,他又回到九中,教授两个班的高中语文。
尽管课务繁重,生活艰辛,但他始终坚持从事著述。请看他在儿子心中留下的背影:“白天无暇写作,都是夜深人静之时,一桌一灯,一纸一笔,于古典文学之沃野,聚精会神而耕耘。
居所并不宽敞,书房与卧室连为一体,夜半醒来,总见家君伏案写作之铁铸身影,总见家君以微笑回答我与家母的劝语。”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里,于先生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从事《陆游年谱》的撰写。此书动笔于1951年,完稿于1959年,1961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出版。
《陆游年谱》刚刚定稿,于先生马不停蹄地开始《杨万里年谱》《范成大年谱》的撰写,于1965年完成初稿并寄给出版社。次年五月,出版社对《杨万里年谱》提出几条修改意见并寄还原稿,让于先生尽快修订后付印。
《范成大年谱》也进入审读程序,原稿则留在出版社。没想到于先生还没来得及动笔修订,一场浩劫突然降临。他在红卫兵的关押下失去自由,家里也屡遭抄掠。要是《杨万里年谱》的书稿被红卫兵发现,肯定会被焚为灰烬,还会成为于先生“宣扬封建文化”的又一条罪证。
这部长达50万字,装订成10册的原稿得以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完全是于先生夫人马熙惠女士的功劳。对此,于先生在《杨万里年谱》的后记中有深情的回忆:“那时,熙惠在家,老病缠绵,只身苦撑灾难。
她猝遇空前浩劫,始而惊疑、震恐,继而冷静下来,善自开脱,以为身外之物,过眼云烟而已。在日日夜夜担心我的生死问题之外,同时暗下决心,保护这部书稿,不忍轻易地让它化为劫灰。
因为她深深知道,我为它经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几年如一日的精神消耗,心血凝聚,是得来不易的。她又清醒地看到:把书稿寄还上海已不可能;转移他处又恐再惹是非。几经考虑,索性把它投掷于走廊上煤炉旁边的火具筐内,覆以破纸杂物,与竹头木屑为伍。
几年中,‘造反派’常是不速之客,呼啸而来,从容而取,扬长而去。但贪婪攫取的目光,却从来不屑扫射这个破筐。就这样,这部书稿才幸逃恢恢劫网,成了我仅存的青毡故物。”
1969年,于先生全家下放到淮阴县插队落户,出身农家的他又回到农家。1973年,于先生到淮阴县中学教书。1978年,于先生调入淮阴师专中文科,总算恢复了与古典文学相关的工作岗位。
此时大地回春,万象复原,从事学术研究不再是一项罪行了。于先生带着兴奋的心情重新开始著述,他赠给本校同仁周本淳教授的诗中有句云“天禄陈编资校理,喜看奋笔答明时”,表明要与后者以此共勉。
于先生恢复了横遭压抑十余年的热情和勤奋,在生命的最后九年中,争分夺秒地对三种年谱进行大幅度的增补、订正。例如早已出版并广受好评的《陆游年谱》,他重写、改写的按语竟多达400余条,真正做到了精益求精。
《杨万里年谱》的原稿在家中搁置多年,字迹已有模糊不清,就在增补的同时重新誊录,终于在其哲嗣于蕴生的协助下最后定稿。于先生在撰写年谱的过程中对古代职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想一鼓作气深入研究,可惜天不假年,竟于1987年遽归道山。已经制定撰述计划的《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与《中国古代官制史》二书未及动笔,成为永久的遗憾。
予生也晚,从未见过于北山先生。《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三册书的封二勒口都印着他的半身小照,红彤彤的脸膛,结实的身板,颇像一位老农。其面部神情也颇似老农,憨厚、和蔼地微笑着,但掩不住岁月风霜的痕迹。
于先生自称“幽燕之士钝如槌”,自属谦词,但也堪称夫子自道。在我看来,“钝如槌”意味着鲁钝、质朴,也意味着诚实、坚强。惟其“钝如槌”,于先生从事著述绝无功利目的,而是发于对学术的衷心热爱。
否则的话,在那个“白专道路”成为畏途的时代,身为中学教师的他何必要冒着风险自讨苦吃?惟其“钝如槌”,于先生治学时绝不投取取巧,而是扎扎实实地下笨功夫,否则的话,三部书稿何以耗费三十多年的心血?惟其“钝如槌”,于先生下笔时绝无哗众取宠之心,而是实事求是地撰写古代诗人的“实录”,否则的话,以先生掌握材料之富,理解文本之透,为何不像时人这般写出一堆“宏论巨著”?惟其“钝如槌”,于先生将曾获前辈学者罗根泽、汪辟疆先生指导之事在后记中郑重道出,否则的话,三书出版时两位前辈早已作古,当年请益之事,除于先生本人外又有何人知晓?……《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合在一起,厚约三寸,这与时下某些动辄“著作等身”的学者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于北山先生生前从未获得任何“项目”的支持,也未获得任何级别的奖励,这与时下某些项目无数、获奖频频的学者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真正推动学术前进的却是前者而决非后者。兴念及此,我凝视着于北山先生的小照,崇敬之意从内心深处油然而起。



















![>莫砺锋诗歌唐朝 97[讲稿][莫砺锋]《诗歌唐朝》](https://pic.bilezu.com/upload/a/fd/afd3dd17c1f9db765269af317a5f94bf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