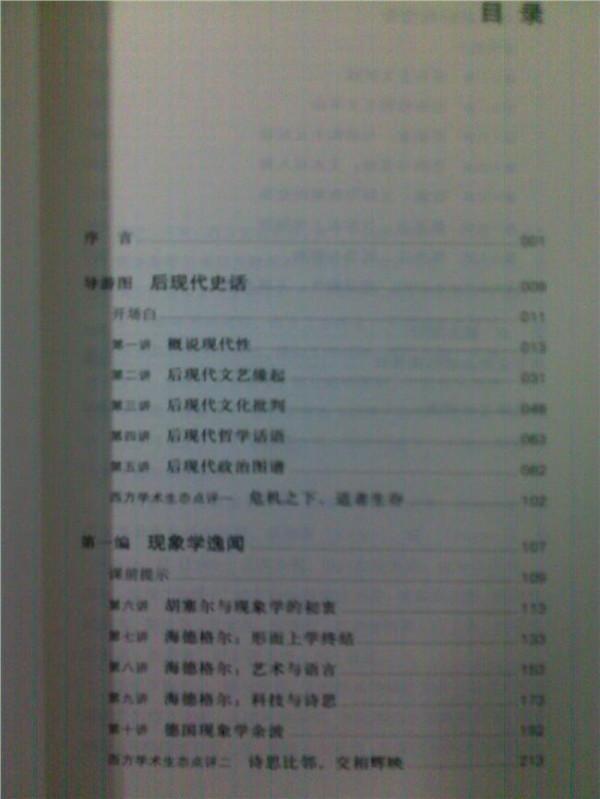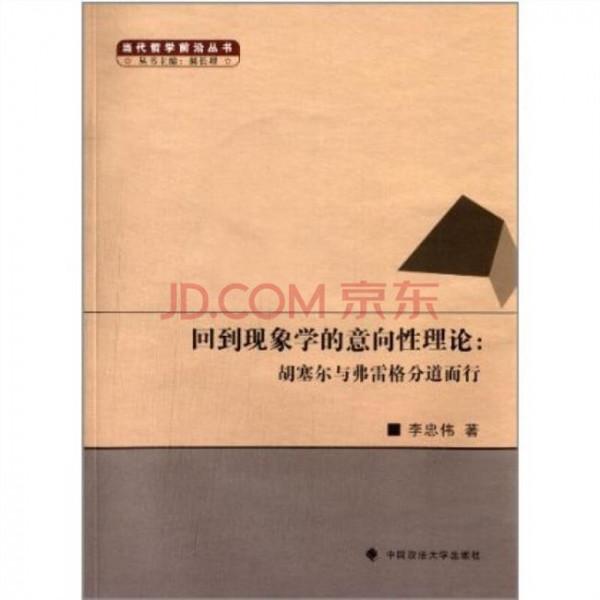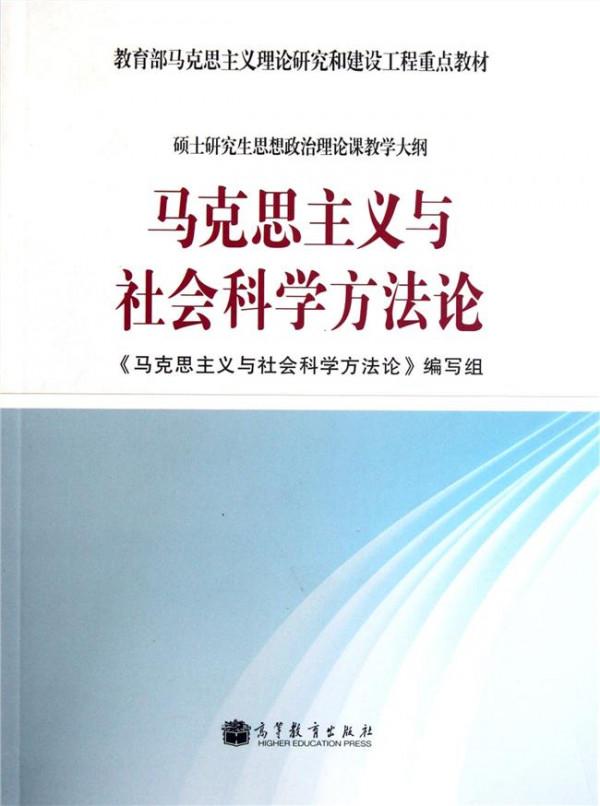逻辑研究胡塞尔 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与德里达的《声音与现象》
张祥龙 今年是胡塞尔《逻辑研究》首卷发表100周年。这本书以及他的随后的一些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引发出了当代欧陆哲学的主流。但是,它的重要与它的难懂不相上下。一位瑞士哲学家燕妮·海尔施说出了这种复杂的感受:“他的哲思太令人捉摸不透,他用过多和过于复杂的语言来表达他对直接性的要求,有时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深刻性呢,还是一种‘模糊性’。
我恨不得将他干脆置之不论。……[但这是]不可能的:胡塞尔对当代哲学以及对各种精神科学的影响实在太明显、太深刻了。
”[1] 胡塞尔的学说确实以某种“直接”的洞见为引导,但他的数学家、逻辑学家的背景,他的“工作哲学”的阐述风格,——对之或可誉为“到事情本身中去”的专注,或可贬为“歧路亡羊”的功夫——使他的思想如大水漫滩,分支纵横而难觅一以贯之的主流。
所以,当代广义的现象学运动中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他的思想弟子中有大成就者无一不是逆其流而上地或通过批评改造这种意识现象学而反激出其中蕴含的巨大思想可能,开出新局面。
顺其流而下者,或较忠实地沿着他制定的研究纲领走的,鲜有不迷失于细枝末节者。创立了解构主义和书写学的法国人德里达(J. Derrida, 1930-)就是反激胡塞尔现象学的一大高手。
德里达的思想是更加引起争议的。一方面,他被一些人认之为开创了一个新的思想时代的大师;另一方面,他遭到了西方“正派”哲学家们的猛烈的、甚至是不够公正的攻击。1992年剑桥大学有意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引来十个国家的著名哲学家们(包括蒯因)的联名抗议。
他们在公开信中抨击道:“德里达先生的学术生涯在我们看来就是把类似于达达主义者或具体派诗人的恶作剧和鬼把戏翻译到学术领域中来。
”“他作品采取了一种拒绝理解的风格。”[2] 我想,如果这些哲学家们认真读了德里达早期的《声音与现象》等书,并且不“采取一种拒绝理解的风格”的话,他们多半不会在这样的公开信上签名,因为这些书表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一些最主要思路正是在与二十世纪最为认真的哲学家之一,即胡塞尔的严肃对话中产生的。
他后来那些似乎怪诞和纯语言游戏式的反叛风格在这里有着很可理解的起源。简言之,同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关系类似,了解德里达与胡塞尔的关系是从学理上真正理解前者的关键。
上个学期(1999年秋季),我在给研究生开的“现象学引论”课中讨论了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和德里达的《声音与现象》,有些感受。在此不揣简陋,试着与读者们分享。
德里达解构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策略是:让胡塞尔自己与自己发生冲突,在本原处暴露出新的可能,从而引出解构主义的关键语词。换言之,他选择胡塞尔学说中的某个交合点,即那既秉承传统形而上学,又包含了较丰富的新因素的地方入手,通过分析显示出胡塞尔的现象学不仅仍然是形而上学,而且是更严格、更直观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并且,正是由于胡塞尔的更直观彻底的方法论要求,使这探索违背他的初衷,暴露了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提供出了新的思想可能。
在这么做时,德里达往往分几步走,尽量减少每一步的跨度,让人感到他最后得出的反形而上学的全新结论正是理应该从胡塞尔的说法中引伸出来的。而这正是《声音与现象》这本书的一个可贵之处,它使人能原原本本地了解解构主义的那些标新立异之说的出处。
形而上学坚持有某种不会改变的自身同一者,它们是世界和知识客观性的保证。结合到以直观的当场给予和构成者为知识源头的胡塞尔学说,德里达认为形而上学的最重要特征就是认定有一种原本单纯的自身在场状态,由它衍生出了、“变更”出了其他的意识方式和存在方式。
《声音与现象》之所以选择《逻辑研究》的第1研究第1章入手,并认为这一章“在严格意义上支配了所有[胡塞尔]后来的分析”,是因为此章对“符号”(Zeichen)做了一个“本质性的区分”,即“表述”(Ausdruck)与“指号”(Anzeichen)的区分,由之而形成了相应的两大系列概念。
表述具有意向及意愿行为赋予的纯含义(Bedeutung),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效和同一的,因而是逻辑的和观念化思想的基础。
独白是这种纯粹的意义表述,约相当于胡塞尔后来讲的“先验意识”。而指号是与时空和物质载体相关的,它可以是无含义的,比如说话时伴随的手势,也可以有含义,比如我们与他人交谈中的话语,但由于时空中介(音符声波)的隔膜,必然掺杂上心理活动。
然而,德里达在这个问题上反驳胡塞尔的主要方式并不像一些人期待的那样是去直接论证这两大系列的不可完全分开或总有所交织(Verflechtung),要是那样的话,他们之间的争论就主要是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而不是形而上学与后现代之争了。
他要论证的是一种更内在贴切的“交织在一起”的状态。
德里达主要是去就表述而言表述,即强调表述也是一种符号,由此而必然与指号一样带有符号的特征,也就是一个可重复的、“替某物而为”(fuer etwas)的再现结构,并以此而逐步去瓦解表述以及与之“共谋”的语音的自身在场的同一性和“自为”(fuer-sich)的结构。
所以,就是在表述中,这种再现结构也不只是“次生的”,而是就处于胡塞尔想为直观单独保留的“原发结构”之中。就此论证是《声音与现象》(以下引用此书时,以《声》表示)[3] 的主要线索而言,此书的第4章是最为重要的。
由此也可看出德里达选择与“符号”直接相关的谈“表述与含义”的第1研究,而不是通常更受人关注的第5、6研究作为解构起点的动机:在这里无论胡塞尔多么想为表述找到直观中的在场的自身同一性,总免不了露出这样那样的破绽,因为整个形势是一个[由于与“符号”相关而]包含着延迟和“再-现”的而不是直接当下“呈现”的局面。
关于表述的具体分析,德里达主要有两条用胡塞尔来反驳胡塞尔的解构思路。第一是认可并深化胡塞尔的这样一个“意义在先”的原则,即表述在被直观充实之前,或实现自己的对象指谓之前,已经具有了意向意义。我们完全可以在不真知表达对象实为何物时而进行表述。
“方的圆”这个表述是“无对象的”,但不是“无意义的”。而且,只有当对象还不在场时而表述已有意义了,这表述才是真正的语言活动。德里达由此推出,意义的原初状态是非充实的、非对象的,当对象在场时,说出的语言反而会失去其原初性。
(《声》第7章)这就是“语言的自由”本性。德里达就是以此来解构胡塞尔更为强调的另一个观点,即意义最终是隶属于对象直观的。按照它,直观、尤其是知觉是一切意义和知识的源头,其他一切意识活动最终都“奠基”于其上。
对于这样一个情况,即当我们读到人称代词“我……”而不知这“我”所指对象是谁时所面对的语言形势,胡塞尔这样看:首先他也承认这时“我”还是有含义或意义的,但他又认为由于不知“我”指谁而使得这个表述形势是“反常的”、“本质上偶然的”。
在德里达看来,正是按胡塞尔本人也主张的“意义在先”的自由原则,我们应该说这个隐匿掉了主体的表达形势是完全正常的。
意义具有类似于“遗嘱”的结构,即总要延迟到主体死亡之后才生效。因此,意义本身包含有原本不在场、不饱满的维度。 第二,为了论证表述独立于指号,胡塞尔用了“独白”的例子(第1研究第1章第8节)。在独白中,我们并不使用实际的语词,而只需要“表象的”语词或“想象中的”语词;因此,在自言自语时,语词完全不起任何指号的功能,我们也并不真正“传诉(或告之)”给自己什么自己还不知道的东西,因为我们自己就在同一时刻体验着这些行动。
换言之,这里自己对自己完全透明,表述与被表述者在当下瞬间完全同一。德里达就从分析胡塞尔讲的“表象”或“想象”的含义入手,很有依据地论证它们的根本意义并非“呈现”,而是“再现”。
这尤其适用于对于符号的表象或想象,并进而用胡塞尔讲的时间构成的结构来反驳他自己的“当下瞬间的自我完全同一”的说法。胡塞尔在分析内时间意识时实际上已经否认了有纯粹独立的“当下现在”可言,因现在总是从根本上与对过去的保持和将来的预持交织在一起的。
但他仍要维持现在在场状态的特权地位,因而认为作为当下原印象的直接变样的保持(Re-tention)与事后对这一印象的回忆再现(Re-praesentation)有本质的不同。
前者还是处于构成“晕圈”中的活生生在场的一部分,后者则是“已经凉了又再加热”的次生的再造过程了。这实际上是将符号化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排斥出了现象学的生命源头之处。德里达认为这两种“Re-” 或“再”并无本质区别,其最有力的一个理由就来自胡塞尔的一个核心主张,即任何意向活动都有一个可被无限重复的核,正是它的存在使得观念的同一性可能。
因此,作为重复的再现是任何意义构成行为,包括时间构成行为所绝对和首要地要求的。
但这也就意味着,上面提到的“替为”结构要先于“自为”结构。请注意,由于这里“再-现”已处于如此原本的地位上,它已主要不指对某个现成者的再现了,而意味着一种原本的不在场与在场交织的状态,一种总以“补充”、“赊欠”、“非自身同一”为前提的原初“结构”。
德里达相信,这样的反驳将动摇现象学和整个形而上学的根基,并由此而引伸出他的解构主义思路。各种“再”的共根是那使重复可能的结构,也就是德里达所讲的“印迹”的构成。
而这也就正是“趋别”(differance,差延)的含义,即在最本源处还势必存在的区别(difference)和拖延(deferring);正是由于这区别(如同索绪尔讲的音位间的区别)造成的动势和拖延维持住了错位与区别,在场和意义才是可能的。
由此可见,“趋别”与“印迹”的本义主要来自现象学的时间分析,由保持结构(或晕结构)和再现结构的贯通而来。所以德里达讲:“与区别不同,趋别指出了时间化的不可还原性”。
又将印迹说成是“保持的印迹”。(《声》130页,85页)在《声》第6章中,德里达说明了语音与胡塞尔追求的形而上学的观念化之间的“同谋”关系。话语之声与书写的不同在于,它不涉及空间中显现的异于我的指号,而主要是一种时间中的当下自我作用。
当我说话时,我的话并不脱开我的气息所及,我同时听到并领会自己所表达的意思,我与我的话语处于一种活生生的自我影响的当下晕圈之中:所以它最适合于体现观念化和主体性所要求的在场的自身同一性。
因此,历史上的形而上学和现象学都要抬高“说的逻各斯”,而贬低再现性或拖延性较强的书写符号的思想地位。然而,德里达分析到,胡塞尔毕竟需要“陈述”,实际上也就是需要符号来表达出观念对象,而诉求于话语或语音的“肉身化”也就势不可当地会引出书写的符号,因为语音的时间化总已是一个保持的印迹,里边有区别和拖延造成的“空间”,必定导向入世还俗。
表述的时空交织和内外交织是原本的。
(《声》第6章最后两段) 而且,德里达理解的书写(écriture, writing,或译“文字”)也不只是一般的物质符号,而应被视为造成趋别的印迹,“这种原书写在意义的源头处起着作用。
”(《声》85页末段)更具体地说,书写就是指那当主体或对象完全缺失或死亡了之时,仍然在起作用的符号。(《声》93页)很明显,这样一个解构主义的中心思路也植根于德里达对胡塞尔的解读之中。 在我看来,《声音与现象》不仅透露出德里达解构思路的精微,善于捕捉和利用对方理论弱点的“猎手” 和“寄生者”的天才,更表明了胡塞尔《逻辑研究》、《内时间意识的现象学》的极深厚的思想蕴含力。
如此晦涩的著作居然能在激发了舍勒、海德格尔、梅洛·庞蒂、萨特等等之后,以“自焚”的方式燃烧出解构的火焰,实在是思想史上的一大奇观。
德里达也受过海德格尔的深刻影响,但是毫不奇怪,他的书写学就是要以胡塞尔而不是他人为对话对象而起源[德里达最早的也是极重要的一部著作是对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一文的解读], 因为胡塞尔的轮廓清晰的两面性给德里达的“借力打力”的解构策略提供了最可利用的发力构架。
海德格尔也强调“在场”的优先,但他讲的在场是主客未分的生成和维持的境域(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已包含了“不在场”),那时还根本没有意向对象之核和先验主体性的地位,也就说不上对于[不同于“保持”的]“重复”的明显的绝对需要。
当然,德里达也批评海德格尔的“在场形而上学”,但那已近乎不同观点、甚至不同语词用法之间的论辩,而不是像《声音与现象》表现出来的那种有内在根据的解构了。
[1] 引自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8页。
[2] 《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232-233页。 [3] J. 德里达(Derrida):Speech and Phenomena (《声音与现象》),David B.
Allison英译,Newton Garver撰写前言,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以下中译文皆出自此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