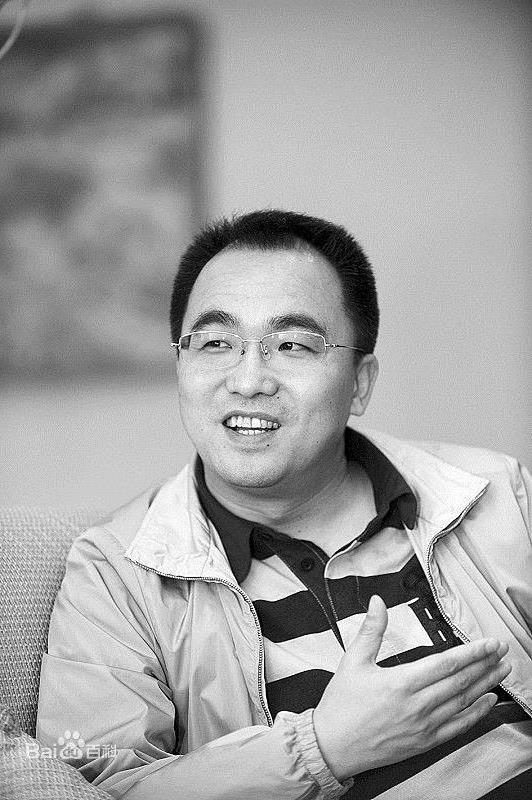阎连科丁庄梦 阎连科《丁庄梦》:他们在苦熬
2006将是文学的丰年,这个预言自然有待读者有待时间去验证《生死疲劳》、《我的丁一之旅》、《丁庄梦》等长篇的质量以及莫言、史铁生、阎连科等作家的能量,但就以刚刚面世的阎连科新长篇《丁庄梦》这部艾滋病题材的小说而言,至少“文学的丰年”已经赢了头彩;不仅如此,当我们细读《丁庄梦》,它于文学、于现实、于过去都有着诸多值得评说的普遍价值,其间的经验与影响亦未尝不可寄于将来。
如果以2006为限观察图书出版,则《丁庄梦》未必是最好的一部小说,但它是2006年第一本最好的小说。
他们都跃过了那块墓石
然而,最好的小说同时未必是好看的小说。阎连科使用一种类似方言的叙述语言讲述北方平原上一个村庄因卖血患上热病(感染艾滋)的故事:秋未的一末,黄昏的秋末……
庄里的静,浓烈的静,绝了声息。丁庄活着,和死了一样。因为绝静,同为秋深,同为黄昏,村落萎了,人也萎了。萎缩着,日子也很着枯干,像埋在地里的尸。
日子如尸。
平原上的草,它就枯了。
平原上的树,它就干了。
平原上的沙地和庄稼,血红之后,它就萎了。
丁庄的人,他就缩在家里,不再出门了。
第一句话其实就定下了整部小说的叙述基调。它是短促的,重复的,拖沓的,不对称的;它是民间的,口语化的,又带有过于抒情的文学色彩,一直延续到全书的最后一句——“新的蹦蹦跳跳的世界了”。考量一位作家的作品,背景、故事、结构乃至年代都是至关重要的,而排在第一的,无疑是语言(叙述)。
对读者来讲,语言代表着最直观的接受能力,对于作者而言意义更为重大,只有选择对了语言才谈得上叙述、故事、结构。《丁庄梦》采取一种咏叹式的叙述方式未必能赢尽读者的芳心,但当我们把整个故事掂一掂——还有比艾滋病这样重大、敏感的话题吗?这已经够重大、够敏感了!
选择一种轻盈的语言来叙述一个沉重的话题无疑是上上之选,换句话说,用任何沉重或悲悯字样的语言都不足以再表达这一题材之重,正如卡尔维诺说的,薄伽丘让他笔下的哲学家跃过墓石摆脱恶少的纠缠(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使得整个故事开阔,继续下去,是为文学品质之“轻逸”,阎连科让他的主人翁丁水阳丁辉丁亮们也跃过了“艾滋病”这块读者心中的大石头,举重若轻,用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来叙述故事。
《丁庄梦》的语言容易让人想到莫言《檀香刑》的精致,相比之下,《兄弟》(上)则是一种高级的、书面语式的外国文学语言。没有比方言更适合这个发生在草根阶层的故事了;尤其是这种“方言”像旧戏曲那样的文雅膛(就是前面说的“类似方言”)。《丁庄梦》里人物的语言,神态,都有戏台上的张致——李三仁便惊着张大了嘴,说“天呀,你让卖血呀!”
张大了嘴:“老天爷,让百姓卖血呀!”
这是中文的艺术的语言,而不是翻译体式的文学语言,如果我们回到“中国的伟大小说”那个命题,首先应该谈的就是作家的语言究竟是不是中国的语言。
藏污纳垢的无辜者
《丁庄梦》是由“我”来讲述的,而“我”,丁庄附近最大的血头丁辉的儿子,12岁,已经被人用毒番茄毒死了——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是12岁的死者,一个躺在坟墓里因人的私欲之争而死的无辜者——而且是并非仅仅因卖血所起的纠纷。
借死者之口来讲故事,似乎暗示了现实的难熬与结局的悲观。和语言一样,《丁庄梦》并未与热病(艾滋)有正面交锋,而是将它作为一个大的背景,转而叙述其他的故事:“一身语文气”的“我”爷爷丁水阳让丁庄人放下包袱走上卖血之路的故事:“我”爹丁辉倒卖棺材,给死去的人配阴亲的故事:“我”叔丁亮与他的兄弟媳妇不伦恋——他们的故事始于丁水阳号召病人集中住到丁庄小学,这一段落占去了全书最大篇幅的第三卷第四卷,这些因为患病住在一起的人,他们制造的故事看起来无关紧要:偷米偷钱偷公章,争权争树争木料……这些故事看起来的确跑题,然而,在第二卷叙述丁庄卖血史时,“我”
死了;第三卷病人们住到一起遇贼时,李三仁死了;第四卷病人们争权夺利时,赵德全死了;第五卷“我”叔和他的兄弟媳妇终于结婚之后,一个有名有姓的赵秀芹死了——就在这里,“我”叔两口子也死了。死亡一直存在,他们在苦熬,同时为自己的一己之欲兴奋不已。
这些看起来跑题的偷鸡摸狗争权夺利恰好证明了走上卖血之路的必然,这些四处游荡的人性之恶,正是我们与艾滋这一重大题材最正面的交锋,至此,这一主题才显露:他们在苦熬,大部分人也是。
而这些段落不仅大气饱满,也直撼人心:丁庄田间地头卖血的景象;血头丁辉在平原上浩浩荡荡卖棺材的景象;配阴亲的景象;坟墓中的叙述者“我”的叙述景象;“我”叔与玲玲的幽会景象——只用了一个字:暖。
叙述者“我”死于丁庄人对“我”爹——血头丁辉的报复,“我”爷爷丁水阳也是一个无辜者——和那些丁庄人一样,是一个藏污纳垢的无辜者。因为听了县上来的高局长的鼓动,丁水阳消除了丁庄人对卖血的成见,当热病流行时,才会有他把病人召集在一起生活,才会有他要自己的血头儿子向全庄人磕头认错,才会有他因棺材、配阴亲的事去质问儿子乃至最后的总爆发。
在丁水阳身上其实始终有一种沉重的罪感,他虽然没有染上热病,但他是丁庄人中最为痛苦的一个:并非所有的灵魂都一个模样,即使藏污纳垢,始终都是无辜的。
《丁庄梦》的第一卷开头是三段《旧约》的文字:酒政的梦、膳长的梦、法老的梦。如果我们解读这三个梦的典故,自然很容易与《丁庄梦》的相关情节对号入座,亦即热病完全吞掉了丁庄曾经有过的繁荣,乃至于获得暴利者(如血头丁辉)都不得善终。
以全书结构看来,这三个梦无疑牵制着全书的节奏、进度和方向。但丁水阳亦非简单的寓言化,他也并非《旧约》中的约瑟,他身上的原罪感其实不同于西方的原罪,他的罪感、痛苦、他的种种赎罪之举,都源于卑微者的良心,这在丁辉贾根柱丁跃进身上早已扭曲。
丁水阳是善良但没有太多分辨力的农民,作者选择让他奔走于全书上下,让他做梦,梦见生死未来,不是为了塑造一个正面的形象,而是正如那些贪婪者是大量存在的一样,丁水阳亦真实存在着。
而同时丁水阳身上亦潜伏着《丁庄梦》值得商榷之处:尽管之前有诸多铺陈,“打死儿子”的举动显得牵强,而在整部小说的高潮之后,包括第七章最后一章、第八卷缺乏应有的从容感——相反是急切地收尾,像急刹车。
说到急切,不得不提到书中尚有多处疑似手笔之误,如马香林误植为丁香林,“我”叔的情人杨玲玲,到死时变成了夏玲玲。
置于时间之中的《丁庄梦》
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你必须把他放在已故的人们当中来进行对照和比较。我打算把这个作为美学评论,而不仅限于历史评说的一条原则。
阎连科在后记里将《日光流年》(1999)、《受活》(2004)和《丁庄梦》相提并论,事实上这三部作品无论题材、风格和故事都甚为接近,但《丁庄梦》更为弘大,而切入口更细致慎重,无论是感情还是技法,《丁庄梦》都是一次大爆发大突破。
然而,当我们将《丁庄梦》放在更大范围里看,其意义并不只局限于它的著者一人身上。与其说艾滋病这一敏感震撼的题材眷顾了阎连科,预示了它的价值影响,毋宁说作者关注当下关注现实的勇气与担当是过于匮乏的。
我们已经见识过太多宏大叙事的作品,亦已有太多不切实际不合逻辑完全不顾受众受得了受不了的文艺作品、文艺腔作品以及大行其道的娘娘腔作品。
《丁庄梦》自有其缺点,或许不一定是读者读了泪流满面交口称赞的作品,甚至可以说,它不会讨得大部分人的好,然而相比之下,它是厚重的,诚恳的,现实的,尤其是它是不折不扣的艺术品。在一个转瞬即逝、即使有太多眼球吸引的新闻题材上延生的文学作品,并没有成为昙花一现式的宣传纪实文章,也没有妄图与现实共谋,合分一杯羹,而且我们长久来看,艾滋病这一噱头会越来越淡,作品本身的纯粹性将会更加明显。
诚然,对任何一个时代而言,文学实质上都只是微乎其微几个人的游戏,但可能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弄潮儿都如过江之鲫,如海选,乃至成为文学的主流,掩盖文学的本来面目。为什么《丁庄梦》会是一个异数?因为它有与大部分海选选手不同的文学品质,也不是好读好看的爆米花作品。的的确确,艾滋病这一题材是时间性的,但借助文学品质,《丁庄梦》这部小说所讲述的故事是超时间的。
当然最为难得的,是《丁庄梦》既有属于它自己的一席之地,又因这一席之地而改变目前的格局——正如T.S.艾略特所言,“当新鲜事物介入之后,那么整个的现有体系必须有所修改”。
这种影响、修改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信心。一针强心剂。久违的现实主义作品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