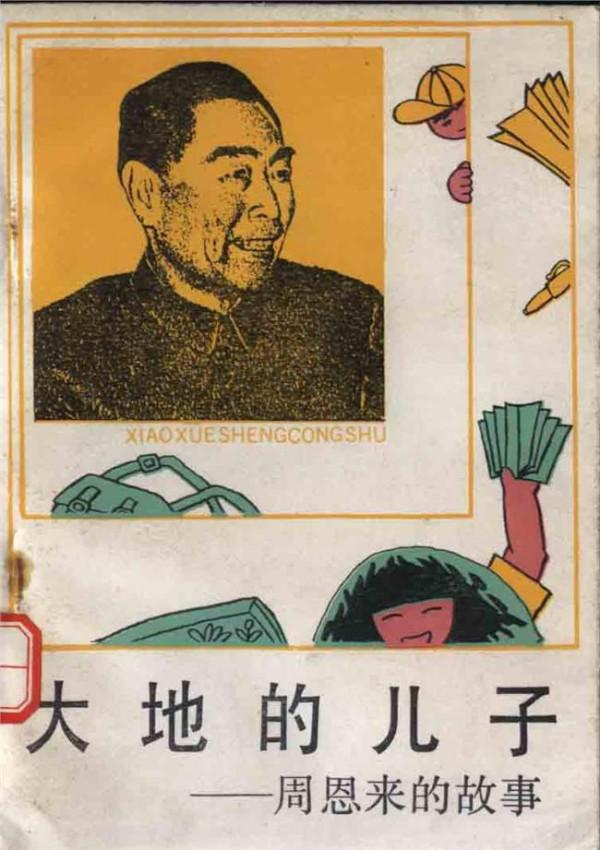赵登禹的后人 七七事变最后的老兵:当年我看着赵登禹将军咽气
70年前的7月7日,日本人在卢沟桥旁的一声枪响,划破了一座城的宁静,激起一支愤怒的军队,更唤醒了一个沉睡的民族。“七七事变”,一个耳熟能详的事件,中华民族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8年。
70年过去了,那些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都已逐渐走向时光深处。当年在卢沟桥的石狮注视下与日军浴血奋战的10万国民革命第二十九军将士,如今在全国也仅剩下7名,而这7部已届耄耋之年的“活历史”,也在渐渐消逝。
时值“七七事变”70周年来临之际,本报寻访了国内最后7位“七七事变”老兵以及著名“七七”将领宋哲元、佟麟阁、赵登禹的后人,意在记住他们的名字,留下他们的记忆,缅怀那段英雄的历史。
李鸿斌
87岁,祖籍山东乐陵县,现居住于南京建邺区文体西村。
1936年年底,初中毕业的他投笔从戎,加入了29军军事训练团。1937年7月28日,侵华日军进攻南苑军营。由于29军对战事形势的错误估计,调动不及,作为宝贵军事后备人才的军训团也被拉上战场,李鸿斌的1700多名同学战友折损过半。
南苑失守后,17岁的李鸿斌跟着队伍往河北固安县撤退。此后,李鸿斌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7期步科,两年毕业后成为国民党军西北军中的一名基层军官。淮海战役时,随部队起义,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李鸿斌一共育有4名子女,现在和老伴生活在一起。
崔金品
90岁,祖籍河南项城,出生于破落的地主家庭,读过8年私塾。1935年加入29军37师特务团,因枪法出众,成为团长张振华的随从副官。“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曾冒着炮火开摩托车到卢沟桥上给镇守其上的219团团长吉星文传达师部命令。后随军撤退到河北保定。
此后,崔金品先后当过77军(由原29军37师改编而成)参谋处徐廷玑处长和77军副军长田春芳的随行副官,还参加过“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枣庄会战”等战役,是目前仍在世的7名29军老兵中官阶最高的。
1948年崔金品随军投诚起义参加陈毅的华东野战军,但终因腿疾而退役返乡,务农谋生,共育有1子4女,现在与九旬老伴生活在一起。
赵金典
88岁,祖籍河南西平。1935年他随乡亲北上参加了29军37师特务团手枪营,负责在师部所在地颐和园大门站岗守卫。“七七事变”中,他曾两次随手枪营护送师长冯治安到卢沟桥督战。29军撤出平津地区后,赵金典先后转战河北、山东、湖北等地。
解放战争时期,不愿帮蒋介石打内战的赵金典卸甲归田。1949年建国后在老家谭店乡和张村当会计,上世纪80年代退休,共育有3子1女。去年一次脑溢血使得赵金典目前行动不便,记忆也渐趋模糊。
张可宗
87岁,祖籍河北南皮,现住重庆市九龙坡区。1934年5月参加29军132师特务团工兵营。“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可宗随军从河间府急行军奔赴南苑支援。7月28日南苑失守,张可宗所在部队撤退至大红门附近时遭到日军伏击,29军副军长佟麟阁及132师师长赵登禹也在此役殉国。其中,赵登禹牺牲前,张可宗一直陪伴身边,并听他留下了“尽忠不能尽孝”的遗言。后来,张可宗在撤退中腹部中流弹受伤。
张可宗随后参加了徐州战役、台儿庄会战等。1949年6月,张可宗从国民党军队退役后辗转到重庆,1949年建国后靠做一些小买卖为生。改革开放后做过个体户,开过小工厂。共育有3子2女,现在生活贫困,和老伴靠低保过活,且体弱多病。
孙敬生
93岁,祖籍河北藁城,现住天津市河西区。参加29军前曾是一名小学教员。1935年,孙敬生投笔从戎,加入29军37师109旅217团机枪连,驻扎在保定。“七七事变”爆发后,孙敬生随217团奔往长辛店支援正与日军激战的219团。敌军用大炮攻击 29军阵地,而孙敬生所在部队只能以机枪和迫击炮还击。孙敬生和战友死守阵地达半个多月,后终南撤至保定。
后来,孙敬生还参加过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等战役。1949年淮海战役中,随队伍投诚起义参加解放军。解放后在南京军区某团当参谋长,1955年评中校军衔,后来到天津市工作,共育有3子1女,现和老伴生活在一起,曾患有冠心病。
马步先
87岁,曾用名马胜云,祖籍河北冀县,现住北京市朝阳区。17岁时来到北平加入29军37师110旅219团3营12连。“七七事变”时,他曾在卢沟桥上阻击敌人进攻。仅靠步枪和大刀,马步先和战友死守卢沟桥达20天之久,7月27日后撤到良乡。
之后,马步先随军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1949年脱离国民党军队退伍,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志愿军中从事后勤工作。战争结束后,马步先一直在人大附中当财务人员,“文革”期间挨过批斗。马步先共育有1子1女,近年来心脏一直不好,耳朵也接近全聋,生活全靠女儿照料,但他仍坚持资助两名华北的贫困大学生和上海一名孤寡老人。
马玉槐
90岁,河北任丘人,原29军109旅217团1营4连7班战士,现住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37年7 月初,平津形势紧张,马玉槐随部队开赴宛平驻防。“七七事变”爆发后,马玉槐在宛平城外担当前哨,他和来犯敌人展开白刃战,大显“大刀军”神威。29军撤退后,马玉槐留在冀中地区抗战,后参加解放军。
解放后,马玉槐一直在北京工作,后来成为一名机关干部,中间曾支援过宁夏建设。共育有7名子女,现在和老伴生活在一起。
1937年7月7日,北平大雨初停,闷如蒸笼。
那一天,来自河南项城的崔金品在37师师部如常值班,当天的电话和电报奇多;17岁的张可宗则在河间府听闻北平局势紧张,忧心忡忡。
那一天,18岁的赵金典在颐和园大门前站岗,瞪圆的双眼怒视着招摇过市的日本兵;21岁的马玉槐则在长辛店照常练习他的4式枪、4式刀和4式拳。
那一天,219团3营战士马步先在宛平城内听着日军近乎挑衅的演习声,紧张得连刀柄都攥出了水;217团机枪连班长孙敬生则与战友高唱了一遍《八德军歌》和《吃饭歌》。
那一天,17岁的军训团学员李鸿斌在南苑军营温习刚学过的军事理论,对面200米处是日本欧亚航空公司,日本兵频繁穿梭其中。然而,仅仅几个小时后,一阵鸣响于卢沟桥的枪声,将这7个素不相识的29军士兵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拉开,中华民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70年后的今天,当年那些共赴国难的热血青年,大都已相继离去,存活者也都是耄耋老者。作为“七七事变”的亲历者,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珍贵的“活历史”。
然而,再顽强的生命也难敌岁月的消磨。前些年,亲历“七七事变”的29军老兵在国内还能找到18名,但到了2006年,这个数字便骤减为9名。随着今年上半年天津冯义田老人和河北韩立才老人的先后离世,如今仍在世的29军老兵在国内只剩下7名,他们大多已是年逾9旬,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今年是“七七事变”70周年,为保存下这些随时可能消失的记忆样本,本报记者辗转找到7名老人,记录下他们当年所见证的“七七事变”,并还原70年前那场震惊中外的战事的部分细节。
每天抱着枪睡觉
赵金典记得,北平的气氛,从1937年6月就开始紧张起来。日军陆续入关,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与平津地区的中国守军29军成对峙之势。
当时的赵金典是颐和园的一名门卫。年仅18岁的他体格过人,参军不久便被选入特务团手枪营—— 一支专门负责保护师部的精锐部队。白天站岗时,赵金典时常能看见日本兵排着方队,喊着听不懂的口号穿街过巷。有时候甚至还有坦克车跟在后面。
这阵势惊扰了不少北平市民,但日军却美其名曰为“演习”。生性耿直的赵金典看不惯日本人这副嚣张嘴脸。每次有日本部队经过时,赵金典都把身体挺得笔直,瞪圆了眼睛。师部首长好几次称赞他“没给中国军人丢脸”。
与此同时,29军也针锋相对地进行各种演习,若是迎面遇上日本兵,战士们就与对方互顶肩膀。“29军武风盛行,日本兵扛不过我们。”一天上午,两个日本兵要求进入颐和园,但遭到赵金典的拒绝。日本兵开始无理挑衅,赵金典一言不发,把背后的“大片刀”抽了出来。看着刀身上的寒光,日本兵吓得转身就跑。赵金典露出一丝微笑,对着对方的背影做了两个劈刀的动作,手上青筋暴突。
当赵金典为他的“大刀吓鬼子”的故事而沾沾自喜时,驻守在宛平城的37师110旅219团3营士兵马步先正感受着战争临近的气息。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附近的演习几乎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们以宛平城和卢沟桥为“假想敌”,没日没夜地练习着攻城。开始还是空弹训练,后来干脆变成了实弹演习。
这让这位17岁的河北青年在一个多月里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天晚上都抱着枪睡,有时候半夜被日本人的叫声惊醒了,就紧紧握着刀把,双手很快就汗水淋漓了。”
此时29军与日本华北驻屯军之间已势如棋盘,当日军频繁“走子儿”时,29军却对形势的判断一错再错,为日后的被动挨打埋下了伏笔。1937年5月,军长宋哲元携家眷回山东老家,他过分乐观地认为此行将“使日方失去纠缠目标,可以缓解日方胁迫之势。”
7月6日,北平大雨。日本人当晚把大炮和战车推到了宛平城外的卢沟桥火车站,气氛骤然紧张。马步先和衣躺在宛平城内一个叫“崔家店”的旅店内,黑暗中,他把步枪和大片刀放在身旁,双手紧握,如临大敌。
“是日本人先开的枪”
1937年7月7日,暮色降临,气氛变得越来越凝重。在大瓦窑一带的日军迟迟不撤。宛平方面也开始有所警觉,天黑前,县警察局下令把东门关闭,不许出入。
晚上10点40分左右,一阵枪声从宛平城外传来。正在卢沟桥下永定河岸布防的马步先惊得从地上跳了起来,推弹上膛,对准前方。“是日本人先开的枪。”时过70年,87岁的马步先仍能清晰记得当时枪声是从城东北方向日军阵地那儿传来的。
枪响后,日方称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要进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严词拒绝。双方僵持到8日凌晨5时左右,几枚炮弹突然飞越宛平城墙,正中金振中营营部,日军开炮了。
“位于卢沟桥北面的铁路桥最先发生战斗。”马步先回忆说。当时29军在桥上只有两个排共80人左右的兵力,由于寡不敌众,仅仅坚持了15分钟,就被日军占领了铁路桥和回龙庙,扼住交通咽喉。
此时,马步先所在的12连正往南支援卢沟桥阵地。此时镇守卢沟桥上的一个排已经打剩为8个人,排长也牺牲了。
敌人密集的炮弹将天边照得白亮,宛平城东顺治门城楼也被击毁。马步先不时在卢沟桥和沿河战壕间换防,敌人来犯时,就用捷克式步枪射击。按照训练要求,本来要待敌人进入200米范围内才能开枪,但有些战士还是太紧张,敌人远在六七百米以外,就早早扣动扳机,浪费了不少子弹。
双方在卢沟桥阵地陷入胶着状。马步先已经一天一夜没睡过觉了,枪声停下的时候就靠着掩体小憩。战士们轮流站岗,一炷香一换。炊事兵也分散到各个班战斗,战士们只得自己动手做饭,多是些烙饼、面条等东西。
7月8日拂晓,北平又下起了滂沱大雨,战壕里一片泽国,马步先站在泥泞中,被雨水模糊了双眼。
“七七事变”迅速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双方接火后数小时,29军军部就发出命令:“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次日,远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发表宣言疾呼全国人民:“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当时将士们的士气非常高涨。铁桥失守后,镇守宛平的3营营长金振中决定组织敢死队去收复,结果群情汹涌,一下子去了几百人,把桥上的鬼子都给赶跑了。”马步先回忆说。
大刀的刀刃都砍卷了
当马步先和战友在战壕里坚守了一夜后,援军37师109旅217团在7月8日早上赶至卢沟桥。他们的到来引起一阵欢呼。217团1营4连7班战士马玉槐和战友赵书云随即被命令为前哨,到宛平城外观察敌情。
中午时分,10多个端着三八枪的日本兵进入马玉槐的视线,马、赵二人边打边撤,敌人恃着人多,叽咕着就扑了上来。马玉槐抽出背上的大刀,一个横劈,刚好磕歪了一个日本兵的刺刀,对方露出空当,马玉槐趁机向前一刺一拧,日本兵在惨叫中倒下。
阵地上别的战士听到声音,都纷纷赶过来支援,日本人丢下几具尸体就跑了。这样的白刃战时常上演。29军人手一把大片刀,连伙夫都有。刀长三尺,七斤重,耍起来风快。
大刀在卢沟桥守卫战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219团团长吉星文就数次脱下上衣,带领战士冲进敌阵,回来的时候刀都卷刃了。“日本人很怕跟29军打白刃战。”马玉槐说。
“七七事变”3天后,为声援“大刀军”而作的《大刀进行曲》闻世。这首歌琅琅上口,很快便传遍全军,开头第一句歌词便是日后广为人知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但大刀仍然无法扭转敌我装备悬殊的局面,守卫卢沟桥的219团伤亡惨重,团长吉星文不得不向37师师长冯治安求援。
而另一边,开战后,赵金典曾护送37师师长冯治安两次上桥督战。他记得当时卢沟桥和宛平城墙都已是弹孔累累,城内有些地方还冒着青烟。阵亡士兵的尸体被战友冒险拖了回来,个别新战士没见过此场面,禁不住哭了起来。
“北平城里的反日游行多了起来,城里也堆满了全国各地寄来的慰问品。”赵金典在颐和园站岗的地方,已经少有日本人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抗战情绪高涨的大学生和各式救亡团体的到来。
时为37师109旅217团机枪连班长的孙敬生也在此时随军驻扎进长辛店。日军的大炮雨点般地落在他们的阵地上。“附近菜田里的蔬果叶子都被震掉了,很多战士都被炸成碎片。”
在随后半个月的时间里,孙敬生所在的连队仅靠6挺机枪和6门射程极短的迫击炮还击敌人,场面非常惨烈。
学生军十命换一命
当卢沟桥阵地烽火连天的时候,离北平20多里远的南苑军营仍是一片平静。17岁的军事训练团学员李鸿斌在这里如常训练,如常学习。他和其他1700多名知识青年一样,将被训练成未来的指挥官。
炮声日隆,但在每周一的训话课上,副军长兼军训团长佟麟阁除了鼓励同学们尽早学成报国外,并不提及北边战事。一些心急的同学跑去问教员,得到的答复大多是“很快会和谈解决的”。
当时抱有这种乐观心理的29军将士并非少数。“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固守宛平,就地抵抗”,企图将战事控制在局部范围内。7月 7日至7月25日期间,事端4次被日军挑起,冀察当局又4次与对方坐到谈判桌旁。此时期双方处于拉锯阶段,战事时断时续。
事实上,29军已经被日本人的烟幕弹所迷惑,“和谈”实则日军的缓兵之计,在双方僵持之际,日军大批入关。至7月25日左右,日军集结在平津地区的兵力已超过6万,还运来飞机坦克,实力已在29军之上。
“7月26日气氛开始不对了,学校也停了课。”这一天,李鸿斌领到一把铁锹,被安排到军营四周挖战壕。同学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以为要上实地演习课。就在这一天,华北驻屯军突然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对方在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完成调动布防的日本人准备发起北平总攻,攻击重点正是李鸿斌所在的南苑兵营,由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率领的南苑守军仓惶应战。
战壕挖好了,军营四周200米范围内的高梁和玉米也被砍掉,各主要路口还放置了圆木作路障。27日傍晚,李鸿斌领到了一杆步枪,200发子弹,4颗手榴弹和一把大刀,外加3天的干粮。有些同学知道要打日本了,兴奋得一个劲地拍掌。
在战壕里候了一夜,28日天刚亮,一阵轰鸣声由远及近,10多架日军飞机飞至南苑上空,洒下大批炸弹。教员刚喊完“同学们趴下”,爆炸声就此起彼伏。营房起火了,阵地到处是两三米深的弹坑。 轰炸稍停,李鸿斌抬起头,有炸弹直接落入战壕里了,残肢断臂布满一地。
这些第一次上战场的学生兵,还没来得及开第一枪就丢了性命。飞机走后,大批日本兵开始缓步前进,前面还有坦克开路。当时李鸿斌还没有见过坦克,只觉得那些“铁砣”势不可挡,子弹打上去一点作用也没有。而南苑守军缺乏重型武器,威力最大的也只是手榴弹和迫击炮,敌人打到跟前了,就跳出战壕用大刀砍。
交火中,李鸿斌看见旁边一个学生趴在土堆上一动不动,于是上前推了一下,结果粘糊糊的满手是血,他已经牺牲了。一位叫赵世荣的同学下颚被炸弹炸飞了,仍抱着机关枪射击,滴下的鲜血染红了整个胸膛。还有些同学被弹片穿透了肚皮,肠子流出来了,用手捂都捂不住。
在敌人密集的火力网下,同学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李鸿斌扔完了四颗手榴弹,就用大刀砍,刀刃上满是敌人的鲜血,已经看不到原来的颜色。到下午2点左右,学生军打退了敌人3次进攻,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700多人剩下不足三分之一,而敌人仍源源不断地涌上来。军训团只得下令撤退,1、2大队向北平方向行进,李鸿斌所在的3大队向南撤离。7月28日傍晚,南苑失守。
“敌我悬殊,加上作战经验不足,我们学生军几乎是十命换一命。”李鸿斌后来在撤退的路上看到北平报纸上登载了消息:“29军军事训练团学生兵英勇抗敌,全团覆没,壮哉!”
“我看着赵将军咽气”
28日下午,守军从南苑撤退后兵分两路,一南一北。佟麟阁和赵登禹选择了往北平进发的路线。
17岁的张可宗时为132师特务团工兵营战士,他的任务是要保护师长赵登禹安全撤离。当时南苑至北平的路,都是三四米宽的沙石土路,两旁是比人还高的青纱帐。很快,仓惶北逃的士兵就把这里堵得水泄不通。日本的飞机追赶至上空,投弹扫射,地面上又是一片血肉横飞。沿途的老百姓已经听说了南苑战事,他们纷纷从家中拿出馒头、窝头,西瓜、酸梅汤等东西,送给29军将士。
行至半途,佟麟阁和赵登禹都从汽车里下来,一是汽车目标太大,二是要亲自疏导混乱不堪的部队。张可宗和特务团的战士紧紧跟着赵登禹,赵一手拿手枪,一手执大刀,看着溃军,眉头紧皱。
途经大红门时,两边的城楼突然出现日本兵的身影,他们居高临下,用机枪扫射29军。赵登禹一边组织四处逃窜的士兵,一边用手枪向敌人还击。张可宗和几名战士上前想把师长拉到掩体处,但赵拒绝了。很快,赵登禹腿部中弹,他坐在路边,继续指挥战斗。张可宗的腹部也中了流弹,但他不敢离开,他蹲在师长旁边用步枪向高处的日本兵射击。
战至下午4时左右,赵登禹身上已经多处中弹,成了一个血人。他再也支撑不住了,倒在了地上。张可宗和几名特务团战士马上把他扶住。此时的赵登禹已经气若游丝,他抓住张可宗他们的衣服,说:“回去告诉我母亲,儿子尽忠不能尽孝了。”不久后,赵登禹断了气。这位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名将,死时仅39岁。
此时,有些战士也跑过来说,副军长佟麟阁也被机枪击中头部,壮烈殉国了。是年,佟45岁。
张可宗和部分战士最终突围,把两名将军的死讯带到了北平。7月31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恤令,追认佟麟阁、赵登禹为陆军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佟、赵二人也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最早牺牲的高级将领。
大撤退
南苑失利是平津抗战的转折点,不但折了两员大将,还迫使29军撤离北平。7月28日后半夜,37师特务团团长副官崔金品接到命令,准备随军南撤。
崔金品感到很为难,他刚获得消息,当年一起来北平参军的同村兄弟赵学珍在一次偷袭日军时不幸牺牲了。崔金品想,老乡的尸体一定还暴露旷野,如果不帮忙收拾一下,以后就没法跟人家爹娘交代了。 战友们开始收拾东西了,崔金品偷偷来到机械房,拿了一支美式枪和一把铁锹,直奔日军大营。日本人已经转移了,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29军战士的尸体。当时天很黑,风把周围的树刮得呼呼作响,他根本无法辨认哪具才是老乡的尸体。
稍作思考,崔金品决定把所有29军战士的尸体都安顿好。院子里有个废弃的地窖,他一边喊着“赵学珍”的名字,一边把能看到的战士都拖进里面,处理了20多具尸体后,天边已经发亮。
崔金品立即跑回团部,此时部队已经撤退。他从厨房背了两袋子白馒头南追而去。此时,日本人已经开始进入北平城,崔金品跑了没多远,敌机就在上空投弹了,迫击炮也在身边爆炸。崔金品一路狂奔,中午时分,他终于赶上了部队。
29军撤离后,7月29日,北平沦陷,同日,38师从天津撤退,30日天津失守。平津地区完全落入日本人之手。
崔金品、赵金典、马步先、马玉槐、孙敬生、李鸿斌、张可宗,这7位士兵各自跟着所属部队南撤,一路上,失望情绪在军中弥漫。他们后来大多到了河北保定,经休整后又奔赴各地继续抗战,8年后取得胜利。
“虽然‘七七事变’最后以29军撤退告终,但也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帷幕。自此以后,各方力量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李鸿斌说。
70年后的军礼
在此后的70年间,曾因“七七事变”而走到一起的7位29军老兵,命运各异。7人后来全都脱离了国民党军队,其中李鸿斌、崔金典、孙敬生、马玉槐更起义投诚,加入共产党的军队。
建国后,7人大部分都退伍另谋出路,只有李鸿斌和孙敬生还继续在军队工作。尤其是孙敬生,曾在南京军区某团当参谋长,1955年评中校军衔。李鸿斌则是部队里一名普通的教员。现在孙住天津,李则在南京养老。
马步先虽然没有参加解放军,但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他主动请缨,参加了志愿军的后勤部队。战争结束后,马步先在人大附中从事财务工作。“文革”期间,因为曾经的“国民党兵”身份而饱受批斗。马步先共育有1子1女,前不久他接受了心脏手术,耳朵也几乎全聋,生活全靠女儿照料。
和马步先一样,马玉槐建国后也去了北京,50年代还当上北京市民政局局长,算是7人里仕途最顺的一位。后来,他还支援过宁夏建设,共育有7名子女。
与其他几位不同,崔金品和赵金典退伍后并没有选择城市,而是回到河南老家,务农为生。崔育有1子4女,生活小康。赵金典却没这么好,他曾当过村里的会计,80年代退休后就一直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平房里。去年中风后,记忆力越发衰退,连村里的一些熟人的名字都记不起来。
张可宗的遭遇可谓7人里最潦倒的。1949年6月他从国民党军队退役后,辗转到重庆,靠做一些小买卖为生,改革开放后还做过个体户,开过小工厂,但均无积累。现在他和老伴每月只靠领420元的低保过活,且老病缠身。
7位老兵虽际遇不一,但现在,他们都在共同期待一个重要的时刻。前不久,在一群民间爱国人士的筹划和帮助下,7名老兵将于今年7月7日重登卢沟桥。这些幸存的历史见证人,在那一天,将举起布满皱纹的右手,向70年前并肩作战的29军将士们行最后一次军礼。




















![>赵丽蓉的大儿子]赵丽蓉儿子照片](https://pic.bilezu.com/upload/b/2c/b2cf8a8c08fed0ca34475beae210b30d_thumb.jpg)

![>赵登禹的大刀 [纪念抗战不能忘却的那些人]大刀将军赵登禹](https://pic.bilezu.com/upload/8/4f/84f84cba2ed4fb2147be2a15cccf86ef_thumb.jpg)